“兩個爭吵中的哈薩克人,只要有一位引用阿拜的詩句或箴言來說服對方,衝突便會戛然而止,雙方很快就會握手言和。這種情景,在哈薩克草原上並不鮮見。”
這是詩人沈葦所著《新疆詞典》的第一個詞條“阿拜”的開頭,這本詞典一共囊括了關于新疆的111個詞條,涉及十幾種文體。
沈葦本是浙江人,但他在新疆一呆就是27年,他曾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青,向往邊疆,常常腦子一熱,帶上簡單行李,懷里揣很少一點錢,坐上綠皮火車就遠行新疆、西藏而去了。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大多熱愛北上廣,喜歡大城市,喜歡到‘中心地帶’去當‘沙丁魚’。這是兩種不同的時代氛圍。”而他調侃自己是以“遲到的盲流”和“無知者”的身份闖入新疆的。
他在新疆做過教師、記者,現為新疆作協專業作家,《西部》文學雜志總編。“如果我不離開浙江,不離開江南,不去新疆,也會寫詩,但我的寫作肯定不是目前這種狀態。”
蓄須讓沈葦看起來有點新疆人的感覺,不過陳丹青對他說:“你看起來還是南方人。”關于蓄須,沈葦還有一個好玩的說法:“我發現大部分留胡子的人比不留胡子的人要害羞。”
現在回到浙江,別人都認為他是新疆人,而在新疆,別人又覺得他是南方人,說不定哪天就離開了。不過沈葦認為這種身份分裂感和尷尬挺真實的,倒不是壞事情。
沈葦覺得在這二十幾年中,新疆和自己是相互的捕獲者。“第一故鄉給了我啟蒙,第二故鄉給了我啟示、教誨。我是新疆的新移民。移民是試圖與遠方、與異鄉結合的人,而異鄉無疑是移民最好的、也是謙卑的課堂。”
這兩年沈葦也有往內地調動的機會,但他都放棄了。一方面是情感的因素,“情感是跟時間有關的,你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越長,你對它的情感就越深,所謂日久生情嘛。寫作正是從這種情感中一點點成長起來的。”還有一個原因是新疆還在吸引他、捕獲他,“我覺得還沒待夠,即使暴恐事件也沒把我趕走。”
沈葦說,在新疆生活的一個有福之處,在于可以欣賞自然、人文、民族等各個層面的差異性。抹去了這種差異性,新疆就不能稱之為新疆了。在新疆文學界,有很多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雙語作家,沈葦平時和他們交流較多,同時他主編的《西部》文學雜志也在不斷發掘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
在沈葦來上海參加活動之際,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就《新疆詞典》的寫作和新疆的多元文化等問題專訪了沈葦。

詩人沈葦
新疆的魅力在于差異性和多樣性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新疆表達”的說法,它具體指什麼?
沈葦:老實說,新疆還沒有找到自己最好的“表達”。因為表達上的失語狀態,使其主體性和內在的真實性沒有得到很好呈現。新疆以前用的旅遊宣傳口號是“魅力新疆”,然後我到網上一查,發現全國從省到地區到縣到鄉到村有300多個“魅力XX”,這就等于什麼都沒說。
“魅力”這個詞已經被用濫了,再用到新疆身上其實是在矮化新疆、遮蔽新疆。一說起新疆,我們總想到“歌舞之鄉”、“瓜果之鄉”等,把新疆變成審美消費的對象,卻唯獨忘掉了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人。我曾在一篇訪談中講到,對于新疆,與其一味強調這個民族那個民族的,還不如多講講“人”。“人民”不是個抽象概念,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在邊疆,哪有這個民族那個民族的,只有一個個的人、一顆顆的心啊。當文學越過民族的邊界,就能找到屬于人的表達。
關于新疆,我在《新疆詞典》里提到了幾種表述:我曾稱新疆是以天山為書脊打開的一冊經典,南疆北疆都是它的頁碼,沙漠綠洲雪山草原都是它的文字。我也曾稱它為“啟示錄式的背景”,世界上三大宗教,有兩個就是產生在沙漠背景中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宗教”一詞拉丁文的原義就是“恐懼”,人有恐懼,就會尋找上帝,就有了信仰。人處在戈壁沙漠中,在荒涼的大背景下就會有堅定的信仰,也會有強勁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上帝是公正的,他將一塊土地變成沙漠,變成不毛之地,但同時將石油、天然氣等藏在了地下,地下有寶藏,所以我認為新疆雖然表面上是荒涼的,但它骨子里的文化是燦爛奪目的。這也是一個表述。
《新疆詞典》沒有前言和後記,所以這次我來之前特別寫了兩首短詩作為前言和後記,這也可以當做我對新疆的表述吧。前言我寫了三句:“世界的存在是為了成就一本書,她願意成為我的一本書嗎?因為它已是大地的心經和原典。”後記我寫了兩句:“我找到了愛她的111個理由,同時得到了166萬平方公里的憂傷。”
我們再來談一談新疆的精神狀態。我想到一個詞——正午。新疆的精神狀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正午時分的寺廟拱頂,同時結合了生命和死亡、陽光和陰影。新疆歷來在政治上與中原關係密切,但在精神氣質等方面,西來文化對它的影響很大。生活在新疆,飲食、人的舉止個性、思維方式等方面有某種歐洲特點,甚至帶有一點土耳其、希臘、印度和阿拉伯的味道。我們常說新疆是四大文明融匯的地方,塔里木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館,現實生活中也能感受到這一點。
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的邊緣,就是地理學中的特提斯海,因為大陸架運動,後來古地中海慢慢萎縮成為現在的樣子,但我覺得這股地中海的精神一直融在新疆的血液里。在《新疆詞典》最後一篇“正午”中,我提到過這種正午的積極態度,不像現代人一味地通過病態、畸形和虛無的東西來反抗。加繆將地中海精神稱之為“正午的思想”,他說:“如果說,古希臘人制造了絕望與悲劇的概念,那總是通過美制造的……這是最崇高的悲劇,而不是像現代精神那樣,從醜惡與平庸出發制造絕望。”
所以說,我們講亞洲腹地的精神地理,歸根到底還是在講人,雖然我知道現在好多人到新疆,首先還是受到地域的感官衝擊,一種自然的震撼。所謂的新疆精神,所謂的亞洲腹地的精神地理,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就是一種反抗虛無和死亡的精神。從這一點上講,雖然現在新疆的處境有些艱難,但是我對新疆的未來不絕望。新疆絕不是“暴力”的代名詞,那里的人們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吃飯、睡覺、生兒育女等等,這種日常性才是更為真實的存在,它是不可顛覆的,就像天山、昆侖一樣不可顛覆。請問,誰能顛覆天山、昆侖?
沈葦:內地文化是很單一的文化,有時候在江南待著跑來跑去,每個地方都差不多。新疆的魅力在于差異性,民族之間、文化之間、習俗之間的差異,這種東西是非常有魅力的。差異性如果被抹殺的話,新疆也不是新疆了。差異性給新疆文化帶來一種混搭色彩,新疆文化是一種混搭文化。混搭文化是很有魅力的文化,就像女孩子喜歡波西米亞風格,它就是身體上、衣飾上的混搭文化。拉美就是混搭文化地區,所以拉美才有印第安文化和殖民文化的糅合,最後產生了拉美文學爆炸。古絲綢之路也是混搭文化,地中海地區也是,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
混搭文化很有魅力,你感覺到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間可以互為鏡像,互為映照和參照。在混搭文化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參照係,這種參照係可以延伸到印度、希臘和羅馬文化,可以延伸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體係。盡管混搭出來的是一個小地方、偏遠地方,但是延伸出去的東西太多了。混搭文化幾乎代表著一種無限的可能性,我覺得它對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澎湃新聞: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詩人的細膩才能敏感地體會到?
沈葦:不單單是寫作者,生活在那里的每個人都能受到啟發和影響。長期生活在一片土地上,文化之間的交融、相互影響,普通人也能感受到。比方說,很簡單的,漢族人會去吃維吾爾族的瑢和烤肉,吃哈薩克族的手抓肉,喝蒙古族的奶茶,飲食就是一種對話和交流。
新疆的漢族人受了很多少數民族生活習性的影響,他們好客直爽、感性熱情,就是受少數民族影響的,新疆漢族和內地漢族還是有一點區別的。在新疆,大家一起吃飯很有儀式感,南方好像沒有這種儀式感。在新疆吃飯前,請客的人一般要站起來發表演講,漢族人吃飯也是這樣的,關于“今天為什麼要請客”,要發表頭頭是道的演講。
吃完飯,在南方好像就一哄而散了,而在新疆,一定要請一個身份地位高一點,最好年齡大一點的人發表總結,把每個人都要點評到。我遇到過一個在喀納斯景區工作的朋友,他寫詩,會唱歌,可以現場把每個人的特點匯集起來編成一首歌,把客人的長相、職業、性格特點等編到歌里去,最後唱一遍作為總結。
新疆人喝酒比我們江浙要文明、浪漫,我們江浙人最後一點酒要倒給一個領導或一個老板,叫發財酒,新疆的最後一點酒要倒給長者、女士或者遠道而來的客人,叫幸福酒。幸福比發財更重要、更高級,發財的人不一定幸福,幸福的人可能很窮,但他就是幸福。喝酒的這個儀式,新疆人無疑比江浙人有文明高度。這也是日常的文明,各民族之間相互受影響。
澎湃新聞:那這種混搭文化是不是只有異鄉人才更容易感受到?
沈葦:不一定的,因人而異。異鄉人在今天是指移民、外來者。但我恰恰看到很多外地去的人對新疆的描述經常是浮光掠影的,甚至是以訛傳訛的。當然本土的人,由于生活時間長,容易引起感受上的麻木和遲鈍。作為出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確需要一點跳出地域看地域、跳出自己看自己的勇氣。
作為外來的人,即使你是一名遊客,也應該更多深入了解新疆,不要只是看新疆的風景,看大山大水,也要了解民族的心聲,與人接觸,才能有更大的觀察和收獲。現在常有內地詩人、作家、畫家和音樂家,經常到新疆生活一段時間,住在村子里面,這樣就有深入、細微、真實的體悟。
澎湃新聞:南方人到新疆和新疆人到南方會不會有利于打破文化邊界?
沈葦:對。人的第一故鄉無法選擇,父母無法選擇,出生的村莊無法選擇,但是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第二故鄉甚至第三故鄉。人在地域變遷和文化反差中受益無窮,會從單一的人變成多維度的、開放開闊的人。當然變遷中也有衝突,不可回避的文化衝突。
比如內高班(編者注:內地高中班,讓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內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學生,他們在新疆有的初中畢業一句漢話都不會說,他們到內地要先學漢語。內地這些城市對他們來說完全是新鮮的地方,他們要適應,要和漢族人接觸,困惑和衝突是必然的。但人是可以溝通的。我最近讀了一本關于內高班的報告文學集,內地的漢族人、老師為了那些孩子真是付出了好多心血。這種溝通我覺得是可能的,交流也是必須的。
我認識一個維吾爾族男孩,現在是我的詩友,叫麥麥提敏·阿卜力孜,1992年出生,他是和田地區皮山縣的一個孩子,初中畢業就到北京通州的潞河中學學習,潞河中學是全國第一所辦內高班的中學。他去的時候一個漢字都不會寫,一句漢話也不會說。但幾年下來,他遇到了很好的老師,他的班主任在北京好像也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小說家,培養他用漢語寫詩。他現在在江蘇上大學,今年應該畢業了,已經出了兩本漢文詩集,還獲得了我們《西部》雜志的“西部文學獎”。對他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維吾爾族詩性思維和優雅的漢語言結合起來後,造就了一匹詩歌黑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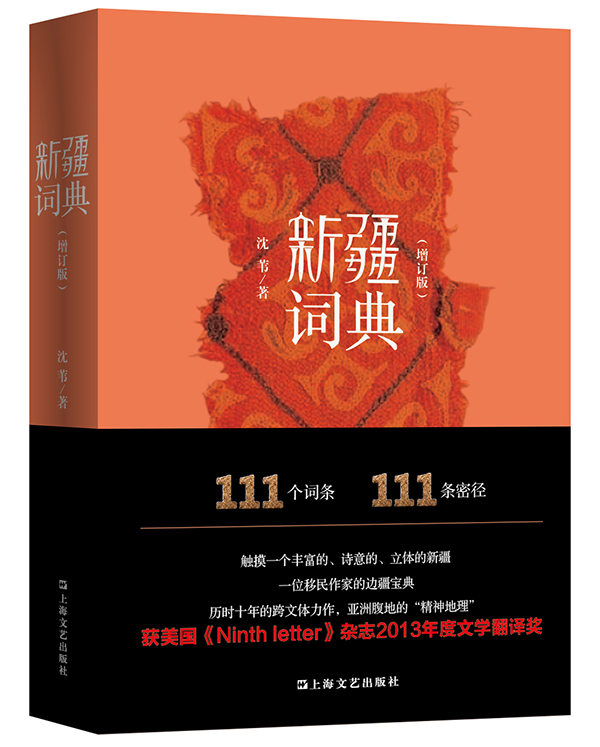
《新疆詞典》,沈葦/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4年10月版。
寫作者需要打破文化和語言的界限
澎湃新聞:《新疆詞典》中的詞條是您事先規劃好的還是之前文章的匯編?
沈葦:其實這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因為我的寫作主要是詩歌,散文對我來說是詩歌的延伸和拓展,也是詩歌之外的一種表達和補償。持續寫詩就像在建一座城堡,我在這座城堡旁邊蓋了一個房子、一個驛站,它就是《新疆詞典》。它提供了理解新疆、進出新疆的一些通道。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跨文體的寫作。因為我對目前散文的寫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約瑟夫·布羅茨基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詩人和散文》,他認為一個詩人在散文中學不到什麼東西,但相反,一個散文家在詩歌里可以有很多的收獲,比如說專注力、凝練和警覺高漲的情緒等。
而且我發現當代文學有一個特點,在我接觸的小說家里面,一流小說家是喜歡詩歌的,會讀詩,探討對詩歌的感覺,二流小說家則對詩歌沒有感覺,三流小說家排斥甚至是痛恨詩歌的。我上次在廣州參加“花地文學榜”的頒獎典禮時碰到了畢飛宇,他的短篇小說是很出色的。他說自己短篇小說的靈感幾乎全部來自于詩歌,這句話讓我很有感觸。
還有就是現在散文的寫法越分越細,有一種不好的“專業化”、“分類化”傾向。古人只有“詩”和“文”的區分,詩歌之外的文體都屬于“文”,包括筆記、話本、雜劇、小說等。而我們現在散文的“文”分得越來越細了,就像大學里的分科一樣,有理科、工科和文科,各科里面也分不同的係和專業,例如我女兒在大學的生命科學院就讀,光生科院里面就有三個專業:生物技術、生物工程、生物制藥。我問她這三個專業有什麼區別,她說大同小異。分得太細了。散文也是一樣。
所以我想通過這本書打破文體之間的界限。我在詩歌寫作中提到“綜合抒情”和“混血的詩”的說法,講求的也是綜合性。當然邊界在文學中是存在的,在文化中也是存在的,甚至也存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總的來說,《新疆詞典》的寫作體現的是一種跨文體的追求,就像現代學科里的“超文本”概念,當然這也是越過語言邊界的一種努力。新疆有52個民族,我們需越過各民族的邊界找到一種超越個人經驗、體現他者自我化的言說,也就是“為他人”的言說,這是文學的基本倫理。作為作家的那個“我”,不單單是一個作為自己的“我”,“我”身上還可能活著他人的靈魂甚至動植物的靈魂、大地和星空的靈魂。
沈葦:我們再來講一講“混血的詩”,我一直覺得詩歌是一種陰陽並濟、雌雄同體的藝術。“西部文學”這個概念太符號化了,什麼“雄壯”啊、“豪邁”啊,其實西部既可以是太陽照耀下的陽剛的西部,也可以是“明月出天山”意境下陰柔的西部。
我在新疆生活了27年,有時會感覺到光憑詩歌來表達新疆已不夠了,需要其他一些文體的努力,來激發我、推動我。包括辦雜志也是以“尋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學表達”為辦刊宗旨,謀求地方性和國際化的結合。所謂地方性,就是《西部》雜志要立足西部,國際化則是指一定要有國際視野,一種開放的文化視野。除詩歌之外,我還寫了一些舞臺藝術作品如歌舞詩等,就是想從多方面來呈現新疆。
澎湃新聞: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您有身份認同的焦慮嗎?向別人介紹自己會說自己是浙江人還是新疆人?
沈葦:有尷尬,有衝突,有矛盾,但都挺真實的,不是壞事情。會有這種情況:回到浙江,他們不承認我是浙江人,說我是新疆人;到了新疆,他們又說我是南方人,說不定哪天就離開了。在他們的種種“假想”中,我就變成懸空的、沒有立足之地的人了。
我寫過一首詩叫《兩個故鄉》。但我現在覺得兩個故鄉已不存在——浙江和新疆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了。從現在的生活來說,空間的概念已經不太重要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往返新疆坐火車,四天三夜,81個小時,有時候坐票買不上還要站上一兩天。林則徐當年發配伊犁充軍,從北京到伊犁走了一百天,放在那個時候,我要是一去新疆可能一輩子就見不到父母親了。
現在回浙江一趟很方便,我早上早點出發,坐飛機到虹橋機場,然後再坐車回家還趕得上吃中飯,半天就到了。現在,人的距離不在空間上,人的距離在心里,空間已不是距離概念。說到前面《異鄉人》這首詩,我是移民,移民就是異鄉人,是“他鄉的隱形人”和“故鄉的陌生人”。古人回到故鄉是“物是人非”,小時候的房子、種的樹都在,但是人都變了,上一輩去世了,同輩變老了。現在叫“物非人非”,環境被徹底改變,鄉村被連根拔起,人真正的故鄉回不去了。
故鄉是人隨身攜帶的東西,就像我們隨身攜帶著語言和詩歌。母語是寫作者最後的故鄉了。我曾說自己得了西部和江南的地域分裂症,我是一個有裂痕的人。《異鄉人》那首詩里說,自己就像一只破皮球,被江南和西域兩只野蠻的腳踢來踢去,但這樣並不痛苦。成為這樣一個人,既是分裂的,也可以通過寫作去治療的。通過地域分裂、文化分裂甚至內心分裂,我更熱切地去尋找一種完整性。
(陶越彥、李靜雲亦對本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