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R��
�@�@�Q��s���i�R�¡A�Q�g�����i�R�¡A�o���G�Ʒ|�@���y�ǤU�h�A�o�����A�|�û��Q�H�O�o�C�o���@�~�P�Ч@�A�b�U�ؼ��x����Ū�P���Ҫ��y�Ҥ��A�ɱ`�u�O�����c�D�M�ꪺ�䨤�ơC�b�o�h�@�᪺20�~��A�γ\�i�H���s�ɥѦo���u���Ч@�A�إh��¶�b�o���W�غت����λP�L�СA�Ӭ}���i�R�¤~�ػP��Q�u���o���������C �����m��A�١n���~�|�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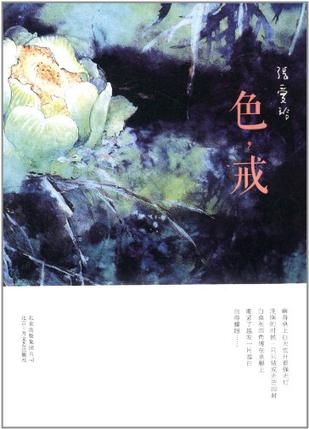
�@�@�p���m��P�١n�@�@���_�m��A�١n�p���G�ƭ쫬�A���ֵ����V�O�A1939�~�Gī�p����L��ä�U�B�qߗ���u��ƥ�C�W���W�D�Gī�p�ͤ_1918�~�A�O���~�W���Ĥ@�j�e�����}�͵e�������N��@���ʭ��k���C�W���_����A�o���K�[�J���ΡA�V��_�鰰�H�������A��������C��ѻP�t���鰰�S���Y�l�B�q���A���S�����Q���C�Ǫ̳��l�����g���L�A�Gī�p����B�q�����ɭԡA�i�R�¨å��b�W���A���ɦo�O�b����Ū�j�ǡC�o���D�o��Ʊ��A�O�q��ӤW���U�ؤp�����j�v��V����x���C�٦����k�O�A�i�R�¬O�q�J�����f���o���o�ӬG�ơA��o�F�ԲӲӸ`�ó̲ױN��g�i�F�m��A�١n���C�@�@�m��A�١n�]�Q�{���O�g�ɤF�k�k�����̥��誺�P���A���L�̬O��l���y�H�P�y�������Y�A��P�Ϊ����Y�A�̲��������C�o�o�ͬO�L���H�A���O�L�����C���ҥH���t�~�@�ر����O�A�m��A�١n�v�g�F�i�R�©M�J���������Y�C�@�@�쫬���i�צ����j����p���m��P�١n���M���ݪk�A���G�s�Gī�p���a�H�A�]�n�b����l�}�s�D�o���|�n�Q���w�M�i�R�¡C�m���a���U�n���@�̧��H��ı�o�o���n���M�����A��i�R�¬O�@�ػ~�ѩM�������A�L�{���m��P�١n���G�ƨä��O���_�Gī�p�C���m�p�G�ڻ��b�q�v�m��A�١n�W�M�e�����g�L�A�N���|���H�U�Ʊ��o�͡C���@�@�Ʊ��i�H�W���o��50�~�N��A���N�b�q�H����i�R�����F�@�ӬG�ơA�Φo�b�m���M�O�n�Ǥ������k�N�O�G���o�T�Ӥp�G�Ƴ����ϧھ_�ʡA�]�ӥ̤ߤ@�M�M��g�o��Ǧ~�C��1983�~�A���N�b��������L�m��P�١n�G�ƪ��Ӿ��G���D�����M���s���ΪۡA���ɭԿP�ʦ��@�Ǥj�ǥ͡B���ǥ͡A�R��o���o�F�A�ۤv��´�@��Cell�]���^�A�]�S���g��A�]�S���g��A�N���t�u�@�A�a�����O�j�ַݡC�䤤�@�ӬO�]�s��l�]���w�A��ӧڦb����I���L�C�L�O�@���Y�l�A�M��L�̦b�_�ʡB�Ѭz�����Ѥ@�s�}�j�����F�n�X�Ӻ~���A�U�譱�@�d���U�A����]���O�G�x�Τ]���O�A���Τ]���O�A����ҦU�譱�����O�C�ӥB�S�ȦU�譱���q���C��������double-agent(�϶���)�C�饻�H�B�˧L���B���ΡB�x�ΡK�K�j�a�@�d�A�������O�ַd���C��ӡA�N���H�����D���f�W�����x�Ϊ��u�A�N���o�ǤH��´�_�ӡA�@����´�_�ӴN���϶��Ҫ��D�F�A�_�O���X�ӤH�Q�e�h�F�C���@�@���N�b1977�~���H����O�ٰv�I�K�a��i�R�»��A�k�D�����藍��O����ҬF�����ίS�ȡC���N�{���A�@�ӧܤ�k���Ҩƨ��{�Y�X��ۤv�H�A�@��Ū�̤��|�����A�ר����ɪ��O�W����ҬF���ӻ��A�L�̪��S�ȵ��藍�|�ܸ`�C�Y�o�˼g�A�f��֩w�q���L�C���ɻO�W�i�O�i�R�³̤j�������C�_�O�L��ij�A�@�w�n��k�D���g�����@�Ӵ��q�H���S�Ȧw�ơA�ӥh����@��S�O�����ȡA�Ʀܥi�H���s�~���O���C�@�@�̫�O�i�R�¦ۤv�Q�q�F�G���n�j�ǾE���A���o��@�s�R��ǥ͡A�@�ѥѤ@�Ӥk�ͥX���h�����@�W�j�~���C�]���o�O�H�ְ������h�ĤޥL�A�ҥH���o��@�ӦP�٪��k�͵o�ͩ����Y�C���G�j�~���b����`�~²�X�A�o�ڥ��L�k����C�oı�o�P�٪��k�ͦ��F�o�K�y�A�ӥB�]���O�o���w���H�A�ϦӦ]�����ǦP�Ǧn���ݤ��_�o�A�ҥH���I���e�}���Pı�C���F�o�߲z�I���A�o�ӨS���L�@�����k�Ĥl�A���p�ۡB�٫�����·¶�ӮI�U�C�ï]����ܫ�A�o�@�s�H�Ӻ���ǡA�P�@�Ӱ���Ҧa�U�u�@�̷f�W�F�u�C�a�U�u�@�̬ݥL�����M�S���L�V�m�A�����_�Q���g��A���Lı�o�L�̤ӹ�A�N�u���F�@�H�ѻP�����C�Ʊѫ�L���\��k�A�Ӿǥs��h�Q�@�����ɡC�o�ӬG�Ʀ����@�I���Gī�p�ƥ�H�ҥH���Ϊۮڥ����i��O�Gī�p�C���q�v�W�M��A�]���Ӧh�H�������v�A�����i�R�¶C�����ڤk�^�����A�ڥu�n���}��M�m��A�١n�G�ƪ��Ӿ��A�����ִC��̵M�~����i�U�i�A�O�����V�ǶV���C�o���_�ǡC�p�G�A�O�Z���s��A�n�l��Ū�̲��y�A�A�{���H�U��Ӽ��D���@�Ӹ��m���O�H�O���i�R�»P���N����ǰQ�����O�A�٬O���~���d�i�R�¦ý����ڭ^���Gī�p���H�����N���C�@�@��ꦭ�b1978�~�A�i�R�´N�g�F�m�Ϥ�X�b�Ϩ��W�n�@�嬰�ۤv���G�ա��A�ϻ���ɪ����פ峹�m���Y�������J�o�X���l�H�X�X���զ�A�١֡n�A�}�Y�K���D���ڳ̤��|�G�סA�S�g�o�C�A��b�ä��X�ɶ��ӥ������x�q�C��~�H�o�g�ѵ��A���@�������סAŪ�̥������D�q�g���w���|�A���N�ε����A���H�o�j�����ѻP���Q���M�ա��G�@�譱�S�@�A�n�������@�O�ڿ��|�F�N���A�ۤv�w�d�h�B�A�i�H�k���_�~�ѡA�N�i�H���ܧ������t�d�C�ڨ쩳��ۤv���@�~���ण�t�d�A�ҥH�u�n�g�F�o�g�u��A�U�����ҡC��
�@�@�m�ۨ��w�n�l�צ����M��H�@�@�i�R�ª��u�g�p���m�ۨ��w�n�A��Z�_1978�~�m�ӫa�n���ӡA�o�O�@�������M�誺�@�~�A���ܫ�Ӥ]���ܦh�i�g�A��_�i�R�ª��孷���ܷP�줣�ѡC�Ҧp����@�a��ζ��m�ۨ��w�n�S�����F�Aı�o��g�p����U�E�r���O���~���k�����H��աA�@�I�G�Ʃʤ]�S���A�s�o���ݤ��U�h�A���ȥu�����N�ѥ����٬O�Y����A�⧺�N���o�F�i�h�A�]���i�R��ı�o�ܩ�p�C�R�·��ɻ��L�̫뤣�o�o���I�����A�K�o�}�a�ζH�A�i������H��Ѫ��[���ӳ��¡C��ΤϹ�o�_�X�A�G���@�ɭ��ݤ_���W7�B8�I�����Ӷ��A�o�O���ܪ��w�ߡ��C�@�@���H�Ԧb�m���a���U�n�����m�ۨ��w�n�G�@�A�L���X��γo�g�u����R���ۿ��~�A�̩��㪺�O��m�ۨ��w�n�����Ϊ����ۦW�¤p���m���@�ýt�n�~���q�v�A���T��O�L���̵L�ȡC�����䪺�ڧJ�]�b2010�~�g�u���g��m�ۨ��w�n�G���i�����谾���ӥX���^���骺�@�A�H���AŪ�̱ФH�S���S�ġC���@�@�i�R�¦b�m�����ӫ��Ψ�L�n�@�夤�A���N�ܦ��}���a���X�@��Ū�̬ݤ����m�ۨ��w�n����]�G���]�p���^�X�ӤH�@�ӭӤߨ������Ӥp���C�s�b�A�ɺެݤ������A�u�����_�I�ϡA�ä����L�k�h�������`�즺�ǡ����¤���L�Pı���A�o�عj�ҡA�ڷQ�ѨӤw�[�C�ڳo���L�O�ө�H�����աA���O���N�b���~�����@���K�U�����DzΤ]�O���ǤF�A�ڭ̤��ߺD�ݦr���涡�����_�峹�C�ӱq�t�@�譱���ӡA���_�峹�ä��O�����C��
�@�@�m�W���i�~�n�O�m�B������n����Z�H�@�@�b�i�R�ª��@�������ǰO���A�����ιL�i�R�¦b�G�Q�@�����Q�~�N�w�g�n���ηdzƼg���T�g�^��p���A�B�O�U���D�A���O�O�GBridge of FilialP iety�FCorpseD river�MThe Shanghai Loafer�A���O���g�εu�g�C�mTheShanghai Loafer�n���G�O�T�g���̦��W���AShanghai�N�O�W���ALoafer�b�^�娽�i���������i�H���Ρ��i�оc���C�i�R�ª��ǰO�@�̭̤w�g���X�Ӥ���Ķ�W�A�p�m�W���C���H�n�B�m�W�����H�n�B�m�W���լۤH�n���C�@�@���W���i�~����M�OThe Shanghai Loafer����Ķ�A�ڧکҪ��A�o�]�O�i�R�°ߤ@�@���V�ڪ�������o�g�p���C�䦸�A�o�����եզa���A�o���ҥH��o�G�ƺ٬����W���i�~���A�O�]���o�����L�O���F���ܥ��ӥu�O�@�ӤH�a���G�ơC�����H�ԬO�o�˲z�Ѫ��C�@�@1983�~1��A�i�R�¦b�m���M�O�n�Ǥ����G�����T�g��@�]���O�@�E���s�~���g���A���L�����g������g�A�m�ۨ��w�n�P�m��A�١n�o����S�ٲK��h�B�C�m�B������n�̫�@���j��A�~�ѥΪ��|�p�����k�A�D�����N�u�g�p�������A�O�@�ӹ���C�o�T�Ӥp�G�Ƴ����g�ϧھ_�ʡA�]�ӥ̤ߤ@�M�M��g�o��Ǧ~�A�Ʀܤ_�Q�_�ӥu�Q��̪���o���ƪ���ߡA�P��g�����{�A�@�I����ı�o�䶡�T�Q�~���ɶ��L�h�F�C�R�N�O���ݭȱo���ȱo�C���@�@�m�W���i�~�n�N�O�m�B������n����Z�H�m��A�١n�sT heSpyring(�iĶ���m���Ҥ��٫��n�Ρm���Ұ�n)�A�m�ۨ��w�n�sVisiting(�iĶ���m���X�n)�A���^��W�ٳ��ܾa�СA���m�B������n�MTheShanghai Loafer�o�ӦW�r��b�f���W��H���ڥu��i�D�A�A�m�ۨ��w�n���Ӥ]���s���ۨ��w�����A�i�R�¤@���٥��������ƪ��h�֡��A��V isiting�]�ۥh�ƻ��C1978�~�A�o�g�H���������G���m���ƪ��h�֡n�D�سQ�������ΤF�h�F�A�t�Q�F�ӡm���°O�n�ӽE�A�m���������n��preten-tious(���@)�F�ǡA���O���U�����D�D�C���i���m�ۨ��w�n�����٦��n�X�ӦW�r�A�o�����A��b�]�Q���X���������p�C�J�M�m�B������n���Q�o��������g���A�����i��N�O�m�W���i�~�n�ܡH�ڻ{�������i��C���@�@�ݹL�m�B�n��Ū�̤]���D�A�G�ƬO�q���s�����g���A���B����������N����M�O���}�y���m�����s�A�]���G�Ƥ����@���k�l�A�p�S�g�M�^�L�H���饻�ӤӡA�i�H���m�B�n�����ߥD�D�O���s�k�H���R�B�A���O���W���i�~���C���o�O�i�R�¤ܦh�~���𦸧�g�Ӧ��������A���O�̪쪺�����C�m�B�n���g�o�̦h�̥ΤO���k���N�O��x�A�Ӧ�x���O�@�Ӥ��餣�����W���i�~�G�L�d�ǭn�d�l�S�g���U�_�~�A�����r�p�AŪ�F�Q�h�~�~�o�Ǧ�A�^��ᰵ����ͷN�]���ѡA�n�̿�����M�d�l�L���A�d�l�쭻���A�ۤv�d�b�W����Фl�o�椣���A�u�פ�b�R�U�y�s�A�̫ᳺ��ѱC�����𦺡C�m�B�n����x�A�ζH�W���i�~���o�W�r�����ŦX�A�ܥi��N�O�mT h e S h an g h aiLoafer�n���b�ߤH���C�@�@�o���]�]�i�H�ܦ��Ħa����������m�W���i�~�n�M�m�B������n���^��Z���P�ɥ��ܡX�X�X�]���o�⥻�N�O�P�@���I��������|���l�ӭ��H�i�R�¦b1966�~12��30��P��L�ӲM�G���ڷh�ӷh�h�����ƤӦh�A����g�S�o�����u�g�p���Z�l���F�C���O����g�O�H���o�Ӫ��A���Z�l�_�i�R�¦Ө��T�ꥭ�`���L�C�@�@���m�W���i�~�n�q�Q�A���ȬO���H�Y���ҩ����A���D�i��쥦���^���Z�a�C���ܤ֨��O�i�H�۶�仡���A�]�ܦ������O�C�m�W���i�~�n�o���Ѷǻ��F�o��h�~�A�ӡm�B������n�]������ı�ݥ@�F�T�Q�~�A�o�n���S������H�q��o��̪����Y�C�p�G�ڪ��q�Q�S���A�mT heShanghai Loafer�n��ꦭ�w����@���A�u�O�j�a���{���X�o�졥���ӡC�����H�Ԧb�m���a���U�n���g�D�C
�@�@�i�R�¨S���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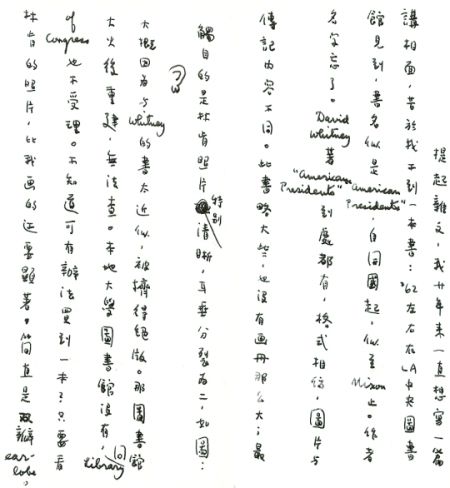
�@�@1990�~2��15��i�R�P���N�H�A�ͤηQ�g�@�g�ۭͬ����峹 �i�R�¦��L���ֺc��n���S���g�n���@�~�A�u�Oť�L���H�ܤ֡C�o���i�D���H�ԷQ�gĬ�C�M�o�p�����G�ơA�O�@�ӦW���maroma port�n�����g�A(�ڭ�����)���G�]�S���g�C�@�@�i�R���ٷQ�L�g�@�g�W���m�T�_�ӺʾG�M�U��v�n���p���A�i�R�ºc��o���D���A���}�F�ڭ̹�o���DzηQ�H�A���̲צo�٬O���F�o���ѡA�o�b�P���N�a�q�H�����졧�G�M�p���]���S���^���H�]�ܤּڬw�H�^���D�����@�A�ڻ{������Ū�̤��|�����쪺�A�u�����v�p���S�B�n�A�����S�u�{�E�j�A���Ȥ@�աC�����ھڱ����A�i�R�«ܥi��Q��G�Ƨ�s���q�v�@���C�@�@1985�~10��A�i�R�¼g�H�����N���Q�g�@�g�m������ӽ͡n��b�m�n�o���A�ثe�S�u�ҥu�n�������h�F�C���N�^�_�D���m������ӽ͡n�D�ط���m�A���g�_�ӷ����e���C���L�g�X����i�H�]silence�^�����Ҧ������ѡ��p�y���C���i�����D��i�R�ª��x�Z���G�F��a���šA���G�o�g��S���g���A�Ӧo�ܥi�ର�F�����D�A�N�s�m�n���Ǥ]�L�v�U�ΡC�ڪL���P���A�o��1984�~8���1988�~3��A�X�G�C�P���h�@���a�C���F���D���D�@���L�۬y���E�p����l�A�٫��M�`�g�@�H�o����g�m������ӽ͡n�A���G�o�O������Ӥ��͡��A�Q���ب�C���ѱo�Q�_�m�Ѥ~�ڡn�����y�W���G���i�O�ڤ@�Ѥ���J�A�o�ثr←ʪ��p�дo�A�ͩR�O�@ŧ�ج����T�A�����F��l�C���@�@���R��R�B���F�P���������Ʊ��@���O�i�R�·P���쪺�A�m���m�O�n�M�m��k�n���N���@�j�q�g��R���A1937�~�t���Q�Ȥk�ծեZ�m��Ħ�n�A�i�R�§⺩�e�M�u�H�Ӥ����X�A��ۤv�e�������y���Ťk�A�S�e�F�o�۷Q�����U�ӦP�Ǫ����ӡC�i�R�¦ۤv�`�ɧ��N�a�����Pñ�Ѧ��R�A�m�i�R�¨p�y���n������Medium(�q�F��)�X�X�q�e�JXX�N���ڼg���F�补�����𡦡C�ڪ��T���@�ؤ~��A��G�šA����w�P�Ʊ��N�p��o�i�C��ı�o���\���@�w�|���\�C��1990�~�A�i�R�¹狀�N���A�Q�G�~�Ӥ@���Q�g�@�g���ۭ����ѡA�b�����F�����Ϯ��]���쪺�m�����`�ΦC�ǡn�A���̲ʥت��O�L�ַӤ��S�O�M���A�ի��������G�C�]���䤣��ѦҸ�ơA�峹�����m�F�C1989�~12��11��A�i�R�¼g�H�����H�����G���ڷQ�g�g�������_�F���A���_�����ͳ��Ӥӧi�D�L���٦w�f�o���ɪ�telepathy�C�������ͫ����@���A�٦w�N�O�L�٦w�A�L�b1965�~2��]���������@�CTelepathy�O�����F�P�����A���@���Ұ����_���g��A�i���_���@�����m�L�٦w���ͫs�L�ǡn�C�����F�����o�g����A�i�R�¨S����ڪ������_�A���̦o�g�����H�������y�ܥi���A�ҿס��F�������O�������U FO�A�ӬO�����w�P���B�����F�P�����������{�H�C�o�ߦ~�g���ڪ������H�A�|���M���κa��]Carl Jung�^�A�ƦܰQ��ë�\�ġA�o�Ǹ��D���ŦX�o�����Ťk�����A�]����F�P�������C�@�@1980�~6��7��A�i�R�¥���H��묰�D�A�g�@�g�s�m�¹��n���p���A���@��X��������@�@�a�A�b����j�Ǫ������s�|�A�^�а_�ԫ�W���q�v���q�����b�A�Ψ�Ӭ���ӹ���C�̫�i�R�¤]�S���g�A��]�q�o1988�~�o�ʫH���i�H�q��G���m�¹��n�p�����D�n���e�O���party�]����^�A�ԫ�W���q�v���q�w����q���y�^�ӡA�[�j�t�m�p�B�n�᪺�����s�|�C�L���p�ͬ��ڨ��@�L�Ҫ��A�����r���A���F�����R�ضR��Ƴo�ơC���i�R�ª��g�@�A�D�`���Y�A�b�ʵ����e�A�`�n�A�T��ҡA��C�Ө��ⳣ�Q�o�M�M�����A�s�����髬�����F���T���������A�~�ۤ�y�g�C�J�M���뤣���x�A�o�K�F�ܤ��g�C�@�@�i�R�¦b�W���t���Q�Ȥk�դ��Dz��~�A�Ǯզ~�Z�m��Ħ�n���Z�n�F�@�i�լd���A�ѷ��~�����~�Ͷ�g�ۤv�̳��w����A�̫뤰���C�i�R�ª����ש����X�H�N���A�D�`���ʮ�A�i�R�º٥������R�������C�o���R�������S�����J�i�R�ª��嶰�A�]�S�h�֤H�ݹL�A����W�@��90�~�N��A�~�Q���l���o���X�ӵo���A�i���S���g���C80�~�N���A�i�R���ٴ�����g�@���g�p���m���k�l�n�A��P���N�G�H���ӤF8�ʫH�A�ӰQ�@�DZ��`�A���p�N�p���~���m��P�١n�A�u�O�o���èS�g���C�@�@
�@�@�]���e��ƨӦۡm���a���U�n ���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