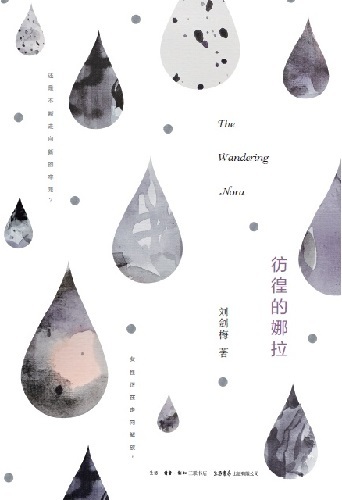
1879年,易卜生《玩偶之家》首演,“娜拉出走時的摔門聲”驚動了整個歐洲。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演講,發聲一問,“娜拉走後怎樣?”
1962年,銀幕上的李雙雙,為自己爭取在家庭和社會的平等權利。
21世紀第二個十年過半,中國女性的身、心、靈,是否已收獲安頓?
繼前一本散文集《狂歡的女神》後,時隔八年,劉劍梅再次結集女性主義思考的續篇《彷徨的娜拉》近日由三聯生活書店出版。劉再復先生特地為該書作序,評價這部作品依然是在“用女性視角觀察社會、觀察人生,為女性說話、為女性請命”。
將新書命名為《彷徨的娜拉》,顯然是與前作對應。相較于《狂歡的女神》呈現出的浪漫與激情,《彷徨的娜拉》傾向于哈姆雷特特型,直面現實的困境以及人生的種種無奈。兩部作品創作之間,作者由青年步入中年,從狂歡到彷徨,從浪漫到現實。作者以女性主義立場,審視、反思兩個主題: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定義,以及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中,女性種種身份的撕扯。
書中,劉劍梅拋出實質性提問:當下中國女性生存狀態進步與否?
《彷徨的娜拉》針對國內社會當前的女性生存現象進行了觀察和思考,沉淀出更深層次的關照。與近一個世紀前的婦女解放、走出家庭相對立,當今社會的女性更多“掉過頭來,轉回家去,重新進入男人的‘樊籠’,追逐男人所設置的銅牆鐵壁”。拋棄女性的獨立與尊嚴,依附于“安樂窩”,“嚴重缺乏主體性”。有家庭的事業女性更是陷入社會義務和家庭義務的雙重壓力之中。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益發嚴苛,而這種困局恐將一直持續下去。相比“狂歡”的瞬間,“彷徨”更是生活的常態。
在序言中,劉劍梅說自己迷戀“翅膀”的意象,她引用馬爾克斯的短篇小說《巨翅老人》:老態龍鐘的天使擁有一副翅膀,被眾人視作怪物,故事的末尾,他還是飛離了這個不值得留念的,充滿欲念的人間。有評論認為,羽毛殘破的翅膀,就如同女性主體性的隱喻,它必然伴隨著世俗的困惑、現實的羈絆,如張愛玲所言“咬噬性”的苦惱。
近日,在北京三聯生活書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劉劍梅與作家閻連科、梁鴻就共同探討“女性精神獨立”這一話題。
“這是一本男性看了會刺痛的書,它會讓你正視自己在生活中是否真正尊重身邊的妻子、母親等女性”,閻連科接連拋出反思,“為什麼中國的男性作家不能清晰得認識到筆下人物的性別?為什麼他們筆下的女性永遠是男性的附庸,永遠處于被動的位置。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角色,檢討自己的文學了。”梁鴻對此亦有同感,她認為很多作品中男性作家把女性描繪很美很純,但這並未提升女性的心靈和形象,而是把女性簡單物化。
對于女性在這個社會“精神獨立”的艱難,劉劍梅深有感慨,《彷徨的娜拉》更是收錄了她對賈平凹小說《帶燈》呈現的“男權主義傾向”的批評,她直言“讀後真的感到絕望,為優秀女性心靈遠處存放而絕望,為千百年來的男性崇拜傳統如此根深蒂固而絕望”,在《帶燈》描述的男權烏托邦里,想改變現實世界的女英雄只能是男性門後桌前的“小貓、小狗”,再有本事也跳不出男權的五指山。
閻連科認為這其實是“文學性大于女性”還是“女性大于文學性”的問題,但根本的原因是“在生存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在文學中談論男性、女性是不予考慮的,而中國的大部分作家還沒能跳脫出‘生存問題’的寫作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