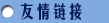《失落的一代》

1973年3月,哈爾濱的知青下鄉運動。李振盛 攝

《失落的一代》,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版,45.00元。

潘鳴嘯
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1977年出版了《上山下鄉:中國的知青運動》一書,他認為知青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這一觀點曾引起很大反響。近日,法國學者潘鳴嘯的《失落的一代》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推進了對于知青史的研究。中國知青研究專家劉小萌等對這本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不久前,潘鳴嘯做客北京,記者專訪了他。
潘鳴嘯
原名Mich elBonnin,法國漢學家,在巴黎獲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或中文刊物發表論文。
潘鳴嘯經歷
意外進入知青研究
法國人潘鳴嘯在中國一幫老知青群里頗有人緣,這些老知青們都視他為朋友,叫他“老潘”。有十多年的時間,他每年都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走訪當年的知青。
潘鳴嘯進入知青研究領域完全是一個意外。1973年,他只身一人到香港。當時,潘鳴嘯甚至收集了一些在知青中傳唱的偷渡歌謠。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幾個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知青。西方人都知道紅衛兵,但沒有人聽說過知青是怎麼回事。老潘與這些偷渡者進行了長談。他們講述的讓老潘大為震驚。在一位法國記者的建議下,潘鳴嘯給香港知青們做了一次集體採訪,合作出了一本《20歲在中國》。這就是潘鳴嘯進入知青史研究的“意外”。
上山下鄉,預防與懲治
新京報:在你《失落的一代》出版之前,有關知青的圖書可謂汗牛充棟,你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外國人,跟中國學者做這樣一個研究有什麼不一樣?
潘鳴嘯:可能我問的問題就不是完全一樣的。我不只是關心這個運動,而且要從這個運動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至少是毛澤東最後10年的中國。而且,我也想了解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怎麼轉到改革開放的中國,所以我特別注重1978年到1980年間的回城風。
我在調查和研究中發現,本來知青未被允許一下子回城,1978年10月份到12月份,有一個很長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談這個問題,會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後來,他們決定,這個運動會結束,可是要有程序,慢慢結束而不會一下子結束。當時有插隊知青和農場知青,插隊知青在農村,要靠自己的工分來吃飯,農場的知青是每個月發工資,雖然工資不高,可是至少他們可以吃飽飯。所以,那次會議決定,農場的知青不回城,以後以職工的名義留在那里。這些知青聽到後非常不高興,覺得他們沒有希望了,所以鬧得比較厲害。有很多所謂的群體的行動,他們罷工,絕食……有一些人到北京去請求。
後來,政府覺得,如果要強迫、強制性地延續知青運動的政策,不會有好結果,所以他們就準許知青一下子回城。由此引發了較大的失業問題,可是他們當時覺得,還是盡快解決這個問題較好。類似這樣的視角,中國學者關注的力度不一定有我大。
新京報:你在書中說過,讓知青上山下鄉“具有預防及懲治的功能”,具體來說,預防的是什麼?
潘鳴嘯:從1966年中到1968年,“文革”開始,中國非常亂。可是,不可以長期的亂下去,不然一個社會不能生存。到1968年,毛澤東可能已經完全了解,一定要恢復秩序,要不然就沒辦法了。
恢復秩序就不可能讓紅衛兵繼續鬥爭。最大的麻煩在于,1968年的紅衛兵組織,都說代表毛澤東思想,認為對方是叛徒,是修正主義者,我們才是好的毛澤東的學生。他們互鬥非常厲害,很多人死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全部的知青解散到廣大的中國農村。
新京報:那麼什麼是“懲治的功能”?
潘鳴嘯:就是我剛才說的,他對那些紅衛兵有一點不滿,他覺得他們沒有完全按照他的話做事,他們繼續鬧武鬥。而且他覺得,從1949年到1966年的教育制度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這批年輕人是被毒害了,應該再教育。所以毛澤東說,知青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所以,知青下鄉有一種懲罰的意思。
那個時候,很多知識青年,特別是當過造反派的那些紅衛兵,就感覺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否認。這一點,也可以跟“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做連接,“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從1962年到1966年,基本上是把出身不好,有家庭問題的人趕到別的地方,也是屬于再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所以,有一些知青覺得這政策是對自己的懲罰。
“三大差別”並未縮小
新京報:你在本書中揭示,毛澤東試圖通過上山下鄉運動縮小“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三大差別,請具體談談?
潘鳴嘯:當時一邊倒學蘇聯,也是蘇聯專家來幫助中國發展。這個發展模式對農民不利,要犧牲農民來搞工業現代化。就當時的情況來說,要縮小三大差別很空洞。因為你把城市的知青派到農村,能解決城市和農村平等的問題嗎?你只是把有一點特權的一部分人扔到一個沒有特權的地方,可是農村的勞動力本來已經太多了,這種做法反而增加了農村的負擔。實踐的結果,並沒有實現理想目標。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上山下鄉”也使農民和知青更加了解當一個城市人的好處。
潘鳴嘯:這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是很多知青、農民跟我講到的。本來很多農民從來沒有進過城,知青使他們知道了城市。法國有一個知青作家叫戴思傑,他寫了一本《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還拍了電影。里面寫到,一個男知青跟一個女青年農民產生了愛情,那個女青年農民很羨慕城市,後來她跑到城市去了。
而那些知青到農村以後,他們發現體力勞動很艱苦,農村沒有什麼文化活動,精神上也會覺得很痛苦,所以還是會覺得城市好。所以,上山下鄉運動根本沒有縮小三大差別,反而讓知青和農民更加了解差別所在。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把城市的人口送到農村,只有農村的人口為了過更好的日子到城市,這是一個歷史的現象,你不能反對———所以很多知青都說,上山下鄉是把歷史的輪子倒過來了。
新京報:你的書里寫了很多知青典型,這些典型是否真正起了帶動作用?
潘鳴嘯:我書里提到過一個我認識的知青,他出身很好,父親是高級幹部,到鄉下後被當成知青模范。那些幹部對他說,你要說你要一輩子扎根在農村,如果你以後經常說這樣的話,是會帶動其他的知青的。如果你起到了這個作用,你不用擔心,以後你很快會回城的。他說,自己那個時候拒絕這麼說,因為他覺得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說,如果自己拼命說要扎根,一年以後第一個回城,那其他的知青會怎麼想?結果必然是對什麼都不信。
事實上,這些知青模范對其他的知青沒有太多的正面帶動作用。只是在開始,動員知青下鄉的時候有一點作用,那個時候學校和街道幹部合作,動員知青:你們學校的比較好的學生他第一個報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你怎麼辦?這種說法是一種壓力。
反思“烏托邦”
新京報:學者吳思的自述中說,上山下鄉後,他非常積極,但是發現事與願違,後來就開始反思。食指、北島的詩也是從“文革”開始創作的,是否可以說,上山下鄉這個運動推動了知青對于現實的思考?
潘鳴嘯:我完全同意。這個運動對這一代人思想的推動影響很大。比方說,北島寫的最有名的一句詩就是:我—不—相—信!北島沒有當過知青,可他的朋友都是知青。他經常去找白洋淀的芒克,他們都一起討論、反思。後來,在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四五運動”,參加的大部分人都是知青。上山下鄉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我在1979年就來中國做商業翻譯,天天跑到西單看大字報,覺得很有意思。我跟知青們談話,他們說我們反思了,我們不可能再有一個“文革”了,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應該有民主、法治。因此,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有一種連接,新一代和老一代的改革派連接在一起了。
新京報:對青年實行改造的結果如何?
潘鳴嘯:我覺得完全失敗了。知青到了農村,沒有變成雷鋒,反而變得非常現實,學會了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因為他們的情況太艱苦,一定要成功回城。如果需要討好幹部,有時候也得說一些另外的知青的壞話,這樣做是沒辦法,要不然回不了城。烏托邦太不實際,知青們就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所以我的書在扉頁上用了舒婷的一首詩《一代人的呼聲》。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最成功的就是農村政策,解決了農村最基本的問題。因為很多年輕知識分子都當過知青,非常了解農村,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因為那些知青在那待了幾年,他們完全了解農民想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