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三十年·講述】阿剨的守望
【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係緩和、改善與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歷的真實故事,續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本文導讀】1949年,一場時代悲劇演繹了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的傷痛。1987年海峽兩岸打破隔絕,不斷交流、發展、融合,至今。雖然有的人終于還是沒能在1987年後回到故土,更沒能見到朝思暮想的親人、朋友,就像本文作者的阿剨,再怎麼癡癡等待,兒子終究還是沒能從臺灣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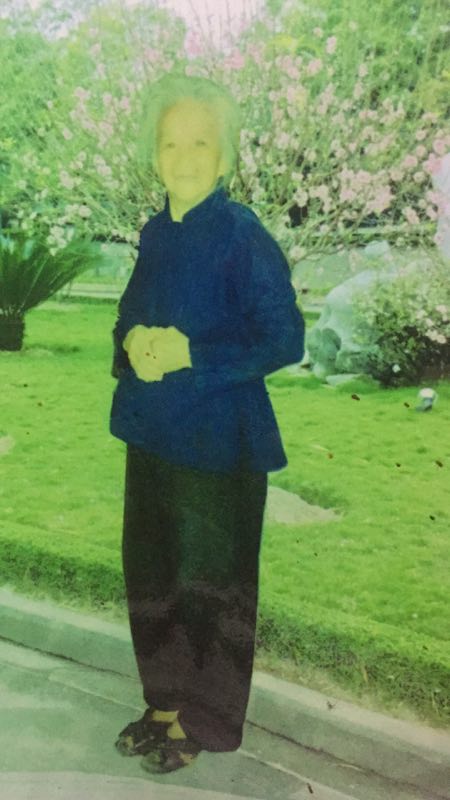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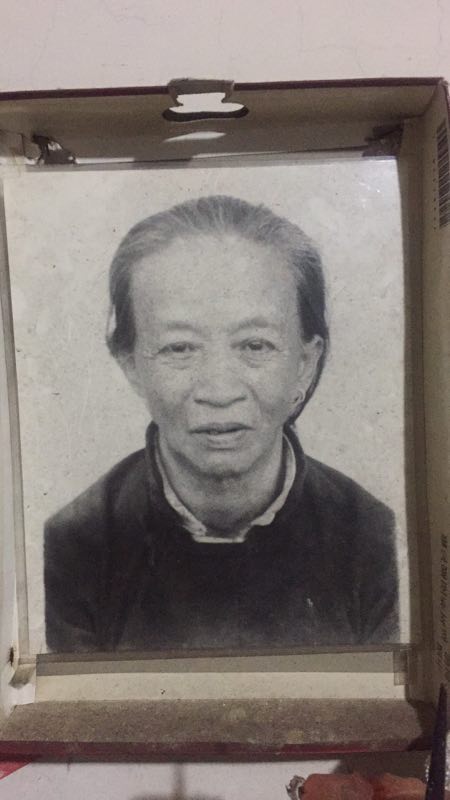
本文作者的阿剨。(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鄭偉,福建
自我懂事起,就常常看見阿剨獨自呆立家門前望著路口,倣佛在癡盼著什麼。
“阿剨,你在幹什麼呢?”
“我在等抗抗。”
“抗抗是誰?”
“是你的伯伯。”
“我? 還有伯伯?您不是只生我爸一個嗎?”我很詫異。
“你爸還有一個哥哥,在臺灣!”阿剨很堅定。
我的好奇心驅使著阿剨打開記憶的閘門,把我帶到那兵荒馬亂,生離死別的舊時代……
一九四二年初冬的一個清早,小雨淅淅瀝瀝下著。在埔埕街一間木工店里,鄭抗抗從母親的懷里接過一周歲的弟弟,抱在胸前,深情地凝視,撫摸著他的頭,低聲說:“阿弟,哥要走了,不能再來抱你了。”
“你要去哪里?”媽媽警覺地問。
“小日本太猖狂,福州也淪陷了,保長、甲長昨天到後詊老家叫我去當兵打鬼子。”抗抗頓了頓說:“今天就是來向你們告別的,一會兒就出發。”
“打鬼子可以,可不能去打自己人。”爸爸聞聲從里屋出來,一臉嚴肅地叮囑道。
“不會的,打完鬼子,我就回來”,抗抗邊把弟弟遞給媽媽邊說,“爸,媽,我走了啊。多保重,別擔心。”
“等下,吃碗面再走。”媽媽叫住抗抗,轉身進入灶房。
抗抗停下腳步,坐在了門檻上,看著埔埕街上為著生計奔忙的人們來來往往。
埔埕街坐落在大樟溪畔,與溪流平行,街道兩旁共有十八條石巷。巷道路面和邊牆均由鵝卵石壘成,寬窄不一,長短各異,細長而幽深,且縱橫交錯,巷巷相通,若無人引路,外來人是斷然繞不出來的。
抗抗不時和路過的熟人打招呼——就要離開這里了,對這熟悉的街巷和鄉親,多少生出了幾分不舍……
“面好了。”母親端著滿滿的一碗又細又長的太平面。抗抗收拾好飄遠的思緒,有滋有味地吃了起來。臨走之前,母親又給他褲袋塞進兩個剛剛從鍋里撈上來並且用紅紙染紅的鴨蛋。那紅蛋滾燙滾燙的感覺,在那寒冷的冬天里,給抗抗平添了幾許溫暖。
雨絲仍在不絕如縷的飄著,年僅十八歲的抗抗帶著母親的祝願,也帶著對父親的承諾,踏上石板路出發了。
小阿弟似乎感應到什麼,“哇哇”地啼哭起來。這哭聲打破了埔埕街的寧靜,也擾亂了家人的心。
爸媽送到路口,一路走,一路叮嚀,直至兒子的背影消失在視線里,這才默默轉身,回到店里時淚水早已打濕了面龐……
聽說,後來抗抗所在的部隊打退了日軍,再後來又被國民黨逼著去剿“赤匪”,最後隨著“國軍”潰退到了臺灣。那時候,阿剨還曾怒氣衝衝地追到保長家,斥責他們說話不算數!保長們用無言以對兌換給阿剨無可奈何。
阿剨一打開話匣子就收不住話題,略顯絮叨的話語間總會夾雜著幾聲嘆息。她看了看我,說:“‘小阿弟’就是你爸。你爺爺死得早,木工店只好關了門。生活突然沒了依靠,過得很是艱難。一直熬到你爸長大有了工作,日子才慢慢有了好轉。”
改革開放後,阿剨過上了四代同堂的生活,本可以盡享天倫之樂、頤養天年,可是她仍強烈希望有生之年能找到抗抗,而且隨著年紀越來越大,這種心願也越來越迫切。
由于兩地疏隔,“國軍”老兵去臺後杳無音信,抗抗亦然。
一天,不知道阿剨從哪里得來一個消息,說有個“神婆”非常靈驗,便尋上門去。只見那“神婆”伏案約半個時辰,突然搖頭晃腦,喃喃自語。飽受骨肉分離之苦的阿剨,早已耐不住性子,急切地問:“我的抗抗現在怎麼樣,啥時候能回來?”“神婆”忽悠道:“抗抗活著,只是被荊棘包圍著,一時回不來。”阿剨驚喜萬分,趕緊從兜里掏出十元給付“花紙錢”以表謝意——那時候,這相當于半月的生活費。
自此,阿剨認定她的抗抗還活著,每天一閒下來便會站在路口,面朝臺灣,恨不得一眼望穿海峽。
延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終于從海峽東岸傳來喜訊,臺灣那邊同意逐漸開放大陸去臺老兵回鄉探親。許多老兵跨越重重障礙陸續回到大陸探親、訪祖、尋根,然而這其間卻總不見抗抗的身影。等啊、盼啊,阿剨急了,見到蚌頭厝李家兄弟繞道香港回來,就上李家打聽抗抗的消息;聽說井里厝林家兒子還在回家的路上,就急切地想到林家打探抗抗的下落……
這些老兵被她的思子之切所感動,都答應返臺後幫忙尋找。他們從臺南找到臺北,從平地找到後山,從眷村找到福州同鄉會……找遍了抗抗可能落腳的地方,遺憾的是都沒有他的蹤跡。
“莫非……”消息傳來,阿剨不敢往下想,她選擇性地相信“神婆“的話,可慌亂的神情卻掩飾不了內心的憂慮。她時不時地念叨著:“我的抗抗啊,你怎麼那麼傻,人家一個個都懂得撥開‘荊棘’跑出來,你怎麼還困在里面呢!”那模樣著實讓人揪心。
家人都擔心若這樣下去阿剨終究會生出病來,得想一個法子安慰安慰老人!阿剨不識字,聽力也不好,而且從沒用過電話,于是我想了個法子 “對症下藥”——我趴在她耳邊大聲喊道:“阿剨,抗抗伯從臺灣打電話給你啦!”
“真的?”她喜出望外,緊緊抓住我遞給她的話筒貼在耳朵上。可憐的阿剨,對著根本就沒有接通的電話,用濃濃的福州方言說了很久很久——“抗抗啊,你怎麼都不回來看媽呀,隔壁家去臺灣的人都回來啦,你怎麼那麼狠心?我已經是九十三歲的人了,吃不了多久……五十幾年沒見面,你都不想我嗎……”不管抗抗有沒有聽到、有沒有回應,她把這幾十年來積壓的思念和埋怨一股腦兒地都扔給了話筒,而後才滿足地放下電話。此刻,阿剨的心情顯得格外舒暢。
第二天,阿剨早早起床,飯後拄著拐杖,來到大門外的矮牆邊,坐在石板凳上,望著村口的方向,逢人就說她的抗抗還活著,不久就會回來看她。那高興勁兒哦,溢于言表。
此後,這個石板凳簡直成了阿剨的專屬座位,陪伴她每天的堅守、翹望和等待……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從山花爛漫盼到枝頭挂果,自烈日炎炎望到寒風蕭瑟……阿剨翹首以盼的抗抗始終沒有出現。失望慢慢地爬上了耄耋老人的臉龐,她眼眉低垂,目光呆滯,話也少了許多。多年緊鎖眉頭形成的道道皺紋,與歲月刻下的痕跡混雜在一起,分不清哪一道是“年輪”,哪一道是憂傷。
這一天,阿剨又如往常一般,準備上石板凳等她的兒子,經過一段下坡路時,不慎身體一歪摔倒在水泥路面上。送醫檢查診斷為股骨頭粉碎性骨折,五天後在不舍與不甘中溘然長逝。
夕陽西下,倦鳥歸巢,周圍的青山漸漸趨于寧靜。阿剨就這樣帶著“神婆”的忽悠,帶著孫子的善意謊言,更是帶著對臺灣兒子的深切思念,遺憾地走了。
一向身體很好的她,在這之前從沒上過醫院,一輩子也沒吃過幾顆藥,要是沒有這一跤,活上百歲也不是奢望。
如今,石板凳依舊躺在門前的矮牆邊,可是阿剨已經遠去,而抗抗伯仍然沒有歸來。其實,未歸的豈止是他一個人,還有那塊也許已成為他安身或長眠的土地!
[責任編輯:何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