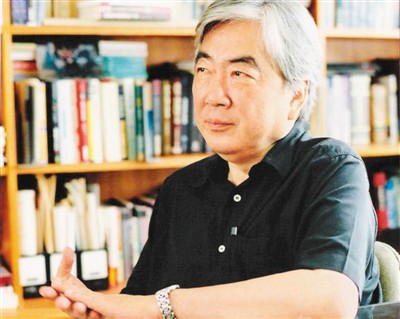
陳映真舊影 陳文發攝
12月1日,兩岸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寶山送別陳映真。其實,很多大陸人不知道他是誰,很多臺灣人已忘記他是誰。
他的文學路從一開始就立足底層民眾立場
陳映真1937年生于臺灣苗栗竹南鎮,本名陳永善。小學時,他從父親書房里找到一本魯迅的《吶喊》。在那個思想禁錮的年代,這本暗紅色封皮的小說集如暗夜中的一道光,陪伴了他的青少年時代,並影響深遠。
1959年,還在上大學的陳永善以陳映真為筆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面攤》,此後他又陸續發表《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將軍族》等。這些早期作品略顯青澀,但已經顯露出陳映真的文學路一開始就超越種族、宗教等藩籬,立足在底層人民的立場上。以《將軍族》為例,講述的是發生在來自大陸的底層老兵和臺灣雛妓之間的感情故事,兩人雖相惜相扶卻抵不過殘酷現實,最終雙雙選擇自殺。
左翼傾向和濃厚的人文關懷,不僅呈現在陳映真的作品中,也貫穿了他的一生。1968年7月,陳映真被以“組織聚讀馬列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等罪名逮捕。7年牢獄生活沒有磨滅他的理想,反而因為與上個世紀50年代被捕的臺灣政治犯同監,結識了那些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讓我知道曾經有一代人抱著高潔的靈魂,為了理想志業而家破人亡的故事”,讓他化繭為蝶,“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的知識分子”。
待到1985年,陳映真抵押了房子創辦《人間》雜志。這本以關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為主題的雜志,創刊號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內湖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鏡頭下那些底層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社會邊緣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響了臺灣整個世代。盡管僅僅存活4年、發行47期就因財務困難而停刊,但有媒體評價說,它“在臺灣雜志史的地位宛如聖典”。
給人希望、尊嚴、安慰和勇氣,他用文學濟世
作家白先勇稱讚陳映真是個極端浪漫的人,“唯有他能直直寫到人心中相當創痛的地方”。固然,陳映真溫和、細膩、不疾不徐的文字具有感染力,但更打動人的應是他自省、謙卑、真摯乃至善良、正直的內心。
對于文學,陳映真的態度從來都是鮮明的。上個世紀70年代,臺灣曾發生一場鄉土文學論戰。作為論戰中的重要角色,陳映真主張文學要來自社會反映社會。2004年他在香港接受訪談時更明言:“寫小說目的很簡單,就是宣傳,宣傳一整代足以譴責眼前犬儒主義世界的一代人。”他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意念先行的作家,是一個文學藝術的功利主義者,甚至公開認為文學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宣傳,“我並不以此為恥,問題是你寫得好不好”。陳映真的功利主義是什麼呢?他曾自言:“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淩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陳映真是用文學來濟世的。學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臺灣的魯迅”。不僅因為他的作品中看得見魯迅的影子,更因為他如魯迅一樣敢于衝破社會禁忌。上世紀80年代,陳映真相繼發表《鈴鐺花》《山路》和《趙南棟》,大膽涉及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在戒嚴時期的臺灣,說錯話是要坐牢的。曾經坐過7年牢、並仍常被某部門叫去問話的陳映真勇敢地挑戰黑幕,以溫和、穩健、真摯的敘述,撼動了尚未解禁的臺灣。
2004年秋,林懷民“雲門舞集”公演了《陳映真·風景》,向陳映真致敬。林懷民說:“在那個時代里面,陳映真的聲音是重要的聲音。”
歷史面前,他選擇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應該走的路
魯迅對陳映真的影響不僅限于文學,陳映真曾說,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從魯迅的作品中,讀到他對中國深切的關懷和熱愛,讓我從小就認定中國是自己的祖國。”陳映真主張臺灣現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在臺灣的延伸和發展,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他撰寫一係列文章揭露“文學臺獨”的荒謬和危害。
1988年,陳映真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那正是李登輝上臺之後,臺灣政局發生巨大變化之時。看到海外“臺獨”組織紛紛回臺,陳映真敏銳的洞察力促使他放下手中的筆,走到反對“臺獨”的第一線——“中國統一聯盟”的宗旨就是促進民族的團結與和平,建立統一的國家,消除兩岸敵對意識,促進兩岸交流。
臺灣作家藍博洲說,當歷史走到陳映真面前時,他選擇了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應該走的路。這是陳映真用一生去實踐的誓言。作為理想主義者,孤獨是必修課。堅守左派立場,陳映真是孤獨的;作為“死不悔改的統一派”,陳映真更是被臺灣某些人批判乃至選擇性遺忘。然而,他的光輝並不因此而減損。
可以說,在當前的兩岸文學界,陳映真是獨一無二的。他為絕食工人寫下感人詩篇、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關愛、積極推動祖國統一事業,他的光輝早已超越文學,光照人間。
[責任編輯:齊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