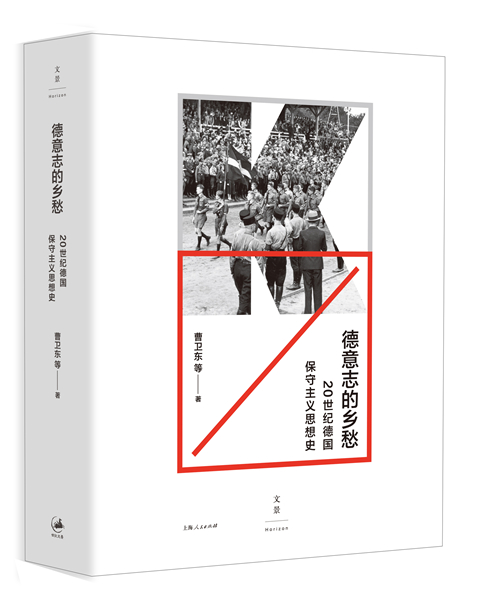
書名:《德意志的鄉愁——20世紀德國保守主義思想史》
著者:曹衛東等
定價:59.00
出版時間:2015年12月
出版社: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書號:978-7-208-13523-9
開本:32開(150*195)
插圖:黑白約60幅
【內容簡介】
20世紀的德國命運多舛。因為“一戰”的失敗,德國人告別了19世紀的黃金時代,受制于戰勝國的盤剝;因為不成熟的魏瑪民主制度,德國國內政治跌宕、危機四起;因為第三帝國的崛起,德意志再次陷入戰爭泥潭,並背負上沉重的道德包袱;因為“冷戰”格局,德國被一分為二,淪為國際政治爭鬥的犧牲品。
多舛的國家命運,並非歷史的偶然,究其根底,以上所有悲劇都反映出作為後發國家的昨日歐洲強國,在面臨現代性的歷史大潮的衝擊之後,所體現出來的應對及其後果。
本書用思想史的手法來細致分析和呈現(有豐富配圖)20世紀德意志思想意識,就化解開了對納粹德國的刻板認識。殘暴的歷史現象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涌動的是民族精神由來已久的推力,相比于納粹政權這個帶有歷史偶然性的結果,民族精神本身要深刻得多。
【作者簡介】
曹衛東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長。
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德國思想史專家。
德國《論證》雜志、香港《社會理論學報》編委,
德國普萊斯納學會學術委員。
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國家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
【目錄】
導 論 德國保守主義:一種現代性話語
第一章 德國青年運動
1. 世紀之交的德意志
2. 青年運動的興衰
3. 青年運動:在理念和意識形態之間
第二章 德國表現主義運動
1. 何為德國表現主義?
2. 表現主義的精神構型及思想史位置
3. 藝術領域的新浪潮:從“橋社”到表現主義文學
4. 特奧多爾 多伊布勒與早期卡爾 施米特
5. 政治與藝術的形而上學: 戈特弗里德 本恩
6. 衰落的寓言:弗蘭茨 卡夫卡
第三章 德國保守主義革命
1. 文化的誘惑:德意志現代化的衝動
2. 保守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與歷史階段
3. 保守主義革命的觀念與思想機制
第四章 技術保守主義
1. 技術保守主義的興起
2. 漢斯 弗萊爾:從工業社會到民族國家的技術轉型
3. 阿諾德 蓋倫:自由與異化的辯證法
4. 赫爾穆特 謝爾斯基:在保守與民主之間
第五章 約阿希姆 里特與新保守主義的現代性方案
1. “零點時刻”、“技術時代”及新保守主義的登場
2. 里特的思想生涯
3. 連續性與非連續性:里特論現代性(1)
4. 市民社會與分解:里特論現代性(2)
5. 代償:里特論現代性(3)
第六章 德國歷史學家之爭
1.“歷史學家之爭”的緣起
2. 論戰的爆發與交鋒: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批判與辯護
3.“歷史學家之爭”的退潮、延續與反思
後 記
【內文選摘】
技術價值之重估: 為民族目標而生
由于對現實的失望,20世紀知識分子多將改造現狀的希望寄托在極權主義政治運動之上。雅各布 塔爾蒙(Jacob Talmon)曾這樣解釋過極權主義:“它最終識別出存在的唯一層面—政治。它將政治的范圍擴寬到涵蓋人類存在的全部。它將人類所有的思想和行動視為具有社會意義的,視為以政治行為為導向的。政治被定義成一種藝術:它應用這種哲學來組織社會,當這種哲學統治生活所有領域時政治的最終目標才能實現。”極權主義借助于全面政治化將社會生活高度組織起來,知識分子正是對極權主義整合社會的力量倍感興趣才被國家社會主義所吸引,直接或間接發言著書表達對希特勒的支持。
在 1927年的復活節集會上,弗萊爾曾做過一次題為“希臘城邦意義”的演說,他將希臘城邦作為理想的典型與魏瑪共和國作對比,尖銳地指出正是魏瑪混亂的時局無法給人們以總體感。他認為個人的意義不是僅靠人自身的力量,而是通過德意志民族特殊的歷史文化獲得的,因此國家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能維護文化傳統的,具有整合力、凝聚力和共同意識的民族共同體。弗萊爾始終強調社會學學科的三大原則:歷史總是在肯定(positive)與批判(critical)、有序(order)與無序(disorder)的時代中循環;現在(弗萊爾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無序的時代;社會學的作用在于揭示無序時代的原因,並在未來創造一個新的肯定時代。 弗萊爾在其著作中一貫“致力于創造一個新的肯定的時代,一個統一的能包容每個人並有助于將他們從文化的碎片和意義的喪失中解放出來的倫理秩序”。弗萊爾在他的著作中大肆宣稱他及其同時代人生活于一個批判的無序的時代,這個時代充斥著現代性危機:社會分裂、文化分化、個人生命無意義。立足于現實,弗萊爾對德國浪漫傳統的態度是極為矛盾的,一方面是對浪漫派強調傳統文化情感上的親近;另一方面又認為浪漫派過于關注內部世界的經驗而不適合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浪漫的空想並不足以改變現實。弗萊爾衝破浪漫派的藩籬,以更激進的姿態要求政治上的變革。很多保守主義者都如弗萊爾,認為傳統保守主義的浪漫派傳統已經不適合于20世紀,“他們在自由資本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一方面是對國家的獨特性持肯定立場的國家主義,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和完全整合的社會”。
1930年夏天納粹選舉成功成為弗萊爾寫作《右派革命》的催化劑。雖然《右派革命》中並未明確出現“國家社會主義”等字樣,弗萊爾也未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此書自1931年發表之日起,就被弗萊爾及其學生理解為是對納粹運動的支援。《右派革命》將魏瑪時代定位為一個批判的、無序的時代,一個應該被否認的時代,而希特勒則能為德國帶來一個肯定的時代,此書無疑加深了人民與魏瑪當局的嫌隙,擴大了納粹運動的影響,它的政治意義也是相當明確的。弗萊爾在《右派革命》不長的序言中指出:國家社會主義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現象—不能用現存的主導當代政治解釋的社會經濟學來說明;它是第一個能抵制住滑入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誘惑的現代運動;是唯一現存的能確實改變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運動。弗萊爾提醒讀者:政治選擇的時候已經來臨,那些長久以來不滿于工業社會和魏瑪政府的人都應該支持納粹運動。
《右派革命》是弗萊爾對工業社會長期思考的結晶,他在其中重點分析了工業社會中國家的作用,認為國家權威因為市場的自由主義而被削弱,它只是作為調節各利益團體的仲裁人而存在,只有當人們生活于一個從工業社會各種利益衝突中解脫出來的國家時,個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從《右派革命》出發,弗萊爾強調政治權力在創造一個具有共同目標的共同體中的作用,認為一個整合的、政治的民族總體只有通過統治(Herrschaft)才能創造和維持。“統治是社會現實最重要的結構因素,所有社會生活通過統治被組織起來,只有通過統治社會生活才被導向一個行動目標。”統治的任務不僅僅在于借助倫理道德目標來塑造一個民族整體,更重要的是要將每個個體和目標聯係在一起,激發起他為這個目標而奮鬥的激情。對于弗萊爾而言,政治權力是創造穩定、整合的統一社會的重要手段。弗萊爾相信由右派革命所創造的權威主義新國家能夠將技術與社會和民族聯係起來,納粹的政治實踐能夠實現他在《國家》中的社會理想。
缺少共同目標的社會不能使其成員獲得存在的意義,不能為技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契機,這是弗萊爾對魏瑪共和國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混亂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共同的目標,個人只會肆無忌憚地追求個人利益。個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和自由,但要將其放置在國家、民族這樣一個共同體的限制之下,也即個人利益的目標最終是實現共同體的價值,也只有共同體的利益才能為個人的奮鬥提供目標感。在《普羅米修斯》一書中弗萊爾明確表達了對個人沒有限制因而產生混亂的時代的反感,他認為現代社會就是缺少這種限制,變得越來越開放,我們才越來越難以確定自身,也不能在一個過于開放的現代社會找到自己的存在之根。一切道德和文化的根基都存在于封閉社會,“開放社會必定無涉道德,如果不說是非道德的話,它將是尋歡逐利者、追求無責任權力者的淵藪,集各種不負責任、玩世不恭之大成〔……〕崇高之事非開放社會所能知”。從其博士論文開始,一直到 1965年出版最後一部著作,弗萊爾主要的理論關注點始終在于探討現代社會何以變得如此開放,而我們又應如何給如此開放的現代社會重新加上界限,使其重新“閉合”起來。意義和確定性始終與界限相關,“劃界”(delimitation)就是在尋找意義,而文化的作用就在于為不斷變化的時間之河流提供閉合性(closedness)和穩定性(stability)。從最深層次上來說,對歷史傳統的思考能深刻反映出對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同時也能反映出思考者本人的價值觀。弗萊爾自身對歷史的評價就是隨著其對現實態度的轉變而變化的。他在《當代理論》里也一再表達了這一理論觀點:現在的文化從傳統中獲得權威,歷史的維度不僅增加現在的“重量”和“深度”,而且使社會文化獲得總體上的連續性。弗萊爾為現代社會加上了歷史的維度,強調現代社會與過去時代的歷史連續性,並在傳統中尋找未來制度的合法性。
《國家》最為集中和明確地說明了現在和過去的密切關係。在《國家》中,歷史被分為三個階段:信仰、風尚和國家。“如黑格爾的思考方式,前兩個階段分別具有肯定的特質和否定的限制。在第三階段,肯定的特質被保存和聯合起來,而否定性的限制則被超越。”第一個歷史階段:信仰。在這一階段,手段與目的不存在衝突,社會處于自我封閉狀態,借助神話、宗教崇拜、語言等文化的凝聚作用,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緊密相連。人們用神話解釋自然和社會,“人們僅僅解釋自然對于人類當下所具有的意義,而非將其作為一種客體進行研究”。宗教崇拜和神話一樣不僅是對自然的神秘式解釋,同時能調整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用語言命名外部事物,語言成為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第三紐帶。弗萊爾認為,在信仰階段人們和自然的這種親緣關係使人居于世界的中心,以自身的行為方式和存在方式來定義自然,他們彼此之間,和外部世界之間並未出現疏離和異化,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意義的“你的世界”(Du-Welt)中。這是一個帶有牧歌情調的前現代社會,人們分享共同的文化和信仰,也具有共同的視野。這樣的社會建基于血緣和土地(Blut und Heimat)之上,缺少內部變化的契機,形成一個穩定、自我封閉、統一的,被弗萊爾稱為“最完全的人類紐帶”的共同體。弗萊爾對信仰階段的社會和歷史並非全無批判:人類的生存並未脫離自然,因而無法創造出如技術、科學、法律、藝術等更高階的文化(這是下一發展階段的產物)。
“信仰”社會只有通過兩方的分裂,且建立一方對另一方的統治才能過渡到社會歷史發展的第二階段:風尚。這一階段社會關係的特點就是統治與依附。統治的長久性保障了血統不證自明的優越性,人們的社會地位來自血統的高貴,當血統論逐漸式微之時,經濟成為統治的動因,財富變成決定社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弗萊爾名為‘風尚’的階段清楚地包含著被馬克思等人稱為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文化內涵深深吸引了弗萊爾:社會衝突取代了和諧的共同體,文化喪失自我封閉性,開始向高一級發展。這一階段的文化發展被西美爾稱為文化的悲劇:文化各部分自主發展,彼此之間缺少相關性,都致力于創造自身的絕對形式,追求抽象、普遍的結構,而忽略人類自身的需要。文化各個領域根據自身邏輯獨立發展,追求自我指涉性,和特定的文化背景脫離,其價值不再來源于特殊的人文背景的意義,而由其自身得出。文化在“風尚”階段發展到鼎盛期,但是各文化門類之間缺乏協同和凝聚,不能組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整個文化呈現碎片化發展的特徵。
“風尚”階段技術的獨立發展尤其引起弗萊爾的關注。但弗萊爾並不就此認為意義和目標的缺乏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技術可能缺乏內在的意義和目標,但是威脅現代社會的無目標和‘總體’缺位的原因並非是技術,而是資本主義。直到現在,現代歐洲技術總是與資本主義(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原則)攜手發展,應是資本主義而非技術要為現代社會目標的喪失負責。”資本主義和現代技術從產生之日起就獨立于人的意圖,按照經濟和資本原則自主發展,現代技術發展越精益,越有可能威脅人類的生存,使人類僅僅成為手段和生產的奴隸。本是作為手段的技術本身演變成目的,不再受人類控制。所以弗萊爾認為我們要做的不是否認技術或是阻礙其發展,而是打破其與資本主義的聯結,將技術重新整合進共同體的總體生活中。
歷史的第三個發展階段“國家”就不僅保留了技術發展的成果,更是將其整合進一個封閉的具有共同信仰和文化的總體中。也就是說,技術的發展要以社會整合為目標,以維護民族的獨特價值為導向,在“國家”階段,技術的此種發展能夠得到保障。弗萊爾將前現代的集體社會(信仰階段的社會)描述成理想社會,一個肯定時代的典型,它具有穩定、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每個人都可以充分了解自己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弗萊爾認為“共同體再次被定義為一個具有共同命運和文化視野的封閉世界。〔……〕這樣一個由類似部分組成的社會和文化只有在前歷史階段,在統治出現以前才能找到其純粹的形式〔……〕雖然共同體不再以前歷史形式存在,但它在之後的時期仍然以改進的形式出現:民族”。弗萊爾試圖重建集體社會中的社會凝聚力、穩定性和共同感,但他並不企圖恢復前現代社會的歷史秩序,而是將眼光放在未來:重建民族共同體。要將民族重建為一個政治上的共同體,就必須強化民族意識和總體意識。自然和歷史本身的過程並不能創造一個新的總體,具有總體意識的人才能推動這一過程,所以弗萊爾同樣強調重建共同體過程中人的主觀意識的重要性。他倡導一種卡里斯瑪型的領袖人物,其權威和統治是不受限的,其作用在于借助權威或高壓政策促進一個分散的社會整合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共同體。領袖原則形成共同體內的等級制,其成員的地位由其為國家和民族作出的貢獻決定。然而並非每個人都願意服務于共同目標,所以國家權威和政治手段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新的共同體內所有領域的整合都要靠國家控制來完成。“技術和經濟從個人效用最大化中解放出來,以民族目標為導向。”弗萊爾支持國家根據民族共同體的利益對技術進行控制,主張運用現代技術來達到民族目標。弗萊爾堅信強國需要先進的技術,而政治的力量能調和技術和民族間的分歧,讓技術為國家所用,不再受命于工業社會的經濟原則。
在弗萊爾取得大學執教資格的論文中,他已經指出:19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普遍將技術的發展視為對人類價值的威脅。在德國,這經常被表述為文明與文化之間的對抗,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之後對德國文化的認定,對英國和法國文明的認定更是使這一觀點盛行起來。從拉丁詞源學上來看,文明一詞自身可能就標志著技術對于德國靈魂而言是陌生的。
弗萊爾從更寬泛的意義上定義文化,將之視為一個共同體信仰和制度的總和,技術與文化的衝突在弗萊爾這里就具體化為技術的發展將導致共同體內共同目標的衰落和特殊文化的消解。“技術解除政治和文化的壁壘”,因為技術,連同其科學化和經濟追求,是一種跨國際的存在,其內在邏輯具有一種普遍性。技術是無國界的,而文化則有其特殊性,一個民族只有保有其文化的特殊性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弗萊爾預見到技術的不斷發展甚至全球化勢必會導致民族共同體獨特文化的喪失,而共同體文化又是社會整合和個人生存意義的來源。特殊才能產生意義,而在技術的高度發展下所有人都會因被席卷到理性化的秩序中而喪失其獨特性,這在弗萊爾看來則意味著普遍的無意義感和無目標感。弗萊爾注意到技術可能給文化帶來的威脅,但他認為通過政治行動可以整合技術與文化。“弗萊爾認為當代哲學家將技術看作外在于文化並對文化有害而忽略了技術在文化歷史中最重要的發展,即技術態度的出現。弗萊爾寫道:現代技術的出現標志著西方歷史甚至是世界歷史的轉折。”現代技術的發展基于這樣一種信念:自然世界是可塑的且人類能夠改造自然世界。技術專家們企圖通過研究自然的客觀性實現改造自然成果的最大化。弗萊爾認為技術的發展不同于文化(形成一個繁榮與衰敗的不斷循環),它是單線的:在技術史上,發展是始終如一的。弗萊爾提出技術的文化意義這一問題,他不僅強調技術無害于文化,還主張技術是現代文化(包括德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弗萊爾並不否認現代技術的合法性,並且:重要的是建構一個結構牢固的、能完完全全吸納個體的統一體。只有一種能在人的僵化狀態中釋放其深層強力,並將他們整合進超越于黨派和階級利益的生產意志中的宗教;只有一種運用自明真理力量的倫理理想係統;簡而言之,重獲或喚醒與他人相關、與我們的生命相關的意志和信仰的普遍而特定的常量,如此則能將 19世紀利己主義導致的分裂和過度的物質主義導向一種新的文化。
這一新的宗教就是民族主義,弗萊爾堅信只有德國的政治右派能將技術和靈魂結合起來,“經濟生活會被重新整合進新宗教,德國的反資本主義再也不會和德國民族主義的需求相背離,民族主義變得現代化,並會成為將德國從無靈魂的物質主義荒漠中拯救出來的文化力量”。弗萊爾為技術提出新的任務:促進新文化的誕生,在這種新文化里,技術需要服務于更高的文化目的。弗萊爾一直關注技術與文化的關係,希望創造一種既能保證技術發展又能將其整合到更大的道德目標中去的新文化,即創造一種“不是憑借技術同時也不與技術背道而馳的文化,一種能讓技術在其中克服資本主義的文化”。因此,弗萊爾認為德國民族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既保留技術帶來的物質利益,又能避免技術對文化的破壞。
1928年弗萊爾在《技術哲學》中又回到技術和靈魂(文化)的融合問題,指出技術能夠和整個文化的內在命運聯係起來,而只有在民族共同體的社會里才能誕生包容了技術的新文化。我們可以明確看出,弗萊爾的技術觀和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脈相承的,他在社會中為技術找到了新的位置,將技術轉到促進民族和文化發展的積極道路上來。但技術的現代化只有在完成了右派革命的、超越工業社會的新帝國中才能實現,無怪乎他將納粹運動視為能實現其政治理想的一道曙光。
在世紀之交的現代性危機和散亂的政治格局中,德意志知識分子努力為德國的現代性尋找新的出路,在一片荊棘叢中奮勇向前。對于像弗萊爾這般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而言,技術的現代化是現代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代性的危機同樣體現在技術上。工業社會的社會狀況和社會組織並不是實現技術現代化的理想環境,所以應為技術的發展培育新的土壤。他將技術的變革寄托在社會變革上,認為一個極權主義的民族國家運用政治權威整合社會各方力量,將能夠克服技術在工業社會的無目的性和工具化,並利用國家控制充分發揮技術的正面作用。弗萊爾尤其重視國家權力和民族共同目標在技術轉型中的作用,從此出發完全可以將弗萊爾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作為理解其技術觀的切入點。而希特勒逐漸暴露出的野心將個人權力欲淩駕于國家、民族之上;對國家社會主義希望的幻滅使弗萊爾及其他有類似理論傾向的德國知識分子轉而支持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激進的保守主義革命過渡為調和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保守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