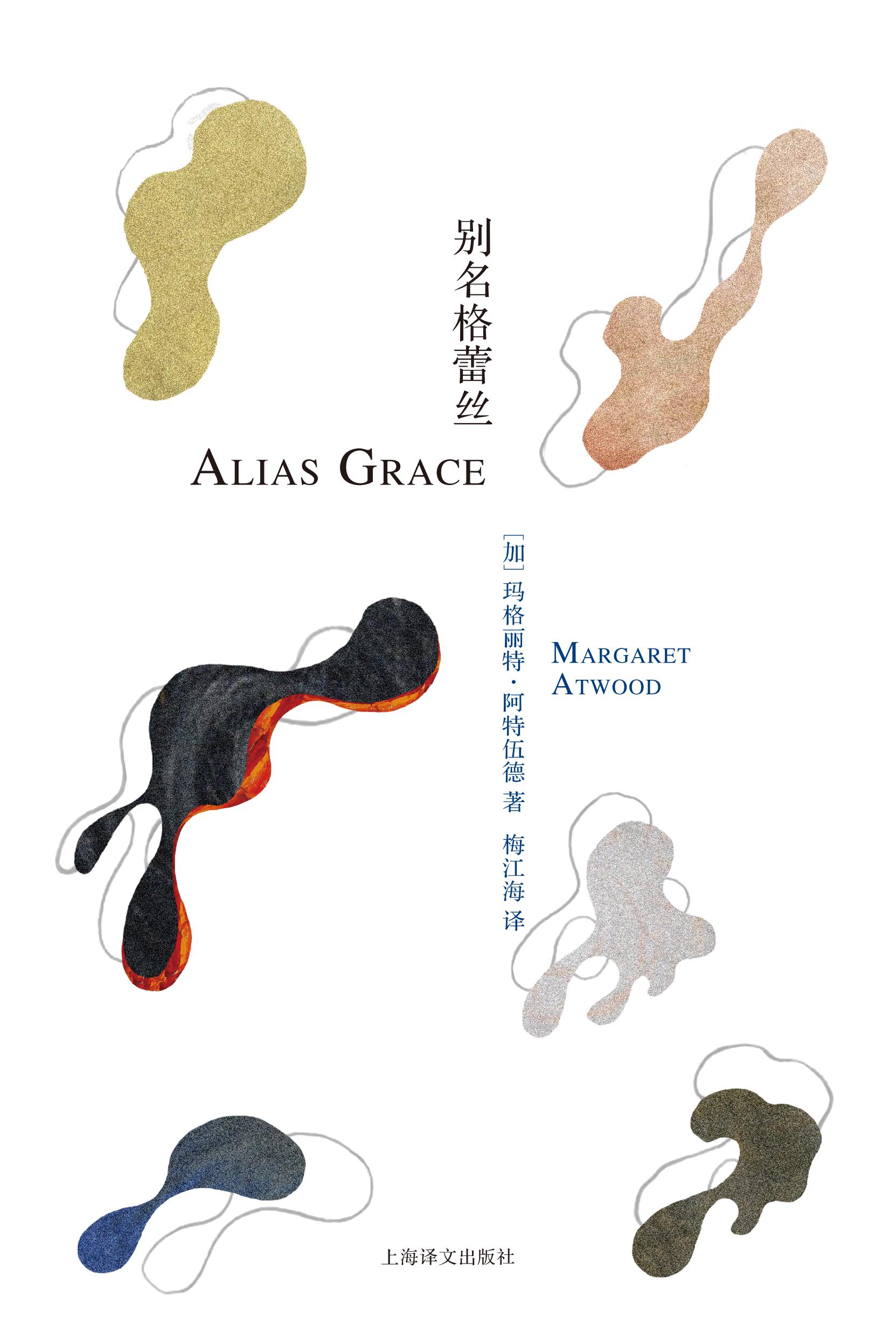
書名:《別名格蕾絲》
作者:【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譯者:梅江海
ISBN:9787-5327-6851-6
出版時間:2016年3月
裝幀:平裝
定價:57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瑪格麗特o阿特伍德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以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樁臭名昭著的罪案為底本,講述了一個錯綜復雜卻充滿詩意的故事。小說乍看充滿現實主義敘事風格,卻又隨著情節的推進,筆法自然翻轉,性、謀殺與階級衝突交相混合,想象的樹脂流淌進了歷史事件的縫隙里。通過人物視角的切換,故事獲得了絢麗的碎片化效果,邪惡與尊嚴、悲劇與華美共存,虛實相生間,特定年代最為廣闊的社會畫卷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作者/譯者簡介】
被譽為“加拿大文學女王”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奮多產的作家,迄今已有14部詩集、11部長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文學評論出版,並主編了《牛津加拿大英語詩歌》、《牛津加拿大英語短篇小說》等文集,此外還撰寫了不少廣播、電視、戲劇、兒童文學作品等。她獲得過除諾貝爾文學獎之外的幾乎所有的國際文學獎和不計其數的其他獎勵和榮譽,並被多倫多大學等十多所國內外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她的作品已被譯成30多種文字。
阿特伍德19歲開始發表自己的第一首詩作。她擅長將日常經驗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層次,她的詩歌不僅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詩界都很有影響,先後獲過多種重要的文學獎。
自從196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可以吃的女人》之後,她的作品頻頻獲獎,這也為她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她創作的三部優秀長篇小說《女仆的故事》(1985)、《貓眼》(1988)、《別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獲得布克獎提名,最後憑借第十部小說《盲刺客》摘得了這項最高文學獎的桂冠。同時,阿特伍德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無論在民間還是文學界都認為她得獎是遲早的事。
阿特伍德的影響不僅跨越了國界,也跨越了文學領域。她一直十分關注美國文化對加拿大無所不在的強大影響和加拿大日益美國化的傾向;為抗拒這種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進獨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她幫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協會,並曾任該作協的主席,還擔任過國際筆會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紐約人》等多種國際知名報刊雜志上發表詩歌、短篇小說、評論等;她還應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國朗誦和演講,擴大加拿大的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她開始關注另一領域--環境保護,顯示了很強的生態意識,並因這方面的創作、論述和所採取的行動而獲得環境保護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榮譽和獎勵。同時,她越來越多地介入國際政治:如反對美加自由貿易法案、為“大赦國際”組織的鬥爭在加拿大開辟陣地,等等。總之,在過去的約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學代言人的身份活躍在世界文壇,被列在“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阿特伍德的創作可按四個歷史階段分為“早期的創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早期的創作”中,詩集《圓圈遊戲》是使她獲得總督獎而在加拿大文壇脫穎而出的;自此,加拿大第一流的大出版社紛紛主動向她敞開大門;同時,媒體的關注再也沒有離開過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中,《幸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的發表引出了褒貶不一的爭議,繼而又引發了一係列關于加拿大文學及文學評論的討論,客觀上使該書成了一部影響遠超出它本身價值的文學評論專著。因為,《幸存》的發表既是加拿大民族主義思潮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反過來推動了這一思潮的發展。這本書的出版,客觀上成了加拿大文學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中,被稱為“女性主義的《1984》”的《使女的故事》極為成功,贏得第二次總督獎及眾多獎勵和榮譽,大大地擴展了她的讀者群,贏得了國際主流市場,並使她躋身世界名人的行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中,被讚為“意義深遠、富有戲劇性、結構精妙絕倫”。
【重要評薦】
我們時代接觸的小說家。--《星期日泰晤士報》
【譯者後記】
有人曾說加拿大文學沒有皇帝,但有位女皇,她就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可是,因為我只是由于教書的需要才零散接觸一些加拿大作家,所以無法判斷上述評論是恰如其分,還是言過其實。但平心而論,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確是在加拿大作家中我較為偏愛的一位。她的作品構思新穎,哲理深邃,語言豐富,逸趣橫生。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在時間永遠不夠用的情況下,擠出時間在她的第九本小說《別名格蕾絲》問世後不久就先睹為快,一口氣將這本不短的小說讀完了。很為小說中一些妙不可言的特點而感到激動,因而決定把書譯成中文,向廣大的中國讀者介紹一本好小說,讓更多的人一睹加拿大文學女皇的風採(我似乎已接受了剛才那條評論)。從一九九八年我的中文譯本《別名格蕾絲》首次由譯林出版社在國內出版,至今已近十多個年頭。時隔十年,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再次向讀者介紹這部作品,如今,上海譯文出版社又打算重版這部不可多得的當代名著。我作為本書的中文譯者,也作為比諸位先行一步的讀者,感到有義務奉獻我本人對這本小說的一孔之見。可謂拋磚引玉,期望能起到打火石的作用,引出新見解的火花。文學創作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文學欣賞與文學批評亦是如此。時常難免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我的見解若有膚淺謬誤之處,還望今後有機會與諸位進一步探討。
這本小說的英文標題是AliasGrace,直接譯成中文便是《別名格蕾絲》。正如英國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一書中所指出,所有小說共有的主要成分是“故事”,沒有故事就沒有小說。我們都像《天方夜譚》里謝赫拉莎德的丈夫蘇丹大人那樣,耐不住懸念的誘惑,急于發現“後來怎麼樣了呢”,從而使深諳“故事中的懸念”之奧妙的謝赫拉莎德免于一死見E.M.Forster,AspectsoftheNovel,London:EdwardArnoldLtd.,1974,pp.1718。。《別名格蕾絲》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于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能利用讀者的好奇心,巧妙地安排情節,致使讀者長時間地處于懸念之中。
這是一個女謀殺犯的故事,因而,阿特伍德在情節安排上大量使用了謀殺故事和偵探小說的手法。故事開始的時間為1859年,即1843年的雙重謀殺案發生之後十六年。女主人公格雷絲·馬克斯正在因參與了她過去的雇主托馬斯·金尼爾和他的管家兼情婦南希·蒙哥馬利的謀殺案而在金斯頓的教養所里服無期徒刑。因為被不少人認為精神不正常的格蕾絲堅持說自己喪失了對謀殺案的記憶,當地有一批“改革人士”聘請了一位名叫西蒙·喬丹的美國醫生來對她進行精神上的調查和鑒定,以便寫出一份專家鑒定報告,附在他們的請願書里,讓格蕾絲獲得赦免。在很大程度上讀者與西蒙·喬丹一樣,急于發現“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她是否真有罪”的答案。就是在這樣的懸念和期待之中,讀者滿懷興致地一頁頁翻過書頁,不斷地證實或否認自己的猜測,探索頭腦里那些問題的答案。像其他偵探小說一樣,重要的線索,如勒死南希的手絹,在書中多次有交代,留有伏筆。第十三部分“潘多拉的盒子”中那場有濃厚的情節劇色彩的神經催眠療程很讓人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中的“終場”:主要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由料事如神的比利時大偵探波羅揭露真兇,在場的和讀書的都大吃一驚,但真相大白,皆大歡喜。整個謀殺案的“結局”又很像典型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兇手曾受過被殺者直接或間接的迫害;兇殺是復仇、伸張正義的非法手段。雖然讀者對罪犯不無惻隱之心,但難案被高手破了,讀者的好奇心得到最大的滿足。
可是,正如作者本人在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記者採訪她時說:《別名格蕾絲》的確“非常像偵探小說,只是結局懸而未決。這就是歷史和謀殺疑案之間的區別”。很顯然,阿特伍德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單單是要講個聳人聽聞的謀殺故事,而是要糾正蘇珊娜·穆迪等在她之前的作家“把流傳的故事以訛傳訛”見本書“作者跋”。的做法,從而還女仆格蕾絲以本來面目。杜邦醫生(傑里邁亞)主持的神經催眠療程不過是小說家為情節的需要而虛構的讓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不可當真。原因很簡單:因為歷史上的格蕾絲之案沒能定性,小說中的謀殺案也應依舊是“懸案”。
在寫這部反映十九世紀中葉加拿大安大略地區生活的歷史小說時,阿特伍德作了極為廣泛的調查研究,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正如她在“作者跋”中所寫明,不僅有關監獄和精神病院的生活“是根據可查找到的歷史性材料寫成的”,而且對招魂術和催眠術在北美的興衰的描寫也是基于史料的。作者在書中詳細描寫了愛爾蘭移民遠渡重洋,歷盡千難萬險來加拿大的情形,提到1837年加拿大的民主領袖麥肯齊領導的“大造反”,並且讓書中的男主角西蒙·喬丹最後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戰場上頭部受傷,喪失記憶。她不僅把小說安置在歷史的總框架內,而且對許多細節,諸如當時多倫多的街道、商店、時裝、風尚及道德舉止,都逐一作過調查。對有關謀殺案的現存史料,小說家更是“盡量作最合乎情理的選擇”。的確,她雖然“把歷史事件小說化了”,但“沒改變任何已知事實”。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威廉·薩克雷在《英國十八世紀的幽默作家》一書中為歷史小說辯護說,歷史小說比歷史更真,因為前者寫的是“真情”(truth),而後者只收集“全真的史料”(authenticinformation)。薩氏還深有體會地說,“我從有虛構情節的小說中親身體驗到當時的生活、風俗、交通、服裝、娛樂、歡笑,以及對社會的嘲笑--過去的時代又變得栩栩如生,我便可以在舊時的英國四處漫遊了。”《牛津版薩克雷全集》,ed.GeorgeSaintsbury,(Oxford,1908)第十三卷,543頁。阿特伍德這本歷史小說的獨到之處在于:她把“史料”和“真情”一道交給讀者,給他們以比較鑒別的機會。本書共分十五個部分、五十三章,每一部分開始前都有幾段摘自當時的作家或當時報刊的引言,擬為該部分的閱讀提供提綱挈領的指南和提示。從第八部分“狐狸與鵝”開始,每一部分的引言中都包括一些原載于當時報刊的、直接報道謀殺案的摘抄段落。隨後,該部分便講述與引言部分相對應的,經小說家重新創作的“真情”。通過這樣的方法,對引言里的“史料”記憶猶新的讀者便能更加主動,更加有意識地欣賞小說家筆下的“真情”,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去體驗書中人物當時的生活環境。這實為一部風格獨特的歷史小說。
作為歷史小說,《別名格蕾絲》全面反映了當時加拿大的社會生活。除了歷史案卷中提到的與謀殺案有關的幾個真人之外,小說家還根據情節和主題的需要創造了許多“假”人物,並且賦予真人物許多可能而可信的“假”特性。通過這些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真、“假”人物之間的相互交往,作者成功地使單一層次的歷史事件有了社會深度和思想力度。
阿特伍德筆下的女主人公格蕾絲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主見的人物。她在書中的作用是多重的:身為地位卑賤的女仆/囚犯,格蕾絲既是局外人(一個善于觀察、頭腦清醒的評論家),又是局內人(一個飽嘗艱辛而又善于自我保護的弱者)。通過這樣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之口,作者有力地抨擊了當時政治、思想(包括種種“偽科學”)、宗教以及社會上的種種弊病。但是,其批評的鋒芒直指當時階級差別懸殊、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與格蕾絲相比,男主人公西蒙·喬丹顯得黯然失色。他與廣為流傳的《鵝媽媽的兒歌》中頭腦簡單的西蒙同名絕非偶然,因為他的確有著傻瓜西蒙似的、不甚開竅的腦瓜。不僅他對恢復格蕾絲的記憶所做的種種努力是徒勞的,而且對自己的生活也徹底失控,以致墮入無法收拾的境地。但是,他也是個“立體”的人物,具有性格的多重性。一方面,他同情格蕾絲,充滿正義感;另一方面,他是當時社會造就出的“我”字當頭的大男子主義者。通過對西蒙·喬丹這樣一個復雜人物的塑造,以及對他與書中一些女性人物之間關係的描寫,作者生動地刻畫了一個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女人,諸如雷切爾·漢弗萊、喬丹夫人、莉迪亞小姐以及菲斯·卡特賴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蒙的支配,做他的附庸,為他而生存。勞動婦女,諸如格蕾絲的母親、格蕾絲、瑪麗·惠特尼和南希·蒙哥馬利,深受統治階級和男人(父權及夫權)的雙重壓迫,尤其令人同情。
本書塑造的眾多女性人物中,除去女主人公格蕾絲,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瑪麗·惠特尼。她性格活潑,思想解放,對格蕾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是,就連這樣一個有見解、有理想的女孩子也擺脫不了受少東家的欺騙和淩辱,正當妙齡就含恨死去的悲慘命運。瑪麗的死整個改變了格蕾絲,正如她後來所說,“沒有瑪麗,我的故事會完全不同”。作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的犧牲品,瑪麗·惠特尼這個人物不僅對本書的主題至關重要,而且提供了偵破謀殺案的重要線索。閱讀本書時,讀者應特別注意第二十章中有關格蕾絲在瑪麗去世後昏睡十個小時的文字,以及第二十二章里第一次出現的聖歌:“多年的岩石,為我開裂,讓我藏身于你……”只有記住了這些重要的線索,才能在第四十八章里聽見神經催眠術下熟睡的格蕾絲大叫:“我可不是格蕾絲!格蕾絲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並再次吟唱那段聖歌時初步悟出書名之奧秘。《別名格蕾絲》--如果就事論事,我們勢必會得出與維林格牧師相同的結論:這是一樁很明顯的著魔案例,即瑪麗·惠特尼的魂附在格蕾絲·馬克斯的身上,謀害了托馬斯·金尼爾和南希·蒙哥馬利。但是,如果我們牢記小說的主題,《別名格蕾絲》又可在廣義上理解為:一個有代表性的、富有正義感的、備受傷害的女人(無論她的名字叫什麼)借用格蕾絲的名義向壓迫她的社會復了仇,行了正義之舉。那聲音說得很清楚:“這次那位紳士也死了,至少也死了一次。公平合理!”--典型的“一報還一報”。但是,本書的妙處在于:多種解釋並存,讀者可以隨意選擇。解破“她是否有罪?”這個謎的真正線索在如何看待罪惡的社會。阿特伍德打開歷史舊案重新審理的本意顯然是要為弱者--受壓迫、遭欺淩的廣大婦女--伸張正義。這實為一部情真意切、發人深省的社會歷史小說。
在敘述手法上,小說家別出心裁,根據故事的需要,巧妙地使用了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敘述相結合的方式。小說的首章以第一人稱倒敘的形式敘述了格蕾絲向喬丹醫生對謀殺事件所作的回憶。格蕾絲的自述用意識流的手法,以書中的主要象徵性實物--牡丹花--為線索,把關鍵的情節描寫得虛虛實實,引人入勝。接著,作者用民謠的形式在第二章里不置可否地重述了當時對該謀殺案的流行說法。第三、第四、第五章(構成書的第三部分“角落里的小貓”)完全是格蕾絲的第一人稱自述,使讀者有機會對女主人公有進一步的了解。在本書的第四部分“年輕人的幻想”(包含第六至第十一章)里,讀者聽到的卻是不同的敘述聲音的穿插使用:喬丹醫生與母親及朋友的通信(可稱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第一人稱自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顯然在情感上持“中立”態度的第三人稱敘述者,其間穿插著格蕾絲的自述,接著又是那位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小說前四部分里使用的這種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聲音給聽眾“講故事”的手法在全書中反復出現,靈活使用。作者通過間或使用第一和第三人稱敘述者的手法,有效地掌握並調整讀者與書中人物之間的關係,使得閱讀更加趣味無窮。一方面,因為本書大部分是格蕾絲的自述,讀者易于受她的情感所感染,喜其所喜,悲其所悲,恨其所恨。但是,另一方面,時而出現的第三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又常把讀者帶出格蕾絲的“小天地”,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她視野之外的社會生活的其他側面。結果是,讀者不僅能較客觀地看待書中人物,而且能自始至終以“不即不離”的態度判斷並預測他們的行為。並且,作為格蕾絲所講“故事”的間接聽眾,讀者因為能夠通觀全局,時常感到比書中的直接聽眾西蒙·喬丹高明。沾沾自喜之余則更多了幾分想弄清究竟的好奇心,殊不知這一切都是作者巧手安排的結果。
《別名格蕾絲》不僅表現出阿特伍德作為社會歷史學家所具備的嚴謹和睿智,以及小說家所特有的創作才能和技巧,而且還洋溢著她那不同凡響的詩人的敏感和想象力。小說中大量出現諸如第八章結尾三段中那樣的直喻疊用、意象連篇的文字。通過對人物的內心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反應作如此細膩的描寫,作者把抽象的感覺變得具體化,形象化,從而使歷史案卷中線條粗獷的謀殺案變成雋永耐讀的文學佳作。形象地說,整個小說是一幅以女仆格蕾絲為中心的十九世紀中葉的加拿大社會歷史全景圖。這幅圖畫的妙處在于:它不是用普通的筆墨繪制成的,而是許多女人一針一針、一個拼塊一個拼塊地縫合起來的。為表現當時各社會階層的婦女生活,作者阿特伍德在書中對傳統的縫被子藝術作了大量的描寫。無論是社會地位高的“貴夫人”(諸如獄長夫人),還是格蕾絲這樣的卑賤女仆,都把縫被子看作一種重要的女紅,一種藝術性的實際消遣。可是,只有在發現小說家用不同的被子圖案的名稱來命名書中的十五個部分,借以畫龍點睛時,明眼的讀者才會意識到作者的用心良苦,匠心獨具。如果說用第一個被子的圖案命名的第一部分“參差不齊的牙邊”用意識流的手法形象地表現了格蕾絲被攪亂的記憶,成功地把讀者帶入懸念,題為“天堂之樹”的最後一部分則把讀者帶到另一個境界--道義上的天堂。格蕾絲“根據自己的想法”設計的被子圖案是意味深長的:“我的樹上有三個三角拼塊會很特別。一塊是白的,我要用瑪麗·惠特尼給我的那件襯裙上的一塊布做。一塊褪色發黃的,要用從我留作紀念的監獄睡衣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第三塊是淡色的棉布,上面有粉色和白色的小花,是從我到金尼爾先生家的第一天南希穿的裙子上剪下的一塊布做的……我要在每個三角的周圍用紅色的羽毛針腳繡一圈,把三個三角繡在一起,形成整個圖案的一部分……這樣,我們三人就會在一起了。”
現實的故事終于以詩的方式有了個幸福的結局,名副其實的“poeticjustice”(理想的公正)。人間的恩恩怨怨到了天堂都化為烏有,三個飽受人間苦難的小姐妹重歸于好,皆大歡喜。如果我們根據小說的結局把書名中的“Grace”一詞解釋為英文原意中的“上帝的恩愛、仁慈、寬容”,便可領會書名里蘊藏著另一層含意。但是,如果把格蕾絲最後的赦免和幸福結局看作是與不公正的世道毫無關係的上帝的恩愛和慈悲,本書的譯名似乎應改為《亦稱主之恩慈》或是其他類似的題目。那麼,讀者沒開卷就會感到濃厚的基督教色彩。這不僅將違反作者的原意阿特伍德並非基督徒。況且,她在本書中使用基督教概念時不無譏諷口吻。,而且會把本來耐人尋味的書名狹義化,概念化。所以,我還是老老實實地按字面含義把書名譯成《別名格蕾絲》。顯然,阿特伍德寫這本書的原意是多層次的,叫人難以捉摸,其深奧之處在寓意頗深的書名上可見一斑。無論如何,這是本具有獨特的雅俗共賞的趣味性和文學性的好書。其最大的好處在于各層次的讀者都能開卷有益,“各取所需”。
本書的翻譯最初承蒙加拿大藝術理事會和加拿大外交及國際貿易部撥款資助,我在此特別表示感謝。我堅信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將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接受和喜愛。可是,由于本人才疏學淺,難免在譯文中有疏漏、錯譯之處,敬請讀者多加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