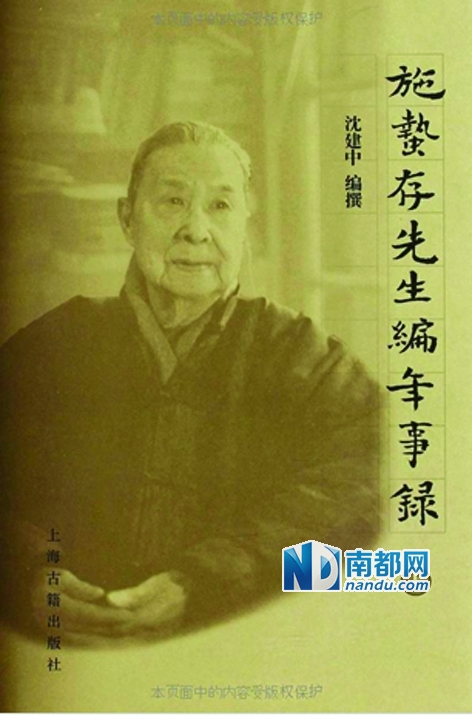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沈建中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版,198.00元。
尹大為 媒體人,上海
十年過得真快,到今年11月,施蟄存先生已故去十年了。施先生弟子沈建中正好編撰成煌煌126萬字的《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可說是對施先生一種深切的懷念。這兩厚冊書,像兩塊沉甸甸的磚頭,施先生活了近百歲,身經二十世紀各個重大歷史時期,確實,這麼厚才當得起他漫長的世紀人生。
《事錄》共1600多頁,一讀之下,比近年諸如梁啟超、黃永年等人的“年譜長編”、“編年事輯”,似乎要完備。作為弟子,作者的條件得天獨厚,可以親炙老人,拿到第一手材料。據作者後記稱寫了“整整十六年”,那應該在施先生生前已經動筆,最初應該得到過先生許多指點。同時,作者也下了苦功,以編年為體,不僅把施先生幾乎所有涉及身世經歷的文章、日記統統編入,還在流通不廣的雜志上,鉤沉出多篇施先生早年用各色筆名撰寫的鴛鴦蝴蝶派風格的少作。施先生一生交遊廣泛,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知名的新文學作家都和他有過交往,作者查閱了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沈從文、鄭振鐸、戴望舒、朱光潛、朱自清、啟功、浦江清、劉吶鷗、呂叔湘、向達、季羨林、徐中玉、許傑等等,近百位與施先生有過交往的師友、學生已發表的日記、書信、年譜和回憶文章。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搜羅了一大批尚未公開發表的施先生往來書信和資料。近年施先生身後大量書信流散到京滬各大拍場以及舊書網站,圖錄介紹上所登大多並不完整,但作者耐心地一一將之錄成文字,有的首尾不全,有的時間模糊,他都在其後注明“市肆影件,所見不全,錄此待考”字樣,以存其真,極為珍貴。
此書堪稱迄今為止內容最為詳實的施蟄存“傳記”。雖書名標為“編年事錄”,其實是一種別樣的“傳記”。施蟄存幾乎是與二十世紀同齡的老人,文學涉獵面又極廣,與魯迅論戰等重大事件的評價眾說紛紜,要為之寫傳,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然而,作者治“傳”所選取的角度極為巧妙,只羅列,不評論,實錄當事人的相關文字,不加作者的個人評論,讓資料自己說話。比如1933年圍繞施蟄存向年輕人推薦《莊子》、《文選》而引發與魯迅的著名論戰,讓他倒了半輩子霉,作者用近二十頁的篇幅照實記錄了幾乎所有發表的往來文字,來龍去脈盡收眼底。除了收進魯迅和施蟄存一來一往近十次公開發表在《申報》、《大晚報》等處的文章片段,雙方和別人說到此事的多封信件,還搜羅了茅盾、曹聚仁、陳子展等人十余篇助戰文章,更找到當時的小報如《出版消息》等等從第三方角度的評論,還原了當時整個文壇生態,讓讀者自己在對比中得出自己的結論。雖是羅列,但某些細節也別見作者取舍的苦心。如施蟄存在《〈莊子〉與〈文選〉》一文中在推薦書目旁“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事錄》第237頁),這注腳提醒我們施先生的推薦有其劃定的范圍,之後雙方論戰、多人助戰似乎有擴大化之嫌。另外作者還他處列出郭沫若1941年發表的一段雜感,頗堪玩味:“我在日本初讀的時候,感覺著魯迅頗受莊子的影響,在最近的復讀上,這感覺又加深了一層。因為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匯,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讚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莊子的反映。”(《事錄》第473頁)郭是論戰的局外人,這段文字多少反映出旁觀者的評價。
全書雖是施先生的個人“傳記”,一個獨特的個案,但卻反映出一代文化人在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中的艱難沉浮,翻閱之下,感慨良多。三十年代編輯《現代》風生水起,四十年代輾轉內地、躲避轟炸、顛沛流離,五十年代反右時“疏忽大意”鑄成大錯等等,這幾段尤為驚心動魄,耐人尋味。正如施先生說的:“我實在坐過一葉小舟在這許多慘絕人寰的亂灘中平安浮過。”(第1643頁)在風雲變幻之際,更突顯出施先生獨特的風骨,借用陳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施先生完全當得起。他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編《現代》雜志時聲名鵲起,可以從他為雜志寫的“宣言”中看出他的堅持:“《現代》是普通的文學雜志,不是狹義的同人刊物;又申明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希望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合適的貢獻。”幾經磨難之後,到2000年他依然故我,他在接受臺灣作家採訪時說:“我認為文學不應該有人為的主流。中國的政治家規畫了寫實主義為主流,我們這些就是旁流、支流、逆流;既然說是要百家爭鳴,為什麼要人為劃分,讓一朵花來做主角?……我深知政治迫害在我們身上是沒有什麼辦法的。我一直深知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我也不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但是必須作家出諸自願。”(第1333頁)兩者放在一起讀,倒是可以讀出些別樣的滋味。
書中一些細節也頗為生動,讀了倒生出許多沉甸甸的悲涼。如1996年《文匯報·筆會》五十周年約好採訪他,第二天人去了他又變卦了。他說:“我不知從何說起,我想從五七年的反‘右’說起,但又覺不太合適!……五七年反‘右’時,華師大內定的名單上本來沒有我,恰好,《文匯報》約我寫文章,就寫了,有人告訴我,現在正在抓右派,你還寫文章,這不是自投羅網嗎?當時我一聽嚇壞了,連夜打電話給《文匯報》撤稿,但報社回話說已經開印,撤不下來了。就這樣,我就隨著文章的問世,成了自己跳出來的右派分子。”(第1545頁)還有,五六十年代,他收藏的兩個版本的《金瓶梅》賣給舊書店,換錢買了雞蛋。還有,1936年施蟄存開始著手寫作長篇《銷金鍋》,“以南宋首都臨安為背景,寫當時的國計民生情況。正在累積史料,動手寫起來,想不到爆發了抗日戰爭。……如果沒有戰爭,我肯定會寫一個長篇。”(第328頁)
有一句話倒是可以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他說:“魯迅是從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從革命走向古碑。”“這是一個諷刺。”我突然翻到一頁,施先生編《現代》創刊號時才二十八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