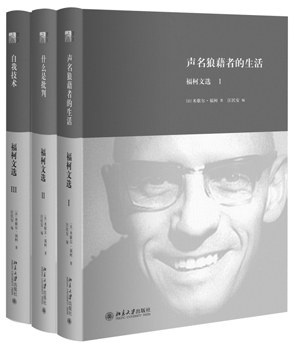
米歇爾·福柯無疑是極度迷人,乃至魅惑的。他學術興趣的紛繁龐雜、理論書寫的批判鋒芒,傳奇式的生死愛欲,都讓人為之著魔。或許,福柯正屬于思想的暗夜:無論在研究領域抑或行文風格上,都奇異詭譎,變幻萬端。他將巴洛克式的繁復修辭、綺麗浪漫的文學想象、幽冥晦暗的象徵隱喻融入理論之中,形成一種描述性的書寫范式。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福柯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和《福柯思想辭典》(重慶大學出版社)無疑能為理解魅惑的福柯提供重要幫助。
當我們談論福柯時,往往聚焦于知識型、話語、權力及主體等艱深術語,而福柯的藝術評論與美學追求卻常被遮蔽。《福柯文選》(《聲名狼藉者的生活》《什麼是批判》《自我技術》)則全景式、立體化呈現了福柯思想的全貌。所收文章從六十年代的“文學時期”至生前最後一次訪談,成為福柯專著及法蘭西學院講座之外的重要文本,具有極高價值。一方面,它從側面展現了福柯研究工作的“發生”(運思與計劃),對專著進行了大量補充性說明與變更性再闡釋。另一方面,書中諸多訪談及講稿也很大程度保有福柯書寫的“生態原貌”。
《文選》在縱向上展現出福柯理論的幾次興趣轉向,在橫向上又跨越了他關切的幾大領域(身體、權力、藝術與生存等問題)。它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福柯思想歷程的“脈絡圖”:從早期對知識、話語生成過程的挖掘,到對瘋癲與理性二元關係史的審視;從對權力關係無處不在的微觀分析,最終回歸于一種“關切自身”的自我技術。然而,《文選》所錄文章雖話題龐雜,但卻深藏著一以貫之的主線:解構不同類型主體塑造過程(即主體化,它意味通過各種改造矯正技術,將個體之人塑造為符合各種標準化的主體),同時探尋如何重構新型的倫理化審美的主體。因而,在本質上,《文選》關注的是從外部“規訓技術”(如權力對身體施加各種控制與懲罰)向內部“自我技術”的轉變與協調過程。
一方面它批判了知識將人塑造為“真理主體”(人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成為知識的客體對象),權力技術將人進行改造,生產出符合要求的馴順化身體(如工廠、軍營、學校和監獄中的矯正、訓練)。另一方面,福柯將個體的生存藝術作為理論追尋的旨歸,自我技術就是自我關注、自我改變、實現升華的自身支配手段。“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係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見《自我技術》)這意味著,個人藝術實踐(形成審美主體)正是自我技術(形成道德主體)的一種典范形式,後者天然涵有前者。藝術書寫與自我技術成為《文選》的雙重鳴奏與完美和聲,形成關切自身的生存美學。
《聲名狼藉者的生活》探討了權力技術怎樣滲入日常微觀生活,邊緣人群生存如何被納入到書寫與話語體係之中。福柯描述權力、生存與文本的三元關係,開拓性地審視了權力對文學的滲透作用。該文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文學選材觀:只選取體現生命原本的強烈力量(如悲慘生活的古典風格美、故事中的暴行);介入現實的文學功用觀:不僅要涉及現實,更要在現實中起作用,成為對現實的“復仇”與“戰鬥”。在主人公設置上,該文更顛覆了古希臘悲劇與法國新古典主義的傳統:他們不是英雄,沒有高貴家世與聖行。相反,他們是聲名狼藉者:低賤、卑鄙,被惡意與厄運刺激出生命能量。“正因為其微不足道,難以察覺,方顯能量之巨大。”
福柯意在揭示權力機制將生活日常納入話語體係的過程,“它們(生活日常——引者注)之所以可以被描述、被記錄,正是因為它們被一種政治權力機制所滲透”。更為深刻的是,此文將文學置于話語權力、日常生活與知識真理的整體布局中,標示出一種現代意義上文學的典型特徵: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它只有依托于社會話語的潛在規定,才有位置,得以生存。
表面上看,這種文學宣言遠離了藝術的審美性,將文學作為話語體係的衍生物、附屬品。實則,這正是福柯的別具一格:他強調文學活動始終是自我生存的實踐,書寫行為就是關切自身命運的生存方式,它不能擺脫外在權力關係、脫離社會話語。《通往無限的語言》《僭越序言》與《外界思想》又成為他“文學時期”的三部曲。在文中,福柯表現出對巴塔耶、布朗肖及薩德等人的迷戀,這里的原因是復雜且多重的。
首先,“僭越”與“外界”對福柯一生都造成了巨大誘惑。他總是將研究目光投向瘋癲、死亡或性等邊緣領域,他的一生更是僭越各種規訓設置的邊界,永遠追求外界經驗的歷程。為此,福柯關注毒癮、同性戀及性虐等極端身體經驗,並曾在迫近死亡時,表現出對死亡的沉醉。在常人看來,這無疑極度瘋狂,但也許正是這些“外界經驗”才使福柯產生了超越學院、無可效倣的魔力,形成了風格化的體驗哲學。
其次,在巴塔耶等人身上,福柯看到文學語言完全能夠突破語言反映論、工具論等傾向,最終上升為一種語言生存論。在文中,文學語言始終與生存、死亡、空間相聯係,與其著作《詞與物》《臨床醫學的誕生》的主題形成照應。在他看來,文學語言是無限的自我重復與增殖,是在自己的空間內進行多重鏡子的折射遊戲。為何以多重鏡子的反射來譬喻文學語言?這是因為它能夠造成折射的無限循環,象徵著文學語言永遠抵制著死亡的迫近,追求一種永生與無限。
福柯並未簡單將書寫視為藝術活動,而是視作生存的技藝,一種作用于靈魂、思想層面的自我技術。書寫成為福柯藝術關切自身的集中體現。在《自述:言說在死後開始》這篇訪談中,他自述了寫作在人生中佔據什麼地位,對他究竟意味什麼。這一問題或許從另一事例中就可窺見端倪。早在福柯醞釀創作《瘋狂史》之前,他的精神狀況就陷入某種令人擔憂的困境,寫作的過程卻奇跡般緩解了精神崩潰的危機。文中,福柯的回答始終聚焦書寫對生存的意義:它創造自我可以棲居的語言空間,它“為了隱藏我們的面孔,在我們自己的書寫中埋葬我們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指定、展示、顯露自身之外的某種東西”。
《自我書寫》《論倫理學的譜係學:研究進展一覽》《自我技術》則將目光投向古代,從古典自我中探尋現代主體生成的線索。“自我書寫”所凝集的自我關注、自我塑造也成為“自我技術”的典范。“自我書寫”首先是書寫自我。它與生活構成了互補,既緩解了獨居的危險,又成為對所思的凝視。其次,它成為對靈魂內在衝動的約束與搏鬥,是自我的教化。更重要的是,自我書寫完全是自身靈魂修練的操演,時刻關聯著沉思、反省與沉默的銘記。它是“關于思想本身的訓練”,其目的完全為了形塑自我。那種為他人書寫的作品卻是很遲才出現的。福柯以古代“個人筆記本”為例,指出自我書寫的最高目標:即“回歸自我、接觸自我、與自我一起生活、相信自我、從自我中受益和自我享樂”,這正是自我技術的旨歸。
以自我技術為核心,福柯晚年將研究重心轉移在藝術與倫理,自我與自身關係的探討上。在《何謂直言?》與《說真話的勇氣》中,他談論了“直言”對自我塑造的作用,這與自我書寫形成完美契合。“直言”的意義在于它坦率、完整、毫不遮掩地向他人說出一切。它既確定了一種言說者與言說內容的一致(直言者相信自己是在“說真話”),又確定了信念與真理的一致性(直言者堅信自己所說即是真理)。同時,只有當直言者面臨生存危險時(如被治罪、驅逐或處死等),當言說真理被內化為一種責任時,才可稱為直言。福柯無疑將原本“直言”的政治意義推及到哲學層面:它是一種生活的藝術,督促個體“關心自己”(智慧、真理及靈魂的完善),以實現精神指引與靈魂教化。
福柯沒有局限于對具體藝術形式(文學、繪畫、電影等)的評論,也並未止于對靈魂層面“自我書寫”與“直言”的探討。他更兼顧了身體修行的技術,徹底將人的身體、生存視為“藝術品”,將各種生活技藝視為藝術實踐。福柯強調自我技術的自由實踐(如節欲是對身體欲望的自主控制、“性藝術”是對自身快感的享用等),不僅走向一種實用主義的審美日常化,更形成了看重身體訓練與治理的身體美學。這是立足于生存美學的“大藝術觀”:“我們必須把自我、我們的生命、自我的存在當做藝術的主要工作來給予關注,並且把它們視為我們應用美學價值的主要領域”。
時至今日,西方結構-後結構主義思潮已逐漸退潮,後現代性的迷戀也被當代性的追求所驅散。然而,福柯的思想卻始終是未竟寶藏,總是給我們帶來驚喜、訝異和震撼。這是因為他從結構主義中走來,又超越了結構主義;批判了理性中心主義,又從不承認是非理性主義者;解構著主體化過程,又同時建構著新型主體(道德主體、審美主體)。福柯就是那麼難以捉摸,因為他總是充滿著斷裂。
正是這種無處不在的“自我變更”,永遠將領域本身“問題化”的思路使他的書寫具有極強的變異性與靈活性。福柯本人更與其理論品質形成某種照應:無論是批判性、反抗性,還是研究領域的邊緣性,生活經驗的獨特性,都使他成為繼尼採和弗洛伊德之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廣的思想家之一。而這只是魅力一角,那更深層倣佛來自地心的吸引源于福柯留給我們的“美學遺產”。它是個體生存與藝術實踐、身體存在與藝術載體、“生活藝術”與學術書寫高度合一的偉大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