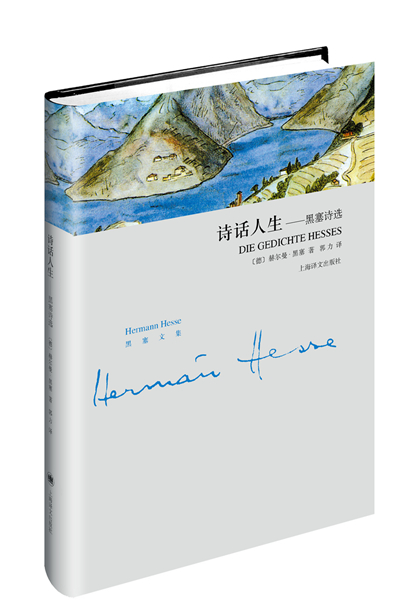
書名: 《詩話人生----黑塞詩選》
作者:[德] 黑塞 著
譯者:郭力 譯
ISBN:978-75327-7015-1
出版時間:2015年8月
【內容簡介】
赫爾曼 黑塞是德國傑出的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43年黑塞的《玻璃球遊戲》出版後,沒有再寫過小說,他一生一直都在進行詩歌創作,去世前一天還寫下最後一首詩《殘枝嘎響》。在黑塞寫詩生涯的近70年間,共做詩約1400首,其中800多首由他親自編輯成15本詩歌選集。最後一本為《人生臺階》,出版于1961年。除分別于1942年、1950年、1957年出版的三本《詩歌總集》外,其他12本在他生前出版的有:《浪漫之歌》(1898)、《詩集》、(1902)《在路上》(1911)、《孤獨者之樂章》(1915)、《畫家的詩》(1920)、《詩歌選集》(1921)《危機》(1928)、《夜的慰籍》(1929)、《生命之樹》(1934)、《新詩集》(1937)《花枝》(1945)《人生臺階》(1961)。我們選了作者的275詩,分少年篇、青年篇、中年篇、老年篇、晚年篇五大部分集一冊;本書的另一特點是:其大部分詩歌都附有解讀式的題解和背景材料,它們串聯起來就等于一部作者小傳,這一方面起了個賞析作用,一方面也為讀者全面了解黑塞提供了一個詳實的史料。
【作者/譯者簡介】
赫爾曼 黑塞(1877—1962),德國作家,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本書收集了作者275詩,分少年篇、青年篇、中年篇、老年篇、晚年篇五大部分.本書譯者郭力1991年留學德國,現定居在德國,目前為弗萊堡大學漢學係漢語教師,並專事中德—德中文化、文學翻譯交流。
【精彩書摘】
獻 詞
這些歌兒乏藝術,少光亮,
無所雕飾,它們在花谷里唱響,
可創作它們的心,是熱的,
我總是發自內心吟唱。
教我唱的,並非什麼智慧,
快樂的歌就誕生于我胸膛;
如果歌兒,在春之山谷唱起,
隨著風兒,它又會逝于晚霞旁。
如果你能理解,在玩笑樂趣與痛苦中
我將什麼當做了神聖,
如果在這些歌中,你能將我年輕的心讀懂,
那便是我所期盼的報償。
(1892夏)
題解:這一年是黑塞青春期狂飆突進、危機重重的一年。在毛爾布隆修道院中學,14歲黑塞的理想同學校經院式精英式教學體係發生了劇烈衝突。1892年3月7日,他從毛爾布隆修道院中學逃出,第二天家人才收到他平安返校的電報。後來人們了解到,這一夜他是在零下七度的野外一個茅草垛里度過的,。
為他的一時“糊涂衝動”,黑塞必須受到處罰。他從半夜12點半一直被關到早晨8點半,關了八個小時的禁閉,這個期間沒有吃喝。返校後,他萎靡不振仍然不能正常就學,5月7日父母只好將他帶到巴登鮑爾一個牧師朋友的療養院。
黑塞在療養院的日子本來還算悠哉遊哉,可他結識了一位名叫奧格妮的年輕姑娘,盡管女孩比他大7歲,可他對她仍一見鐘情,不能自拔,不斷給她寫情詩。受到婉拒後,他的內心又一次失去平衡,他羞愧已極,甚至買了手槍,威脅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兩天後,在牧師建議下,他被送往專門收治有精神障礙青少年的施德藤宮安定療養院。
整個七月份他都在這家安定院度過,父母讓他住院的決定令剛滿15歲的小黑塞憤懣不已,心靈受到極大傷害,使他一時產生了很強的叛逆心理。這期間他寫下23首獻給奧格妮的詩,這里便是其中一首。
【譯者序】
黑塞從小就表現出特殊的文學天賦。他不到五歲時,母親在日記中寫道:“他一天都在說韻文,哪些詞跟哪些詞合轍押韻,他總會找到,而且常很成功。”
黑塞9歲時,就讀于家鄉卡爾夫的拉丁語小學。正是在這所學校,小赫爾曼在讀課外讀物時,第一次受到了強烈的文學震撼。那是當他讀到荷爾德林的詩作《夜》中的詩句片斷時:
夜,來了,
對我們不睬不理,身披滿天星光,
這個人間異類,一臉驚異,晶瑩閃亮,
它憂鬱、輝煌,群山之巔,緩緩而上。
黑塞近60歲時,在回憶文章中還記下了當年受到的內心震撼:“這就是文學創作!這就是文學家啊!這些不可思議的詩行對我這個小男孩沒有確切內涵,可它們卻如此神聖,讓我第一次對父母語言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受。在我的耳畔,它們的聲響如此強勁,就像在對我宣告想象力的神奇,宣告文學創作的奧秘……”
正是在這所拉丁語學校,黑塞從12歲起便下定決心:這輩子“要麼當文學家,要麼什麼都不當”。然而他的家庭卻希望他能成為一名傳教士,做神職人員。因而從少年時代起他同家庭、學校衝突不斷,為自己的理想進行了頑強抗爭。最後他終于通過自己的努力走上了文學之路,實現了當作家詩人的少年夢,並成為20世紀世界矚目的傑出作家。
黑塞一生著書眾多,不光有廣為讀者喜愛的小說《彼得 卡門青》、《悉達多》、《在輪下》、《納爾齊斯與歌爾蒙德》、《東方之旅》、《荒原狼》、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玻璃球遊戲》等,還創作了眾多水彩畫作,出版了不少詩畫隨筆集。
黑塞的文學創作,以詩歌創作為始,又以詩歌終結。他的第一本詩集《浪漫之歌》,收集了他從15歲開始的詩歌創作。而最後一首詩《殘枝嘎響》,完成于他去世前一天。
在黑塞詩作生涯的近70年間,共做詩約1400首,其中800多首由他親自編輯成15本詩歌選集。最後一本為《人生臺階》,出版于1961年。除分別于1942年、1952年、1957年出版的三本《詩歌總集》外,其他12本在他生前出版的詩集是:
1.《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1898)
2.《詩集》(Gedichte,1902)
3.《在路上》(Unterwegs,1911)
4.《孤獨者的音樂》(Musik des Einsamen,1915)
5.《 畫家的詩》(Gedichte des Malers,1920)
6.《詩歌選集》(Ausgew hlte Gedichte,1921)
7.《危機》(Krisis,1928)
8.《夜的慰藉》(Trost der Nacht,1929)
9. 《生命之樹》(Vom Baum des Lebens,1934)
10. 《新詩集》(Neue Gedichte,1937)
11. 《花枝》(Der Bl徂tenzweig,
12. 《人生臺階》(Stufen,1961)
作詩之于黑塞
黑塞是一位很著魔于詩作、又希望受到認可的詩人。1904年27歲的他新婚後與妻子搬到博登湖畔。當時作為自由撰稿人他總是一個筆記本不離身,隨時記錄他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與思考。筆記本里甚至記有一段他的“文學墓志銘”:“這里安息著詩人(Lyriker)黑塞,可惜他生前沒有得到這樣的認可,卻被當作娛樂作家受到過分重視。”寫這段話時,黑塞30歲。
1909年,在給一位編輯朋友的信中他寫道:“很高興您喜歡我的詩,這些詩也是我最喜愛的;就算笨讀者更喜歡我的小說,對我來說,一首好詩還是頂得上三部小說。”
這時候的黑塞詩作很少考慮讀者。他認為,作詩首先是個人私事,是“世界在自我個體中的反射,是‘我’對世界的反應,是抱怨,是沉思,是自覺自願完全孤獨(Vereinsamung)的遊戲。”
他需要了解自己,需要記錄自己的生活經歷和體驗,而不在意人群標準。1898年21歲的他在一篇關于詩作的文章中寫道:“一首詩是一種發泄,一種呼與叫,是嘆息,是某種表情或手勢,是心靈對某一經歷的反應——在這個反應中,心靈需擺脫由經歷引起的內在翻騰,還需在其中變得愈發自覺。”這就是說,他首先要用韻律語言組織表達他的感受。詩歌之于他是具有治愈能力的“心靈舞步,是理想畫面,是文字表達的神奇方式”。至于它們是否能在技巧、形式上取得成功,是否具有超個人價值,開始時都是次要問題。如他一次寫道,寫作“不好的詩,可以比閱讀最美的詩更令人歡愉。”因為它“可化解痛苦”,甚至可使痛苦“通過不慎流暢的韻律,轉化為愉悅。”
1902年4月24歲的詩人給朋友寫道:“詩人寫詩完全為自己,不會想到為什麼讀者。小說的作者則不同,他寫作,是因為他要面向一群人,要對這些人講故事,並知道如何影響這些人。”
對黑塞來說,詩歌也是對印象的表達,就像他40歲後在水彩畫方面的嘗試一樣,借此方式可表達某一時刻的感觸。
黑塞喜歡將他的即時詩作加入他的小說故事中,融匯到情節里,讓小說得到文學形式上的豐富。因此在他大部分書籍中,詩篇常被用作引子,比如《赫爾曼 勞舍爾》中的《露露》,《彼得 卡門青》中的《伊麗莎白》,《克諾爾普》的旅行詩,《克林格索爾的最後夏天》中的畫家之歌,《悉達多》中的《通往內在之路》,《荒原狼》的組詩《危機》和《玻璃球遊戲》中年輕人約翰的思考組詩等。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黑塞也沒停止詩歌創作。對此他在二戰期間表示:在世界大戰的當口,一個作者在這個時候還玩這種看上去世人陌生的遊戲,他是不是沒有更理智的事情可幹了?不過“比起大多數人來”,他認為,他的確做了“更好的事情,做了一些沒有破壞性、無足輕重然而美妙的事情”。他沒有去射殺、去轟炸、去放煤氣或去制造彈藥,而寫出了詩篇。
他還寫道:“你也可以這樣解釋:在這個明天就可能遭毀滅的世界里,詩人不過採摘了他的詞匯,播下種去, 又進行了選苗,就像對正在草坪上生長的蓮銀花和報春花一樣。這些草坪也許明天會被榴彈炸毀,會在毒氣中窒息。但花朵(的構型)不會受這些可能性的影響。它們還會精心孕育花萼和花瓣:或是四瓣,或是五瓣,或帶著光滑的邊緣,或呈鋸齒狀,但都極盡精致而美麗。”
從這樣的回答可以看出,對黑塞來說最重要的,要用重建對待毀滅,要用盡可能不被強制的內在世界去排除外界的強制,即便會被世人視為怪物和保守。這個意願看上去貌似單純和美猶如自然景觀,如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一切的一切……如它們所展現的,都是自然使成;而如果被眼睛看到,便是奇觀。”
從靈感之作到推敲之作
有些黑塞專家認為,從黑塞詩作手跡看,他寫詩不同于寫散文,對自己的詩作他永遠會用不滿足的審慎目光不斷進行修改,加工,刪除,甚至重寫,他要讓詩歌贏得輕盈的樂感,讓它不再像編的,而成為自然而然的一體。
比如他的《伊麗莎白》第二部,關于這首詩的寫作,1901年7月30日,24歲的黑塞在給他《詩集》第一發行人的信中寫道:“您很喜歡《好像白雲》這首詩,我很高興。夏天我喜歡在盧塞恩湖里劃船,我常在那兒獨自劃上幾天或幾個星期,一邊劃還一邊輕聲唱歌,唱些沒有意義的詞兒,唱意大利文,唱流行歌曲,或者隨口唱些想出的韻文。一次在望見美麗夏雲的瞬間,這首詩便蹦出了我的唇,我根本不用找詞了。不自覺地唱了兩三遍,我才開始留意其中的詞匯,好回家寫下。我的大多數詩都是這樣寫成的,不過沒有哪首像這首讓我稱心如意。”
可以說這樣的創作是他年輕時的詩作特點。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寫作內容的復雜多樣,這樣的即興之作也越來越少。
黑塞對 《吹笛》一詩的創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對這首詩的創作,二戰期間1940年4月,62歲的他在給最小的兒子——三兒子馬丁的信中寫道:
“隨信寄上一首新詩最後的修改稿。這14天里,我除了處理些該處理的事務,就是對這首詩改來改去,別的幾乎什麼都沒做。它原有8行,現在成了12行,就這樣吧。沒錯,事情挺奇怪:當今半個地球都在墳墓及掩體中,在船廠和工廠之中。碉堡林立,戰艦遊弋,一副定要將我們的世界完全變成塵埃碎片的陣勢。而我卻整日為一首詩的完美斟字酌句。是這樣的:這首詩原本有四段,現在改為三段,我希望改得更好了、更簡潔了,主要的內容也保留了下來。第一段的第四句,一開始我對它不滿意,那顯然是個應急措施,每次給朋友抄這詩時,抄到這句我就會不舒服,覺得越來越不開心,越來越有殘缺,越來越反感。所以現在我要將它一字字一句句地再認真推敲,看看缺陷到底在哪兒。也許有人會問,這工作有什麼意義?百分之九十的讀者不會注意到這首詩還有它的修改稿,盡管也會有個別人做出奇怪的反應。有件事我不會忘記,盡管這是30年前的事了。有個讀者向我索要一首詩,他是在一本雜志上讀到的,這首詩中的八句他能背下來,可其間有一句忘記了。當我找到這首詩時,我發現,這一句正是這首詩中薄弱的一句, 在草稿上我就劃過問號,可長久以來卻將它忽略了,它正是需要修改的地方!”
簡潔樸實,拒絕新潮
黑塞的詩作題材源于生活而非生僻遙遠。他具有用簡潔語言表達復雜問題的能力,用畫面表達思想的能力;還具有與其選用隱諱比喻而更樂于直接表達的傾向。
黑塞寫詩非常重視節奏和押韻,因此他的詩大部分都很押韻。因為詩作對黑塞來說不只是表述,“當詩歌的內容借助人為煉金術的手段越來越多地精煉成某個形式、風格、曲調的時候,它便成了創作。”對他來說,“音樂藝術是基本要素,它是詩歌發源及歸宿。”
不過還是有大約50首詩作(佔他公開發表詩作中的二十分之一),缺少“柔和韻律”,沒有“元音的樂動”…… 如他在一次描述詩的音樂效果時描述的。
一般的詩歌創作常會因為誇張的遣詞,使詩篇顯得不真實,顯得故作姿態和裝腔作勢。相比之下,黑塞的詩篇都較清新,沒有很多修飾,它們的表達方式不受評論家左右,且可被各個年齡段的廣大讀者接受。
黑塞堅持以韻律詩表達他的情懷,這樣的理想在他不少詩作中得到了成功體現,這也是黑塞詩作廣為大眾喜愛,流傳甚廣,且很多音樂作曲家都願意為他的詩歌譜曲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黑塞的新詩集《孤獨者的音樂》出版時,法國著名作家、音樂評論家羅曼 羅蘭給黑塞寫信道:“算您幸運,我不是作曲家。否則我無法控制自己,不為您的詩句寫下音符。您的詩句,樸實簡潔,句句直抵心扉。”
為黑塞詩歌譜曲的事例,最早出現在20世紀前夕,而最近的一次是在1977年,這年奧地利作曲家艾內姆(Gottfreid von Einem)同舒克斯(Othmar Schoecks)為黑塞一首早年詩作譜了曲,並通過德國留聲機協會灌制在唱片上傳播開來。據稱,德國20世紀的詩人中,沒有哪一位像黑塞這樣,其詩作受到如此頻繁的譜曲。到目前為止,由黑塞詩作譜曲的歌曲已達4000余首。
關于黑塞詩作的風格,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特奧多爾 豪斯(1913年他曾接管黑塞創刊的左派雜志《三月》),做過如此評價:
誰感覺不到這點:在當今常具強制性的“目的詩歌”之間,遠離評論家們的蹩腳評論(評論也是他們的權利),做這樣一位詩人的讀者有多麼愉快?!重要的是,他不是記者,而是藝術家。黑塞的那些詩行,放棄了抗爭,是成熟硬澀的陽剛花朵,又是沉靜堅實的步履,為讀者熟悉,並讓我們樂于追隨,因為它們會將我們引向尚未受到玷污的殿堂!
這句話給筆者的啟發是,我們中國人喜歡用“青澀”一詞形容青春不成熟狀態;如果說某人的文筆很澀(很可能是艱澀),一般為貶義詞,說明不流暢、生僻、難讀難懂。而豪斯竟將黑塞詩行說成是“成熟硬澀的花朵”,這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在這里花朵不過是藝術成熟階段的象徵。試想,並非所有果實都甜蜜、可口,因而“澀”對德國人也是一種成熟美,有它的章法與追求。
正如前面所述,黑塞的詩深受德國人民的喜愛,因為他的詩歌語言簡潔樸素(Einfach und schlicht)。在這點上,也有過評論家提出過批評。對此1926年黑塞在給一位評論家的信中寫道:“您對我提到的那些詩,都是我去年冬天的新作。從美學角度上看,它們可能沒什麼價值……不過,你們那些美學標準在我看來也很值得懷疑……我放棄美學追求已經多年了,我不創作而只想自白,就像溺水者或中毒人不再能顧及他們的頭型和變了調的聲音,而單單要呼喊一樣。”
我譯黑塞詩歌與致謝
筆者最初接觸到黑塞詩歌,是在1982年錢春綺先生翻譯的《德國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中。1991年筆者自費到德國留學後,在房東老太太書架上見到一本《黑塞散文詩歌集》,粗粗翻讀了幾頁,便印象深刻,希望翻譯黑塞詩歌的想法油然而生。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中,黑塞年少時及老年時的詩作從內容和風格上看都迥然不同,我們雖然有了一些譯本,但因缺乏詩作的背景資料,讀起來難免有一些不易理解之處,這也不免令人遺憾。比如黑塞23歲時寫下的愛情詩《伊麗莎白》被當成中老年作品;wandern一詞一般被翻譯成漂泊,黑塞被稱為漂泊詩人。漂泊,顧名思義,隨漂而泊,讓人感到被動、無奈、窘迫。然而Wandern一般指德國人喜聞樂見的徒步行及遠足活動,一般是有固定居所的修身健體、開拓視野、體驗生活的行為。規模小的可說成散步,規模較大的便具有中國文人“行萬里路”的人文精神,是一項精神內涵豐富的活動。
筆者開始著手翻譯黑塞詩歌時,也因為這些資料的缺乏而幹脆放下筆來,去研究黑塞生平,閱讀了幾本黑塞生平及參考書後,又轉回來翻譯他的詩歌。
盡管如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還是遇到了許多困難。有德國朋友對我說,黑塞詩歌很受德語讀者喜愛,但要真正讀懂也不很容易。對我來說,翻譯如破謎;在每首詩的翻譯上,我都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果說平均每首詩我有四個問題的話,那翻譯這270多首詩,我至少遇到了1000多個問題。在此,如果沒有眾多友人的幫助,我的翻譯工作是無法想象的。
在此,譯者要特別感謝對我的翻譯工作始終給予了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他們是譯者的先生Richard Wilkinson、女兒林佳希、德國文理中學退休德語教師 Rolf M徂ller 先生、Kay Mestern 先生、Alexander K徂hn先生、Lydia Funk女士、Linde Wuttke女士、Wolfgang Bammert先 生、Dagmar M徂ller-Mobashery女士、Isabel Schmidt女士等。他們對我的解釋說明,筆者在書中或以“米勒老師”之名做了總結,或將之做了歸納匯總。
如前所述,黑塞詩歌的特點是用詞簡潔樸實,在翻譯過程中筆者也希望盡量保持這個特色;希望譯詩盡量押韻,但仍將表達詩的內容作為首要任務,因而常不得不放棄押韻上的努力。此外,在部分詩歌後面,以簡短的“題解”形式,盡可能簡略地介紹一些背景和相關的資料,這也是筆者希望填補的空白,以便讀者理解詩作。
郭力
于德國弗萊堡
2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