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的戰國策派:被忽略的偉大思想群體
採訪手記
與趙尋老師相識,是在弘道書院的一次研討會上。趙尋老師有關戰國策派的發言,讓人受益匪淺,耳目一新。為何如此卓有見識的思想群體,在幾十年之後卻湮沒無聞?會後,趙尋老師決定做幾期訪談,追溯戰國策派的思想,更追溯中華文明千年來的發展歷程。
趙尋老師有關嚴復先生的思想溯源格外值得重視,這是他即將出版新書里面的觀點,此次提前拿出分享。嚴復先生在文章中,第一次論述了晚清落後的原因,認為晚清時期的國人無自由,全是被帝王所奴役,而西方富強的原因則在于他們葆有一個社會……
嘉賓簡介
趙尋,200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先後任香港大學,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思想史,哲學和藝術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近代思想與文明》等。
戰國策派:被忽略的民國偉大思想群體
搜狐讀書宋晨希:您對雷海宗先生、賀麟先生有著深入的研究。雷先生和賀先生是“戰國策派”的中心人物,近年也不斷有對“戰國策派”的研究與回顧出現,您可否談談您的看法?這些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思想人物,在今天的世界語境中,能為我們提供什麼樣的啟示?
趙尋: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戰國策派”是真正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長期以來,他們的著作,除了極少數例外,如賀麟先生,都幽靈一樣散落在各地不同圖書館的“保存庫”,或N字打頭的“內部書目”中。
去年11月,“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雷海宗、林同濟卷”出版,雷卷粗估超過50萬字,新發現了雷先生在報刊發表的大量文章,和此前整理出版的論著結合在一起,可以比較全面地窺見其四十年代的思想歷程;這是一個突破。林卷卻未能在《天地之間》(2004年)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拓展。而陳銓、何永佶等人的情形,則幾乎沒有改觀:“民國思想文叢 戰國策派卷”(2013年)收入何文近十篇,但較之九十年代出版的《時代之波》文選(何僅收一文),整體上進展甚微。而事實上,陳、何二人,著述甚豐,絕非泛觀可了。
除了資料方面的限制,上世紀四十年代“意識形態戰”——不是1910年代的“思想戰”——的沉重負擔,更深刻地制約著“戰國策派”研究的進展。到今天為止,充斥人們視野的,依然是那種孤立、刻板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傳聲筒的“德國策”形象。
然而,除陳銓一人留學德國外,其余人接受的,都是美國學術訓練——賀先生也是在哈佛獲得碩士學位後赴德,一年後即提前回國。在他們的論著作中,除陳、賀二人因學術專業與德國有關,不時涉及外,包括林同濟在內都並不如何經常提到“德意志”。尤其是雷海宗先生,以我的閱讀而言,除一篇對哲學家Jaspers的書評,並無與德國有關的文字。至于其史學觀念與治史方法,與他在清華前後所濡染的梁啟超、陳寅恪,及在芝加哥大學所承受的美國史學大家James Westfall Thompson——歐洲中世紀史、早期現代史大家,芝大至今有其紀念大樓——的影響,如果不是有更深刻的關聯,也絕不在《西方的沒落》之下。硬以“文化形態史學”來看,雷先生也更接近湯因比,而不是斯賓格勒。
但我們的研究者,卻仍在以“德國思想在中國”的模式,無意識地延續這一策略。意識形態抹黑策略的效果,可見一斑。實際上,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他們相互之間雖不無共同之處,但學術背景、理論方法的差異,同樣明顯。

1927年雷海宗在美國芝加哥獲得博士學位
以內中居于中心位置,相似度看似很高的雷、林二先生而言,實亦大不相同:雷是典型的史家,講學論政,一皆出之以史的尺度;林究心政治,論史衡文,亦不忘政治的邏輯。以二人的史觀而論,雷先生的中國歷史五階段論,與林的三階段論很不相同——硬說地話,林先生更接近于斯賓格勒,而離中國歷史更遠。
與其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厚此薄彼,以至于連一些核心人物的基本情況,如早歲即揚名清華,哈佛政治學博士出身,僅在《戰國策》就發表過10多篇文章的何永佶,竟然連辭世的年份,至今也無法確定;不如從不同的維度出發,有分有合,呈現其作為一個時代中心人物的姿態。當然,如何讓“戰國策派”回歸其自身的思想史語境脈絡,則是新的工作展開的前提。
近些年知識界對“戰國策派”的關注,有一個背景,那就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的持續影響。亨廷頓的歷史理論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來源,那就是湯因比的,雖然其理論指向大相徑庭。而戰國策派則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做出了中國文明的的回應,那是對中國文明之世界歷史價值的貞定。完全不同于當下一些市儈的顛倒之論。
晚清墨學復興:西方的科技源于墨子?
搜狐讀書宋晨希:王爾敏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論文,追溯戰國策派的起源。他認為在晚清的時候,墨學傳統得到了復活,人們開始用先秦諸子的思想比擬西方的科學技術,比如科學技術其實可以從墨子思想里找到因子。您認為,戰國策派是否與這個思潮有關呢?
趙尋:七十年代末期,王爾敏先生在《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中提出,晚清墨學的重光對近代思想觀念如“科學”、“平等”的興起,有很大的推助;在總結“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時,也對戰國策派諸人倍加推崇:許之為“20世紀百年人才精英,為最傑出的學界領袖”。我完全同意他的論斷。但戰國策派與墨學的關係,卻可能比較復雜。

令墨學復活的《墨子間詁》
說晚清墨學的復興,不能不說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所謂“間詁”,就是行間注,夾注。很多人都說,此書一出,《墨子》從此成為一部可讀通的書。但《墨子間詁》絕非訓詁、疏證那麼簡單。孫詒讓與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交誼很深,故在“間詁”成書後,寫序點破:從仲容賢弟的書看,不僅是西人的光學、重學出自墨子,而且在《墨經》中的“備梯、備突、備穴”,也是“泰西機器之權輿”。這似乎仍有點“西學中源”的影子吧。
但他接著就說:“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也許只有以孟學為主,墨學為輔,才能夠“安內而攘外”,所以大家千萬別以為“間詁”是在敝精勞神,玩什麼無用的文字訓詁。原來,是身逢“戰國”,才讓他們決定讓墨子再次“出世”的。“今天下一大戰國也”這個判斷,雷海宗先生等人是否了解我不知道,但滄海橫流,天將大亂的感受,卻一定是共同的。
孟子曾以楊朱、墨子的為我、兼愛,為無君無父的異端邪說,深以天下不歸于楊,則歸于墨為憂。但俞、孫等人,卻以孟、墨為內、外輔弼,這就是時代的變化。但若說孫詒讓興墨的目的,和清中期的汪中、畢沅等有根本的不同,則不是事實。
《墨子間詁》是典型的清代“子學”的路子:以子解經,以子翼經。雖然以子解經,在客觀上提高了諸子的地位,使得子學終與六經等量齊觀,無形中開了從內部衝擊儒學正典的先河。但要說到以墨學為導引,與西學里應外合,開出中國現代的思想局面的,卻是繼之而起的梁啟超一代。
梁啟超:墨家有蘇俄社會主義的影子
搜狐讀書宋晨希:梁啟超是如何看待墨子的呢?據我所知,梁啟超先生曾經對先秦以來的諸子,都曾用現代視野進行了梳理。
趙尋:梁任公集中討論墨子有兩個階段。一是“新民叢報”時期。為了催生新國民,任公無所不用其極地調度了包括墨子在內、耳聞目睹的所有資源,有名的例子,如以墨子“非命”為辭,批判儒家的“命定主義”,鼓動“進取、冒險”,發揚“力行主義”——順便講,蔣公介石的“力行哲學”,即是從此而來。
又如以“利人即所以利己”,發揮“兼愛”之義:“墨子以實利主義,為兼愛主義之後援,其意謂:不兼愛者則直接以利己,兼愛者則間接以利己。”這就是說,兼愛是間接的利己。而間接的利己,不僅利己,也利國、利群,且長久利己、利國、利群。不過到了下一個階段,在1920年代的墨學著作中,這些卻成了任公自我批判和修正的對象。
原先因國家危亡而見重的“輕生死”、“忍痛苦”的墨家精神,轉而顯出“只承認社會,不承認個人”,只知道平等而不知自由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墨子的社會理想中,出現了蘇俄革命的影子!“墨子的新社會,可謂之平等而不自由的社會,揣想起來,和現在的俄國勞農政府,很有點相同。”任公並引太炎對墨學的批評:“墨學若行,一定鬧到教會專制,殺人流血!”對當時仍熱衷墨學的五四學人示警。其前後對立如此,愛恨變幻之劇,可想而知。
但這卻可能是墨學直接影響到“戰國策派”思維的時期。1920年代,是戰國策派主力求學清華的時代——以入學先後為序,何永吉是甲子級學生,1916年即已入清華,為最早,但因年幼八年後方畢業,滯留清華亦最長,而且熱心社團組織,是學生時代即已聞名者;雷海宗和賀麟為1919年入學,陳銓為1921年,林同濟為1922年。
他們在校時間相對集中,相互之間的往還雖尚不可知,卻有共同的交往對象,比如吳宓先生,假設他們此時彼此已有基本的了解,應不為過。梁任公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雖晚,但很早就在清華兼課:著名的《墨子學案》,即是其1920年冬在清華所講“國學小史”的部分內容。如此,至少,雷先生、賀先生、何先生三人,是不乏機會“親承音旨”的。
這不是說,戰國策派就只能接受梁先生晚年而非早年的墨學觀。事實上,外敵淩侵的現實,更容易讓四十年代的“戰國策”與世紀初的“新民說”,發生共鳴。只要客觀地看,任公對“國民性”病態的批判,與戰國派對“無兵的文化”、“官僚傳統”、“家族主義”等中國文明衰頹敗變根由的抉發與抨擊,明顯有其貫通一致之處。
但人們一向以“德意志思想文化”作為戰國策派的思想源泉,嚴責其對納粹主義的“認識不清”或“惡意鼓吹”,而對任公“新民說”背後的“種族主義”、“國家主義”邏輯,諱莫如深——即使劉禾等人只是用後殖民理論,在魯迅“國民性批判”的研究中,稍稍觸及到這一背景,至今收獲的也仍也只是情緒化的嘲弄:“魯迅上了傳教士的當?”
所以,盡管因戰國策派的研究開展太晚,很多重要的材料已不可能獲得,但我們仍要堅持近代墨學與西學傳播的這個假說,用以呈現戰國策派生長的中、長程背景,打破意識形態戰略下的“德國策”派的黑暗圖景。
“戰國策派”是五四之後,新一代以“國士”自期的知識分子,為謀興國的聚集。身逢亂世,想往華夏文明重光的迫切,容或使他們顧此失彼,但他們絕非權利的鷹犬,更非納粹德國的智庫。
百年前的偉人評選:黃帝和墨子上榜
搜狐讀書宋晨希:剛才談到墨學與西學,我想,作為一個文化積淀深厚的國家,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僅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全面西化,是否與中西之間的這種比附相關?
趙尋:肯定會有這個因素。《民報》創刊的時候,扉頁上有兩個古代人物的圖像:一是黃帝,從民族來源的意義上講,這還好理解。但另一個就是墨子,為什麼?墨子像上方的文字是:“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很明顯,“兼愛”被詮釋成了法國大革命精神的“平等、博愛”。這顯然是時代措置的謬誤。黃帝作為“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其實同樣很可疑:民族主義是極其晚近的意識形態,黃帝如何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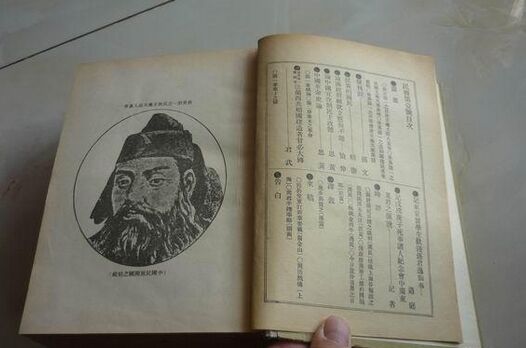
《民報》創刊號上的黃帝像
前面說,為了應對西方的衝擊,晚清學人用“內學”與“外學”,為一向水火不容的儒、墨作溝通。但這個“外學”,慢慢從科技,延伸到制度,後來更成為民族精神的依賴,完全取代了儒學的位置。所以,隨儒、墨互補的子學之墨而興的,不再是那種對墨、儒關係的申辯,像蒙文通先生對墨、儒合流的論證等等——蒙先生問,為什麼與儒學同為顯學的墨家,後來竟消失不見了?原來是融合到儒家里去了。
墨學促五四知識人“打倒孔家店”?
搜狐讀書宋晨希:那這些“格義”,究竟有沒有對中國思維的轉變起作用?
趙尋:如果講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革命性轉變,用雷海宗先生的話講,有兩個方面的變化最重要:一是體制,一個科舉。體制的變革,以1911年君主制的瓦解為標志;科舉的廢除,則在此前的1905年。二者分別代表著“政治與文化”的劇變,但都主要是通過外力,以直接的、政治革命的方式造成的。
但因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一向以儒家為中心,革命之後繼起的,一定是有別于儒家的內容。但即使是有別于儒家的,也一定會在意識形態的層面,與儒家發生關聯:一向被儒家視為異端邪說的也好,旁枝末節的也好,都一定會以非儒或反儒的“先驅者”的面目,與儒學發生關係。
這是我們觀察中國近代思想流變時,需要特加注意的。從這點上看,一向與儒學對立的墨家思想,確實起過不小的作用。即使是五四時代,在破除家族主義、君主主義,興起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等方面,仍到處有墨家的旗幟飛揚。郭沫若到五十年代,回憶及此,仍說“當年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雖涉誇飾,卻是實情。
如此,我們就可以在外緣的、直接性的、事實因素,與長期性的、緩慢變化的精神要素之間,建立一種動態的平衡,放寬歷史的眼界,發現在那些事件的硝煙與亮光之下的歷史場地,發掘在歷史的皺褶之處隱藏的斷裂與轉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作無謂的、別有用心的“格義”。
嚴復為何發文稱甲午戰敗不可悲?
搜狐讀書宋晨希:挖掘歷史的皺褶,是後現代史學的一個主要特徵。如果從這一立場出發,怎樣重新審視戰國策派的興衰?
趙尋:晚清以來,籠罩一個半多世紀的潮流,可以概括為“富國強兵”四字——也可以用一個字來說,那就是戰國策派一些人喜說的“力”,power。幾乎所有的診斷,都下在使中國不能富、不能強的貧窮、衰弱的病態上。所有的人考慮的,也首要是,如何恢復民族的生機、國家的活力?如何自強?
1947年,雷海宗先生寫《自強運動的回顧與展望》,把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現代史概括為一部六個階段的“自強失敗史”與“失敗再圖自強史”,認為日本雖已倒下成為人家的傀儡,但中國仍在蘇聯的圖謀之下,不能自安,唯有繼續圖強。 但是,“富強”豈止是戰國策派興起時的世紀潮流?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今天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我們不仍處在“大國崛起”的夢想之中?所以,如果要做真正的歷史反省,就不能不涉及到它的“效果歷史”,不能不涉及它對當下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只能從頭說起。
“富國強兵”的成為潮流,始于甲午之敗。首先發難的,是在甲午海戰中創深痛劇的嚴復。盡管並未親入戰陣,但前線浴血戰死者,不是留英的同學,便是北洋水師學堂的友朋、同事和學生——自1893年來,嚴先生已是學堂名義上的“總辦”——據說,他又與前線書信極密,周知戰事,故敗訊傳來,久鬱胸中的怒吼,便再難抑制,一氣寫下著名的《直報》五篇:
《論世變之亟》1895年2月4-5日刊出時,威海衛實已陷落。故《原強》、《辟韓》、《原強續篇》,遂如連炮,在3月4-9、13-14、29日《直報》,接踵而至。《救亡決論》雖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寫成,但悼往傷來,感時憂國,情懷完全一致,學界一向稱為“《直報》四論”。但嚴先生極重《原強》,後來曾有大改,且《原強續篇》也另有“作意”,還是稱“直報五篇”為好。

嚴復
《直報》五篇是嚴復一生中最令人驚天動地的文字。有人說,五篇中如《辟韓》等,有推卸責任或“棄北(李鴻章)投南(張之洞)”的謀劃,那是看錯了“五篇”的背景,無感于嚴先生盛年的淩厲悲風。
但之所以說驚天動地,卻並非因為如史華慈所說,嚴先生突然恢復了他一向不太充沛的“公民勇氣”——相反,恰恰是因為過于熱烈的公民情懷,議論縱橫,才不為當年一手遮天的上司李鴻章所喜,投閒置散北洋十五年,無所建白——末代太傅陳寶琛在嚴復墓表中記下這個過節,以及琉球被割後嚴先生痛心疾首的一則預言:“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只是嚴先生也沒有想到,不到10年,日本的繩索就套向了中國,這頭亞洲文明的年邁母牛!
“五篇”的驚天動地,也不是因為嚴先生終于在火一樣的激情中,說出了他一向深自晦韜的對達爾文和斯賓塞的信仰。在甲午之節節潰敗的舉國震驚中,嚴先生以“吾輩一身即不足惜,然如吾子孫與中國之人種何?”的亡國、亡種之悲,慷慨陳詞:戰敗並可悲!真正可悲的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民氣之已困。”而“民力、民智、民德”的發揚,只有“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才是西方富強的秘密,才是日本制勝于疆場之關鍵。很多年前,當我在“五篇”中反復讀到嚴先生有關“自由”的論斷時,仍有如受電擊之感,其對20世紀初期前後風雨飄搖之中國人的震撼,更當何似?但在我看來,這仍不是“五篇”之所以驚天動地的所在。
“五篇”真正令我驚心動魄的所在,是其所揭示和定義的,是作為社會狀態的民主!這一對民主的社會定義,不僅一舉打破了晚清以來在“君主”、“民主”之間膚淺格義和文字遊戲,而且直指現代社會的成立的根基:“自由”,並使之——“自由”——由此成為一個現代概念,成為“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概念!
“《直報》五篇”及“嚴譯八種”,雖未享有托克維爾名著《美國的民主》在美國的榮耀,但嚴先生對十九世紀英國的觀察及其對啟蒙思想的思考,確有超越其西方本土的價值。一些西方的有識之士,如史華慈,也已有論列。反倒是,兩個甲子以來,吾人在承受嚴先生以其烈士情懷貢獻給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的恩惠同時,一直在有意無意地誤讀、誤導這一價值的精神方向;其中尤為嚴重的,是在“民(種)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威權政治”的途徑上,對嚴先生的扭曲和利用。這其中就包含了“戰國策派”的某些思想家。
嚴復揭秘西方富強原因:葆有一個社會
搜狐讀書宋晨希:這太令人震驚了!您能簡單界定一下作為社會狀態民主的意義嗎?
趙尋:在晚清的輿論氛圍中,由獨裁君主統治的國家如沙皇俄國和明治日本,卻被稱為“民主”國家:因為,據說,它們依據法律和人民的利益進行統治——在古文中“民主”和“君主”的意義,確也並無區別——這就相當于說,存在一種“民主—君主制”。
這顯然是對“民主”的濫用。嚴復必須進行一種根本性的區分,既符合他對十九世紀英國社會的實地觀察,又能揭示三種制度的根本區別。甲午之敗,使他終于認定,人民是否真正擁有平等參與各級政府事務的權利,亦即是否存在“政治自由”,才是民主與否的關鍵所在。因而,他把無條件的平等,作為民主的定義和現代社會的前提。
在《論世變之亟》中,嚴先生在列舉“與華人言西治”的種種困難之後,合盤端出:中、西之道的根本區別,在“自由不自由”的差異——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
然而,為何作為與生俱來的稟賦與權利的自由,在中、西思想之間,竟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嚴先生的解釋,是令人驚心動魄的,遠遠超過了對中國歷古聖人皆不敢言自由的譴責:中國的(舊式的)自由,不過是“專以待人及物”——亦即不關于自己——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則是生而平等與獨立的個體,個人意志之實現的結果;
西人自由,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
在嚴先生看來,這才是西方富強的秘密:他們葆有一個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每個個體,因為其天賦的平等與獨立的權利,不再是奴隸,不再是與他人、國家不相幹的依附或零余;也因為這一天賦的平等與獨立的權利,有了自由參與政治事務的自由,以及與他人結成共同體的自由。而這樣的自由,也即意味著民主,自由的民主。這樣的個體,就是公民。他們是社會與國家的主人。Liah Greenfield分析近代以來,走向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五種路徑:嚴先生選擇的,正是由英國所代表的典型的“公民國家”的道路——在1500-1650年間,“主權民族”概念的拉丁文natio被解釋為a nation,而後者又被界定為:people(公民)。
為簡明論證起見,此處僅截取《原強》中論今日西洋之強的一段,作為例證: 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而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民長大鷙悍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較而論之,又為吾民所必不及。……(故)凡所以保民養民之事,其精密廣遠,較之中國之所有所為……且其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學術;其為學術也,又一一求之實事實理……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 這是嚴先生留給現代中國最重要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