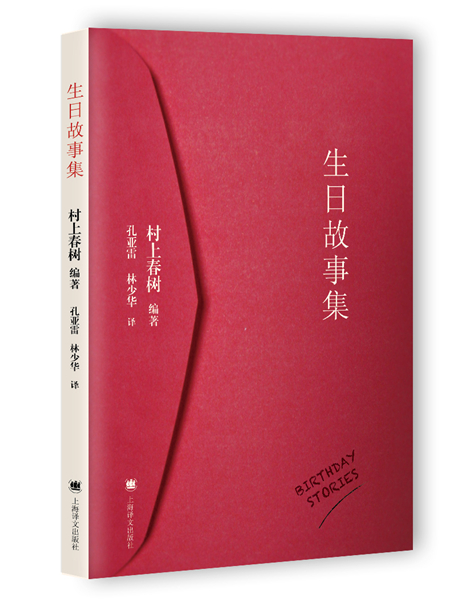
“精彩……村上春樹以優雅輕盈的筆觸介紹了所有的這些短篇小說”
——《星期日先驅報》
“一部令人難忘的小說集。小說的語調和場景如同每位作者般迥異,但它們都與那種隨意卻又極端重要的方式相關——我們正是以這種方式標志出生命的流逝。”
——《觀察家》
書名:《生日故事集》
編者:村上春樹
譯者:林少華、孔亞雷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定價:36.00
ISBN:978-7-5327-6982-7
【內容簡介】
《生日故事集》是由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選編並創作的一部以生日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其中12篇都是來自當代久負盛名的歐美短篇小說家之手,例如雷蒙德 卡佛、克萊爾 吉根、大衛 福斯特 華萊士等。
雖然每篇小說的主題都是與生日相關,但每一篇小說都風格各異,情節妙趣橫生,尤其最後一篇《生日女孩》是由村上本人親自操刀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為這本選編之作起到了畫龍點睛之效,意味深長,清新雋永。
【編者/譯者簡介】
編者:
村上春樹,日本現代小說家,生于京都伏見區。畢業于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演劇科,亦擅長美國文學的翻譯,29歲開始寫作,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即獲得日本群像新人獎,1987年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上市至2010年在日本暢銷一千萬冊,國內簡體版到2004年銷售總量786萬,引起“村上現象”。其作品風格深受歐美作家的影響,基調輕盈,少有日本戰後陰鬱沉重的文字氣息,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被譽為日本80年代的文學旗手。
譯者:
林少華,1952年生,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是村上春樹的“禦用翻譯”。畢業于吉林大學日文專業,現為中國海洋大學日語係教授。因其翻譯了日本文學家村上春樹的眾多作品而聞名中國大陸。譯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31卷村上春樹文集及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名家作品凡45種。因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而為廣大讀者熟悉,此後陸續翻譯32卷村上春樹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東山魁夷等名家作品。林少華以優美典雅的文字和對日本文學作品氣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讀者的推崇,同時他還應多家報刊邀請,撰寫專欄,亦是國內知名的專欄作家。
孔亞雷,1975年生,現為自由小說家、翻譯家。200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不失者》。他翻譯過的作家包括美國小說家保羅 奧斯特、加拿大歌手兼詩人萊昂納德 科恩、英國作家傑夫 戴爾等。他的短篇小說《芒果》和《小而溫暖的死》曾分別入選2005、2006年中國最佳短篇小說。2012年獲得第四屆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
【目錄】
村上春樹/ 序言:我的生日,你的生日 1
拉塞爾 班克斯/ 摩爾人 3
丹尼斯 約翰遜/ 盾盾 17
威廉 特雷弗/ 蒂莫西的生日 27
丹尼爾 萊昂斯/ 生日蛋糕 51
琳達 塞克森/ 變 61
大衛 福斯特 華萊士/ 永遠在上 71
伊森 坎寧/ 天使仁慈,天使憤怒 87
安德莉亞 李/ 生日禮物 103
雷蒙德 卡佛/ 洗澡 131
保羅 索魯/ 骰子遊戲 145
克萊爾 吉根/ 在水邊 155
劉易斯 羅賓遜/ 搭車 167
村上春樹/ 生日女郎 193
【書摘】
骰子遊戲
保羅 索魯
那個年輕人一邊走出我們的迷失天堂吧,一邊用肩膀擠開別人穿過旅館大廳,看見我,他用一種挑釁的語氣說:“今天我可長見識了!”為了引起我注意,他聲音說得很響。希望我的沉默和溫和的笑容能讓他平靜下來。
“我能幫您嗎?”我說,“我是經理。”
他三十出頭,很帥——頭發彈性十足——穿著件黑襯衫,更襯出他那焦躁的粉紅色臉龐。他氣喘吁吁,還有點慌亂,看上去就像剛從一場辱罵中脫身。男人被女人打了一耳光時就是那樣。
“看見那家夥了嗎?他瘋了!”
他走了,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他指的那個人埃迪 阿爾法塔,是酒吧的常客,總是和他老婆雪莉一起來,他崇拜她。他是市區一位有名的會計師——雖然為人過于嚴肅,但很成功,在畢肖普街有間事務所。我最喜歡他的是他對賭博的熱情。埃迪不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賭博的會計師,不過賭桌上的冒險和賬簿上的莊嚴使他顯得既矛盾又自信。他下的賭注適中。他經常贏。他說他有一套體係。
埃迪正專注地環視著酒吧,連我都沒看見。他老婆在哪兒?雪莉是個小巧的女人,幾乎像個小精靈——短發,骨骼精致,小手小腳,非常愛幹凈,總是衣著整潔,而且蒼白,特別是跟高大黝黑、炫耀著自己滿身毛發的埃迪 阿爾法塔相比。埃迪也以雪莉——他的白人戰利品——為榮,這點顯而易見,而且他的舉止有點輕微的神經兮兮的懼內,那是許多夏威夷異族婚姻中少數民族那方的一大特徵。他很有自我意識,急切地想做對事,但又不清楚怎麼做才算對,而且對別人在看著他們有一種不安的念頭。別人也確實在看。
再一次巡視酒吧的時候,我看見埃迪手里拿著骰子罐,搖晃著,發出輕笑聲。那只皮罐和那套骰子是巴蒂 哈莫斯卡從曼谷帶來的,那里的人在酒吧里擲骰子來決定誰付下一輪的酒錢。我經常研究玩骰子那些人聚精會神的表情和露出的大牙,心想在遊戲中,我們顯得多麼的極端好鬥和逞強,多麼的極端獸性。
但今晚我注意到的不是遊戲而是埃迪的對手。在迷失天堂吧很少看見衝浪手。更高級別的衝浪手,特雷那一夥的,外出一個星期捕浪的,有,但從沒有像這位的,一年四季都玩水的本地浪蕩子——光腳,寬肩,羅圈腿,一塊刺青在腰部,另一塊在兩個肩胛骨中間,寫著名字CODY ,透過他的破爛襯衫刺青全都清晰可見。他的帽子反戴著,一頭被太陽暴曬的長發,顏色和質地都像稻草,他的眼神黯淡而茫然,皮膚火燒過似的,滿臉雀斑,大大小小的,更增添了他外表的魯莽。他很年輕,大概頂多二十二三歲。而埃迪 阿爾法塔四十多了,所以這看上去很滑稽:皮膚黝黑、襯衫扎在褲子里、胸口別著兩支鋼筆的會計師,和衣衫襤褸穿著短褲的小夥子——思塔斯牌帽子,奎克斯爾沃牌短褲,洛克莫辛牌襯衫。他的腳很臟,腳趾有淤血。
“水老鼠。”特雷會說。
兩個男人沉溺在吧臺上翻滾的骰子里,而我也在想這些遊戲是多麼的傷感,它們的規則和儀式,它們讓我們荒唐地滿懷希望,它們那可以預知的結果,它們那可憐的功效——也就是供我們消遣掉玩遊戲的那段時間。所有玩遊戲的人在我看來都像是無可救藥的迷失者;遊戲是那些無法承受孤獨,不讀書的人——總是男人——的娛樂。骰子遊戲中有一種殘酷的淒楚,小小的輕笑,投擲,萩嗒聲,點數決定一切。
或許這只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無害娛樂?我幹嗎去考慮它,甚至注意它,這簡直有點病態,所以我轉而去關注更明顯的事:頭一次埃迪的老婆沒和他一起在酒吧里。他的笑聲更突出了這一點,他在催那個衝浪手,他熟練地移動著骰子罐,讓骰子發出快速的碰撞聲,他的嘴巴張得有點兒太大,他的笑聲有點兒太尖,當他贏了,就碰碰衝浪手的胳膊。埃迪的皮膚黝黑,像被烤過,而那個男孩白里透紅,像被燒過——我覺得有點意思。不過我很高興他們在這兒歡聲笑語,我喜歡把我的旅館看成一個避難所。
回到前臺,為了打探消息,我跟陳提到埃迪 阿爾法塔一個人在酒吧里。 “他老婆在樓上,”陳說,“我給他們開了802 房間。他們幾個小時前來的。住一晚。” 不同尋常,一對火奴魯魯夫婦在一家火奴魯魯旅館住一晚。
也許那意味著他們的房子被罩起來了,在煙熏消毒,但如果那樣的話,他們應該會找個周末做那種工作,要不就去一個鄰島待幾天。
“這些花是剛送來給阿爾法塔夫人的。”
一束花擺在桌面上。賀卡上寫著,生日快樂,親愛的。獻上我所有的愛,埃迪。
一次浪漫的生日休假——這解釋了一切。我在辦公室瀏覽了這個月的入住記錄,隨後,為了找杯喝的,我看見埃迪一個人在酒吧,叼著瓶啤酒,看上去正在沉思。沒有那個衝浪手的影子,我記起先前那個跑掉的男人說埃迪的話:他瘋了。
但埃迪的樣子很平靜。也許比平時稍稍顯得更安靜;獨自一人,但心滿意足。是賭博讓他思考嗎?不管怎樣,賭博遊戲已經結束了。
他被那個水老鼠甩了嗎?上一次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推那個年輕人,骰子在吧臺上萩嗒作響,他嚷著要酒,一邊拍著那個年輕人刺青的胳膊。我不想得出任何結論,但在我看來,這確實像一出戲謔的求偶戰,一場粗野的交配之舞中,兩個大男人在圍欄里推來撞去,對著骰子談笑風生。
“誰贏了?”我說,因為埃迪還在心不在焉地搖著骰子罐。“我們要過夜,”他說,他的輕笑就像骰子的聲音。“我明白了,”我說,為了試探他,因為其實我已經知道了,我問,“一次慶祝?”
“雪莉的生日。”他擲了把骰子,對擲出的數字皺了皺眉,又飛快地把它們收到一起。“這次是個大生日。四十歲。去年我們去了拉斯維加斯。雪莉手氣很好。她贏了五百美元。男人們都跑過來搞她,沾點手氣。‘你要排隊。’他們說。你真該瞧瞧。”
他停下來,看著我臉上半帶微笑的專注表情。我在思索:搞她?沾點手氣?他看出了我心里沒說出口的問題。
“我就愛這樣。”他說。穿著袖珍鞋、嬌小蒼白的雪莉,被一幫體型龐大、充滿希望的賭徒包圍著,而埃迪在一旁得意洋洋,就像狗展上的贏家。
“那次之前的生日,我們花了一個周末學潛水。拿證書的。我很糟。我把那看成一次賭博。我差點嚇得淹死。而雪莉學得如此之快,把那些學員都看呆了。他們全被她迷住了。你真該瞧瞧她的樣子——她穿緊身潛水衣有多麼性感。就像沒穿。”
回憶讓他很愉快,他碰碰自己的大腿,就像在找潛水衣,然後他再次把骰子收到一起。又一輪輕笑和投擲。
“她三十五歲那次我們真正爽了一把。我哥們和我帶她去了迪斯尼樂園。她就像個小孩。”他笑起來,沉浸在回憶中,還滿意地喘著氣。“她把他弄得筋疲力盡!”
搖晃著骰子罐,他又玩起來。
“她現在在哪兒?”
“我給她找了個衝浪手。他們在樓上。”他看上去很開心。他還在搖骰子。
“誰贏了?”
“你說呢?”
那個穿破襯衫的年輕人走進房間,他淤血的腳趾頭壓在地毯上,燈光很暗,雪莉穿著過生日的高級內衣,比一個高個的孩子大不了多少,但卻對此心領神會,整個過程幾乎都是默默進行的——這就是我想象的畫面。他們兩個在床上翻滾時,埃迪就待在樓下。而在這一切的尾聲,會突然涌上一陣憂慮,因為沒人知道這一切結束時會發生什麼。這就是遊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