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張悅然。 王旭冬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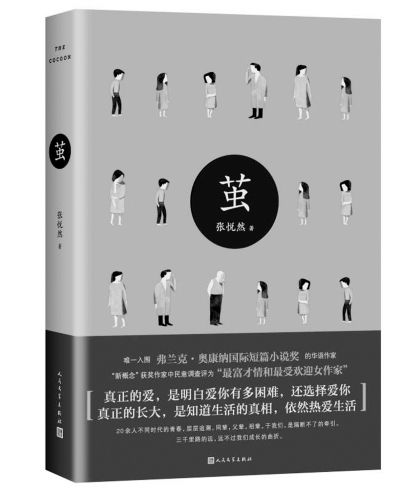
《繭》封面。
本報記者 路艷霞
10年前,80後作家張悅然因長篇小說《誓鳥》,而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等獎項的光環,令她的文學前途一片光明。此後,與她同時代的作家或一本接著一本地出書,或在影視圈施展拳腳。而她顯得有些平淡,主編雜志,到中國人民大學教書,許久未有新作誕生。
今年年初,長篇小說《繭》終于在《收獲》雜志發表。昨天,她帶著這部小說的單行本出現在了大家面前。這是一部讓讀者等得有些心焦的作品,在張悅然的微博下,有人留言,等太久了,等過了整個青春;還有人甚至說,有生之年,還好等到了。
新小說的語言變得更平凡
在昨天的新書首發現場,作家余華感慨道,另外一個張悅然來到了他的面前,既熟悉又陌生,她的語言變得更平凡了。“我讀《繭》的時候,經常發出會心的笑聲,我很讚賞她現在的寫作。”《繭》通過李佳棲和程恭兩位80後各自的講述,呈現了兩個家庭三代人的恩怨。
新書首發前一天,張悅然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她介紹,在上一部作品《誓鳥》中,從前的那種語言風格被展現到了極致,那是一種綿密、繁復、華麗的語言風格。這對一部充滿幻想的小說而言是合適的,但對《繭》這樣一部沉重而現實的作品來說,就會成為負累。“一種事物形成自己風格的時候,那本身也意味著一種局限。”
“這部小說寫得很慢,我想在創作過程中,完成語言上的改變。”不過,張悅然也一再說,風格的印記很難消除,也不應該被消除。所以在《繭》里,依然能看到她從前的語言風格。
關于同輩人的新作,評論家楊慶祥這樣評價, 張悅然處理小說《繭》是完全80後的方式,這部小說更像是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合體。除了父輩的歷史之外,小說中還有另外一個線索,就是80後主人公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精神軌跡。他認為,這是一部尋求對話和尋求理解的小說。
張悅然透露,將首次執導根據自己第二部長篇小說《水仙已乘鯉魚去》改編成的電影,“能讓我以現在的視角去詮釋原來的作品,彌補小說里留下的遺憾,這個嘗試很有意思。”她很清楚,她做任何選擇,都不會受別人的影響,“在這個節奏越來越快的世界,我花了那麼多年去寫一本書,就足以說明,外界的影響在我這里不起作用。”
高中時第一次看到“我的讀者”
14歲那年,張悅然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諾言角落》,是兩個女孩間承諾、告別的故事。
張悅然回憶,寫《諾言角落》根本沒有想過要發表,小說後來被她父親的一個朋友偶然讀到,推薦給了一家雜志。“那是一個有些學術氣息的雜志,我的小說刊登在上面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她甚至猜想,盡管雜志社編輯一再肯定她的才華,但也許只是因為有父親朋友的推薦,他們才發表了那篇小說。小說沒有來得及修改,有些粗糙,張悅然總覺得把自己的幼稚暴露在了人前,也沒有拿給任何同學看。
在那之後,她仍舊寫,一直到上高中時,才在學校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第二篇文章。不久後的一天課間,幾個別的班的女生站在教室門口朝里面張望,想知道誰是張悅然。“那應該算是第一次,我看到了我的讀者。”
2001年參加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對張悅然的人生是個轉折。她記得,收到復賽邀請時,她特別高興,因為寒假可以去上海玩了。最終她獲得了一等獎,順利得到保送清華的名額。但到4月,教育部下文件,保送又被取消了,她不得不回到校園準備考試。“這個過程算是一場磨難,但它對我有一種啟示性的意義,那就是寫作應該不帶有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從此她堅信,寫作只是一種本能的需要而已。
張悅然否認父母在寫作上對她的引導,她的父母對她的管束一向很少。只是她父親在大學中文係教書,常來家里的客人都是中文係的老師。她會經常搬個小板凳,假裝在一旁玩,其實是在聽他們聊天。而且,張悅然的父親有很多書,他的書架,就是她最早的精神營養。
不需要家人在旁邊不斷喝彩
母親保留著張悅然小時候寫的作文,但那是很多年前,她以為寫作只是女兒愛好的時候,才有意保存了下來。這些年回到濟南的家里,張悅然發現母親從來沒有拿出來,也從來沒有看過那些作文。她對這樣的狀態很滿意。
張悅然說,當她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以後,寫作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家人來說,它已變得很尋常,不再具有什麼特別意義。“我媽媽更關心的是,我有沒有好好吃飯,是不是又睡得很晚。”
不過,當寶貝女兒拿出新出版的《繭》時,母親非常認真地閱讀了勒口上的作者簡介,那種神情,好像是在了解一個她不認識的陌生人。讀完之後,她隨意地將書擱在了桌子上。“我特別喜歡媽媽的這種反應。我不需要那種不斷在旁邊喝彩的家人,因為寫作本來就是一個人的事。一個寫作者成熟的標志或許是,我知道我一個人可以面對和寫作有關的所有事。”在張悅然看來,寫作其實根本沒有成功可言,與內心的掙扎和跋涉相比,外界的認可微不足道。她很希望父母和她一樣,撇棄虛榮,不再希望自己通過寫作獲得任何寫作之外的東西。“對于我而言,那就是最大的支持。”
在女兒心目中,父親睿智、清醒,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不相信奇跡。往往是在女兒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的時候,他會表示其實這沒有太大意義。“我現在挺感激這種冰冷的態度,某種意義上說,那就是生活的真相。我爸爸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希望能及早讓他的孩子成熟起來,不要因為幻想破滅而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