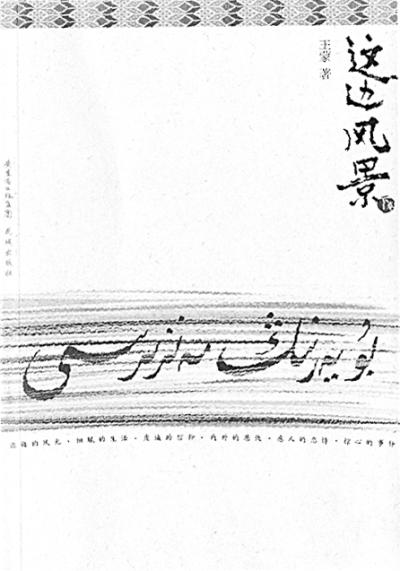
記者:首先想請您介紹一下這部獲獎作品《這邊風景》。這部您39歲時在新疆開始創作的作品,卻于79歲時才出版,按照您自己的說法,“好比是79歲的王蒙看到39歲的王蒙”。
王蒙:20世紀60年代,在我處于逆境的時候,我下決心到邊疆去,到農村去,破釜沉舟,重新打造一個更寬闊也更堅實的寫作人,打造一個煥然一新的工農化的寫作人。按當時的認識,我必須寫工農兵,只有寫工農兵才有出路。就像我在1963年底坐著火車帶著全家從北京到新疆時所吟蚑的:“死死生生血未冷,風風雨雨志彌堅。春光唱徹方無恨,猶有微軀獻塞邊。”
我到了伊犁州伊寧縣,巴彥岱人民公社,與維吾爾族農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並曾擔任二大隊副大隊長。
我很快與農民打成一片,講維吾爾語,讀維吾爾文書籍,背誦維吾爾文毛主席語錄與“老三篇”。我住在老農阿卜都熱合滿·奴爾與黑力其汗·烏斯曼夫婦家。我住的一間小屋,在我到來以後,燕子飛來做了巢,每天我與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農民們從這一點上認定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愛生活,我愛人民,我愛不同的環境與新鮮的經驗,我愛雪山與大漠,湖泊與草原,綠洲與戈壁灘。我得到了愛的回報。當地的農民喜歡我。
你可以說我是在特殊處境下做出的不一般的選擇,但是我選擇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滿生機,愛戀著邊疆的對于我來說是全新的一切: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鏝、水磨,還有情歌《黑黑的眼睛》;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漢、回、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錫伯、俄羅斯;還有瑢餅、拉條子、哈密瓜與蘋果園。我曾經說我在新疆16年,完成著維吾爾語“博士後”的學業。我至今回想起這一切,更要強調說,新疆各族人民對我恩重如山。困境中,是那里的人民保護了我。
于是有了《這邊風景》,我確實書寫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細節。勞動、夏收、割草、揚場、趕車……我寫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奮鬥、挫折、懶漢、積極分子;我寫了邊疆歷史的風風雨雨、恩怨情仇,我寫了那里大異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討論作品的時候,有學者說他們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圖,有的說邊疆生活細節排山倒海。一位維吾爾族女教授說:作家把他的心交給了我們,新疆各族人民也就願意把心交給他。
記者:請談談獲獎後的感受。
王蒙:此書的得獎最讓我感謝的是它將有利于人們關注新疆,了解新疆,熱愛新疆,走近新疆。我為新疆的兄弟姐妹們高興。
這本書的得獎,還讓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經得住時間的考驗。41年前動筆寫的書,37年前基本定稿,兩年前出版,現在受到了關注。毋庸置疑,寫作的年代與當下區別很大,寫作時有各種的局限性,可以說當時的寫作是戴著鐐銬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銘心的生活經驗,有了血肉相連的感情交融,有了親近大地的匍匐與諦聽,有了對于人民音容笑貌的細膩記憶與欣賞,你寫出來的人、生活、情感,就能突破局限、擺脫鐐銬、充滿真情、充滿趣味,成就你所難以預見的閱讀的厚味與快樂。
仍然是王蒙寫的,仍然熱愛,仍然多情,仍然興致盎然,仍然一片光明,仍然有“青春萬歲”的信念,有“新來的年輕人”的眼光與好奇心,有對于生活的繽紛期待,有對于愛情的謳歌,有對于歷史和時代的鑽研,有對于日子的珍惜與溫習。
記者:在您看來,文學評獎與文學是什麼關係?
王蒙:茅盾文學獎的獲得當然令人高興。文學獎引人注目,因為它向讀者推薦了文學。獎為文學增光,前提是文學能不能給獎增光,能不能給予心靈以撫摸與衝擊、營養與激揚。只有文學本身可愛,獎才可愛。離開了作品去研究文學獎,未免可笑與可悲。獎能錦上添花,獎能促進發行,但是獎不能彌補缺陷,獎不能化東施為西施。把功夫放在爭取得獎而不是寫好作品上,只能說是作者沒出息到了極致。 (本報記者 饒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