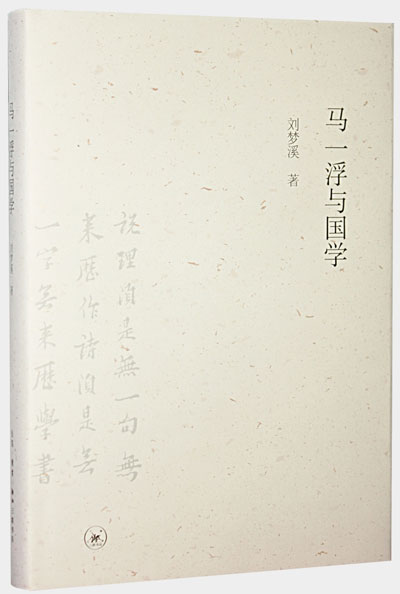
人民網北京7月27日電 近日,劉夢溪先生的《馬一浮與國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劉夢溪主講《馬一浮與國學》讀書活動,向讀者介紹了這位學術大家的生平與成就。
馬一浮是20世紀的學術大家、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一生追求學術, 學貫中西,涉獵廣泛,在經學、史學、哲學、佛學等領域均有建樹,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鑽研精深,行文又多微言大義,故能深入了解馬一浮學術之人甚少,能集中介紹其學術之專著則更為少見。
劉夢溪先生以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見長,善于通過對重要學術人物的研究來展開其對學術史之研究,用幾十年之功治陳寅恪和馬一浮。而馬一浮研究則更為艱辛,劉先生戲稱馬一浮是“雲端上的人物”。劉先生認為,家庭背景、婚姻生活、留學經歷、朋友結交對馬一浮選擇終身以學術為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重視儒家典籍的研習和釋家載籍的精修,從而形成其儒佛會通的思想,亦與其經歷息息相關。馬一浮始終強調並堅持知識分子應有自由研究之空間,學術研究應有自主性,獨立不倚,志不可奪。他主張讀書應漸次與窮理盡性、蓄德進德、體驗證悟、涵養功夫、變化氣質聯係起來,即其所謂讀書之五個階段。他強調“六藝論”,認為六藝統攝中西一切學術,國學即六藝之學;又強調“義理明相論”,是馬一浮針對六藝而建構的融通儒佛又輔以因明之學的新義理學說。馬一浮在浙大,尤其是建立和管理復性書院的過程中,他的學術旨趣、人才培養理念等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實踐。
馬一浮的學術思想體係,可以用“新義理學說”立名,其學理構成為“六藝論”和“義理名相論”兩部分,其方法則是儒佛互闡和會通儒佛。對馬先生的一生為學而言,儒學是底色,佛學是生活,詩學是性情。他將國學重新定義為“六藝之學”的“國學論”,前賢不逮,義顯當代,澤被後世。
劉夢溪與他的馬一浮研究
一、怎樣看待近十年的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熱
最近十年來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是文化傳承和文化重建的不得不然的現象。它根源于百年以來不間斷地反傳統,特別是對十年內亂期間“大破四舊”、“跟傳統徹底決裂”思潮的一種反彈。
但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國學與教育、禮儀與道德,其義理內涵及化跡型態,極為深邃復雜,今之學者分疏起來,猶感匪易,化入現行教育體制或成為可以踐行的當代人的生活倫理,更是知難行亦難的艱辛旅程。
好在中國有廣大博厚的民間社會,當佔據社會主流的價值係統“禮崩樂壞”的時候,還可以在民間找到那些文化的碎片,即所謂“禮失求諸野”。因此雖經過長期地對文化的大、小傳統的污名毀棄,我民族的文化傳統仍然還能斷而相續、不絕如縷。新儒家將後五四時期的傳統文化,形容為“花果飄零”,固為的論。但根脈尚存,只要有培育的土壤,重新著花結果,並非不可期待。
文化的“大傳統”則是指社會佔據主流位置的思想型態,例如漢代中葉以來的儒家思想。五四“反傳統”主要是反思和試圖整合文化的“大傳統”,民間社會的“小傳統”未曾發生深層的動搖。當下我們所致力的,是在民間“小傳統”先期重建之後,再一次對大傳統的整合與重建。這是一個接續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重建我國固有文化價值信仰的文化揚厲過程。
我們高興地看到,百年時日從未曾有過的文化人和國家中樞,正在合力創造文化重建的新世局。新的文化復興的曙光已經在華夏聖土露出潛發的微茫。
二、馬一浮是誰?他的大師氣質是什麼?
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紀的“儒之聖者”。過去學界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馬一浮相提並論,但在這三個人當中,要講學問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個詞,學問的“本我”境界——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一等的。但是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籌,這是我的看法。我說馬先生是二十世紀大師中的“儒之聖者”,但是你不能講熊十力是“儒之聖者”,也不能將梁漱溟是“儒之聖者”。他們都是儒學思想現代重構當中的重要人物,但只有馬先生我們可以稱他為“儒之聖者”。
馬先生又不僅僅是“儒之聖者”,他還是“高人”,還是“逸士”,也可以說是一個現代的隱者。在中國傳統當中,有品評人物的傳統。這個在六朝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發達。出現了很多奇書,譬如劉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說新語》,一部記述魏晉人物風採面貌、品評人物性格精神的專書。我們如果用傳統的方法品評人物,馬先生顯然不僅僅是大學者,不僅僅是大師級的人物,他還是“高人”。他的眼光銳利,對學問一目了然,對人也一目了然。你剛一進來,想說的話,沒想說的話,他都知道。
馬先生學問根柢的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內在精神的凈化,少有與之比肩者。他常說的一句話叫“刊落習氣”。大家不要以為“習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氣”,不僅為我們學者所要去掉,也為一般人所要去掉。每個從事專業的人也有這樣那樣的專業“習氣”。常常我們看到有一些學人,甚至有一些老師,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覺得另外的領域都沒有他這個領域重要。這也是一種“專業偏執病”,也是專業的“習氣”。專業的成就是好的,專業的精神是好的,專業的“習氣”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
三、國學概念的取義及流變
“國學”這個概念中國歷史上就有,《周禮》里面就有,《漢書》、《後漢書》、《晉書》里面,都有“國學”的概念。但歷來講的所謂“國學”,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
“國學”作為一個現代學術的概念,至少我們在1902年,梁啟超和黃遵憲的通信里面,就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了。而在1902至1904年,梁啟超寫《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里面最後一節,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麼興旺,新學青年吐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啟超說,“外學”越發達,“國學”反而增添活氣,獲得發展的生機。他在這里再次用了“國學”的概念,而且把“國學”和“外學”兩個概念比較著使用。
可是,當時對于什麼是“國學”,沒有人作分疏。
直到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第二年,1923年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國學門”要出版一個刊物,叫《國學季刊》。請胡適之先生寫發刊詞,他第一次給國學下了一個定義。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
“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胡適說,自從章太炎先生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概念的內涵太寬,所以胡先生這個定義事實上沒有被學術界採納,後來很長時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不見再有人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為什麼呢?“國故”這個概念太龐雜,古代的社會制度、古代的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衣飾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國學”就是研究這些漫無邊際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東西,你很難把握住哪些是這一“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事實上,學術界沒有採納胡適先生的定義,學術界不約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就是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
什麼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呢?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代的理學,明代心學,以及清代中葉的“樸學”(“清代漢學”)等。這是一個學術史的流變。這樣定義國學,還是太泛。人家會問:你是指哪個時代的學術呢?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還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講中國的學術,不僅有儒學,還有道家,還有道教,還有佛學,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呢?所以,把國學定義為“中國固有學術”,還是太籠統,太寬泛。
四、馬一浮重新定義國學
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在浙江大學開國學講座。他在第一講里,就提出需要重新定義國學,他把這個叫“揩定國學名義”。
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 “六藝”就是“六經”,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這是中國學問的最初的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馬一浮先生認為,國學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給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國學定義。
馬一浮提出這樣一個國學定義,它的了不起之處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結合起來。你講“國學是中國的固有學術”,那是關于學術史流變的學問,專業人員研究起來尚且不無困難,你怎麼可能叫社會學科、自然學科、其他學科都來關注這樣一個“國學”呢?一般民眾更不用說了。
可是既然叫“國學”,就不能跟一般民眾不發生關聯。如果定義“國學”是“六藝之學”,就是國學是“六經”,跟全體民眾都有關係了。因為“六經”是中國人立國和做人的基本依據,是中華文化價值倫理的源泉。所以如果把“國學”定義為“六經”的話,它就可以進入現代的教育。
五、國學和“六經”的價值論理
“六經”的文詞比較難讀,但《論語》和《孟子》實際上是“六經”的簡約的通俗的讀本,因為孔子和孟子講的思想,就是“六經”的思想。孔、孟闡述的義理,就是“六經”的基本義理。
我把“六經”的基本義理概括為“敬”、“誠”、“信”,還有“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 “敬”是什麼?就是人的“自性莊嚴”。“敬”是個體生命的莊嚴,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個人都應該具有的,我甚至認為“敬”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
這種“自性的莊嚴”,馬先生當然實現了。二十世紀的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自性的莊嚴”的表現。那麼一般人士、沒有文化的人有沒有“自性的莊嚴”?當然有。我們看《紅樓夢》,當賈赦要娶鴛鴦做妾的時候,鴛鴦堅決不允,做了很多極端的舉動,包括破口大罵,甚至把自己的頭發剪下來,所彰顯的就是鴛鴦這個年輕女性的“自性的莊嚴”。
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莊嚴”的突出體現。人的“自性的莊嚴”,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婦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沒文化都可以做到。我們當下所缺的,就是這種人的“自性的莊嚴”。當代文化價值理念的建構,亟需添補的,就中國傳統這一塊,我講的以“敬”來帶領的這些價值理念,包括誠信、忠恕、仁愛、知恥、和同等,應該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補的精神價值。
而以“六經”為內容的國學,就可以通過教育的環節,和全體國民聯係起來。所以我主張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在現代知識教育體係之外補充上價值教育。
【作者簡介】
劉夢溪 當代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學術思想與人物》(2004)、《紅樓夢與百年中國》(2005)、《論國學》(2008)、《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國學與紅學》(2011)、《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說》(2014)等。亦曾編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35卷、2000萬字,1997)。
【圖書信息】
《馬一浮與國學》,劉夢溪 著,定價:52元,2015年6月三聯書店刊行 裝幀: 精裝ISBN: 978-7-108-052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