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命運的人生》作者凱爾泰斯·伊姆雷說,“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使仇恨永遠存在下去。”皮埃爾·勒努阿爾在《帶條紋的地獄囚服》中寫道,“我還屬于集中營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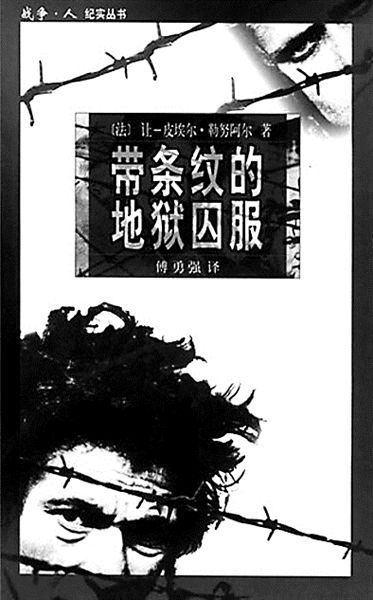
《帶條紋的地獄囚服》 (法)讓-皮埃爾·勒努阿爾譯者:傅勇強人民文學出版社

諾獎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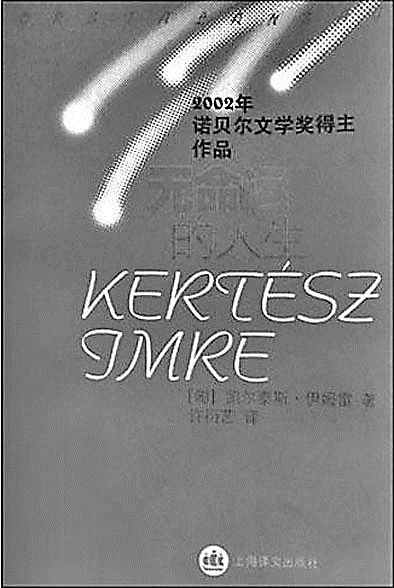
《無命運的人生》 作者:(匈)凱爾泰斯·伊姆雷譯者: 許衍藝上海譯文出版社
有許多歷史的黑暗復雜地帶,其實在我們理解之外。或者說,盡管有諸多文本在幫我們理解,但在當事人看來,仍然觸不可及。我在這里縮小范圍,說說奧斯維辛,以及兩個親歷人的文本留給我的感受。
“我感覺自己與他們不同,完全是陌生人。我還屬于集中營的世界。”一位名叫讓—皮埃爾·勒努阿爾的法國老人這樣寫道。他的《帶條紋的地獄囚服》這本回憶錄最近我再次拿起,完全是凱爾泰斯的緣故,我讀他的《船夫日記》讀得入味,忍不住想將作家其他著作也拿來讀。只找到上譯版那本《無命運的人生》,旁邊挨著的就是這本。都是幾年前的舊書了,書脊還很細薄,若不是這樣定向地翻找,看到它們也非易事。但是,該看見的,總會被看見。這只是個機遇與時間的問題。同樣,願意理解與能理解,這也是個時間的問題。
《無命運的人生》(另一個版本譯作《命運無常》),也是帶自傳色彩的集中營文本,正好可以對比來讀。他們一個是生于1922年的匈牙利猶太人,15歲被輾轉運送至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等幾個集中營;一個是生于1929年的法國猶太人,呆過幾個集中營直至二戰勝利。凱爾泰斯的書里,有大量的心理描述,倣佛一個內在的眼,在展開對環境、對人以及自己內心細致的探尋,閱讀的進程也便如探尋本身一樣難熬、不確定而且莫測。相比之下,讓—皮埃爾·勒努阿爾的敘述要明快跳脫得多。片斷式、跳躍式的場景捕捉,省略了很多前鋪後陳。諸多形形色色的“人”,構建出屬于集中營的特殊生態。“這里也是歐洲。”作者以希臘神話作喻,他說這里既有諸神(黨衛軍)、半神(替納粹看管集中營的老德國犯人)、還有來自德國統治下不同歐洲國家的賤民。賤民雖然是命運的共同體,但也不意味著沒有摩擦,相反,有時的對話還挺生猛:
“俄國同志,我的勺在哪兒?”“我他媽不知道。”“剛才還在桌上。”“我他媽沒看見。”“我們彼此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說話,你沒偷我的勺?”“法國傻X,叫喚什麼。你要勺,這兒有。”他把我的彎勺扔在桌上,說。“法國傻X,你在這待得有日子了,早該曉得東西誰撿就歸誰。”……
抄錄出這一小段,因為它非常代表這本書的敘述風格。簡潔利索,聲畫兼具,但沒有別的。我卻記住了這把勺子。我們通過電影建立起來的集中營想象,解放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了百了的解放,但事實遠非這樣:“很久以後聽人講,遣返的蘇聯人回去後全被處決或流放到西伯利亞了。而其中一些人曾經有過英雄壯舉,尤其是那些遊擊隊員,他們在德國戰線後方採取過有效的戰爭行動。但紅軍中所有軍官或士兵一旦被敵人俘虜,就被稱作叛徒,也被當作叛徒對待……”我猜作者寫至此地,一定會聯想到那把勺子。
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卻是以平靜與超然的筆觸寫下,這既令人震撼,同時也耐人尋味。為什麼不將所受的苦難轉成憤怒的撻伐,作者在後記中這樣表達:“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使仇恨永遠存在下去。”
走到這一步並不容易,因為這本書最後一章叫《後遺症》,講的是集中營生活對其後來生活的影響。與《無命運的人生》的最後一章異曲同工,他們都說到了一個感受:孤立與隔膜。經此一遭的人們,是否能夠遺忘,以開始新的生活?凱爾泰斯筆下這位少年的回答是:NO。“發生過的事情是已經發生過的,我終歸不能夠命令自己的記憶把它們給忘了的。我認為,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時,要麼就是在我的大腦出問題或患病時,新生活才可能開始。”有過與舊時鄰居不歡而散的對話,少年突然感到:“在那些煙囪旁邊,在痛苦的間隙中,也有過某種與幸福相似的東西。”而讓—皮埃爾·勒努阿爾也遭遇過不理解,一次還是在他對奧地利猶太人說過一番話之後:“親愛的,假如我不是法國青年,是德國青年,我也會參加戰爭,我寧願不去思考讓我執行的命令。”對方不解:“您受盡了所有這些痛苦之後,怎麼還能說出這樣的話?” 是啊,怎麼能?怎麼會?但我知道語言有時的吊詭,讓在這里用了寧願與假如。正是這兩個詞,墊出了黑暗與苦痛的全部重量。
與凱爾泰斯的諾獎名聲相比,讓—皮埃爾·勒努阿爾聽來相對陌生,百度上的中文資料,還停留在與書相關的部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健在,只是看到印在封底的他的肖像,依然精神矍鑠、氣色很好。此書是他晚年應孩子的要求所寫,後記中他真心希望他所經歷的是所謂文明國家進行的最後一次戰爭。一位對世界心懷希望的老人,總是讓人溫暖,這也是我讀這本書的感受。
說苦難會轉化為人生的財富,這是一句籠統的話。苦難怎樣化為財富,凱爾泰斯與這位老人,都提示了各自的方向。看《船夫日記》當知,《無命運的人生》只是凱爾泰斯思考奧斯維辛的第一步。他後來移居柏林,說要把大屠殺作為思考的起點。“現在,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我們該如何從這里繼續前進?”而讓—皮埃爾·勒努阿爾戰後從事企業管理工作。書中記錄了與一位美國人的相遇。他告訴他,當年執行轟炸任務,目標正是他所在的米斯堡集中營。“後來我們常在一起打高爾夫球。沒有怨恨。”這件事就此結尾。
樸素而高貴,是作家莫里斯·德呂翁對他這本書最精準的評價,但我體會到,這絕不僅僅指文體的質地,還指的是以這種文字來敘述苦難的那個人。
“我們和他們存在鴻溝。”莫里斯·德呂翁的推薦序里還提到一個關鍵詞,要理解它就得同時理解凱爾泰斯這句話:“怎樣才能處理好資料與整理原則之間難以跨越的斷崖?如何避開那些經過修飾、反復出現的狡黠窺望的劇情?”創作者的自問,也差不多提示了作為觀看者的我們所容易陷入的陷阱。而要彌合這斷崖與鴻溝,就得如凱爾泰斯書中少年所說:“得把所有這四年、六年或者十二年都乘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二十四小時……最後再把所有這些都倒回去,每秒鐘、每分鐘、每小時,每天地倒回去,然後把所有的時間全都消磨掉。”顯然我們沒法做到,就像我們沒法想象,在這消磨的過程中,除開那巨大的恐懼與顫栗,還有冗長的麻木與無聊。以及在我們聽來頗不可思議的“幸福”。
而這兩本小書,都在以各自方式提示著這些,可貴的還有,在深感不被理解中,他們仍自覺地搭建著這一記憶遺產與現實、未來之間的橋梁。(孫小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