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下午,專程從上海趕來的金宇澄和向來深居簡出的阿城相聚北京言幾又書店,共同探討金宇澄最新出版的作品《回望》。《回望》可以看作金宇澄的私人回憶錄,關于父親和母親,關于記憶與印象,當然也關于舊日的上海。

活動現場。金宇澄(中)與阿城(右)對談。
中國式的敘事給人一種碎片化的體驗
金宇澄表示,《回望》和《繁花》在創作過程上有很大的區別。《繁花》其實是一個和網友持續互動而來的產物,而《回望》的寫作則是斷斷續續的。最早的一篇寫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算是道聽途說來的,是在家聽父母談起往事的拼湊所得。接下來便是在父親過世之後,慢慢收集關于父親生前的材料,漸漸加深了對父親的了解。金宇澄說,材料中其中幾封信給自己觸動很深,這些也都收錄在書中。因此總體來看,《回望》並沒有固定的形式,而是分成了三個部分:開始是一個引子,中間一部分重新審視了大量的史料,而最後一部分則由金宇澄母親的口述組成。
這種近乎片段式的描寫方式,其實和金宇澄的閱讀密切相關。金宇澄說自己特別喜歡中國式的敘事方式,喜歡看筆記體的故事。雖然西方的敘事方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大規模地影響了中國的讀者和作者,但金宇澄仍對中國式的寫法很感興趣。“中國式的寫法不是要把人的里里外外都說清楚,而是就幾句話,這總是給讀者一種碎片化的閱讀體驗,生動的,一個人露出來又消失。”
在談及歷史時,金宇澄也說自己不喜歡看頭頭是道、邏輯性非常強的大歷史,反而傾心于類似八卦的故事,因為“你會覺得這些東西就在眼前”。金宇澄提到清代李伯元所著的《南亭筆記》,里面記錄了很多無甚由頭的怪人。
比如晚清時代有個將軍級的人物,是湖南人,常穿白色戰袍騎白馬,經常被認為是清代趙雲。此人有很多老婆,但當他有了一大筆錢的時候就到上海玩。當時全國只有上海最好玩,因為上海有租借,有紅燈區。他到上海就化裝成一個乞丐,跪在有妓院的四馬路上,手里拿著一沓手紙,看見一個女孩子就遞一張手紙給她,一般情況下他會被罵被拒絕,但是也有心地很好的女孩帶走了手紙。此人跪在地上把手紙發完就走了。把手紙帶回家的女孩子發現手紙里夾著一張黃金的葉子。
金宇澄評價說:“這個故事到這就結束了,你不知道出于什麼原因他這麼做。就好像在飯店里剛吃到一個很好的菜,就沒有了,所以味道特別濃。這種小小的短章能給人很大的想象空間。所以我在《回望》里有時候會觸及到一些小的細節。越是沒有原因的短的敘事,反而能產生非常強烈的想象的空間。有些非虛構的寫法是非常仔細地梳理一個人物,大致平衡和完整,甚至也有虛構的成分。但我想做的是只要覺得有趣的,就把它記下來,甚至于有很多的空白。這可能和一般的非虛構不太一樣。”
阿城則說在讀《繁花》和《回望》時,發現兩本書中都有一個上海地圖,如果相互比對著看,會發現兩張地圖里的地點基本沒有重合。假如金宇澄繼續這樣寫下去,就會出現一個非常完整密集的上海地圖,每一個點都有自己精彩的、能夠被讀者記住的故事。而慢慢地,如果其他作者也加入,那麼上海這個區域在時間軸上的串聯將會非常豐富,讀者會因此對上海這個城市有越來越清晰和深入的了解。“這是我從金老師的作品里得到的比較深的見解,我特別期盼他在以後的著作中能夠把這個地圖呈現得更加細致。就像以前巴爾扎克寫《人間喜劇》,把整個巴黎和與巴黎有關的外省描繪出來,提供了一個最詳細的法國地圖。對于北京來說也需要一個這樣的地圖,但現在看來,北京這邊的人比較愛忘事兒,這個地圖一直沒有開始建立。”阿城說。
中國的寫實主義像氣球,能拴住氣球的點在于自然主義
《回望》開篇的第一句,是關于物件的描寫。“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角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臺,請店家刨平了臺面,上漆,木紋很漂亮。”與此類似的細節,在《繁花》中也多,細細密密像針腳,鋪排開來。阿城對這樣的細節描寫頗為推崇,阿城談到十八世紀五六十年的時候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他們開始對很多事情發生興趣,希望對很多的點深入挖掘,這個挖掘導致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省,導致人們發現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寫是妖魔化的。
“法國大革命歷史的推力的結構和原來的環境漸漸就像一個島慢慢升起來,露出水面,水都流走了,我們看到了遺址。這個島對于影響世界的法國大革命進行深刻地反省,這個反省導致對于革命的反省,關于革命還是改良的爭論就有了新的詳實的資料以供討論和鑒定。這有很大的影響,對于波旁王朝的認識和以前也不同了。所以細節挖掘做的越普遍越深入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會產生更普遍更深入的認識。”阿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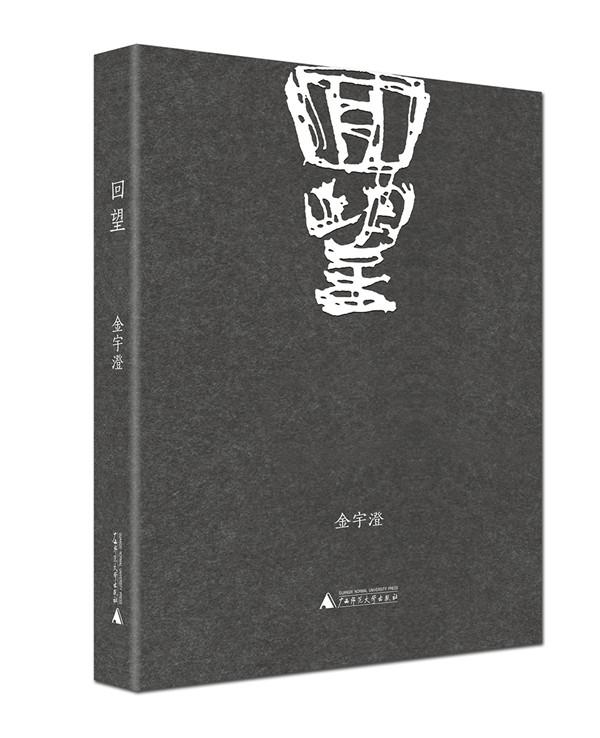
《回望》封面
阿城也由此談開,講到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中國一直在強調寫實主義,但寫實主義的基礎其實是自然主義。像巴爾扎克、福樓拜這樣的作家的描寫,自然主義代表人物左拉認為,他們沒有到達寫實的極限,一定要通過自然主義達到寫實的極限。到了極限之後退回來才能知道對于寫實主義的把握是否有分寸、夠分量。阿城說:“沒有對這個底線的認識的時候,我們不好把握,看不清自己的寫作在一個什麼恰當的合適的寫實的度。我在‘文革’時候看到了人生的絕境,就是底線,再往前走就是死亡。誰是樂觀主義?當然是我,因為只要我一回頭,就是亮。前面是最黑,我越偏頭會越來越亮,越來越光明。在文學上這個底線就是自然主義,到了這個時候,只要你一偏頭,所有細節的顯現、細節的意義在哪里等問題就會越來越清晰。”
阿城也談到中國對于自然主義的態度一直以來是批判的,因為中國的寫實主義是關于覺悟夠不夠的判斷,是在討論對于現實的認識。自然主義恰恰相反,里面不涉及什麼價值判斷,但卻很有力量。阿城做了一個比喻:“寫實主義一直像個氣球,飄忽不定,必然有一股強風來,主流來,就隨著主流飄,沒有一個線能拴住這個氣球,氣球就是寫作。氣球的扣在哪,下面的點在哪?就是自然主義的描寫。”
“張愛玲對《紅樓夢》不是特別滿意,因為它還是傳遞了一個價值觀,比如後來賈寶玉出家了,那是很強力的價值觀。但是《金瓶梅》不是,你看到的是自然生物體如何慢慢爛掉、死亡,本能的東西在那里來回蠕動。中國實際上是有比左拉在時間和空間都要早的自然主義傳統的,其實有很多人繼承了中國的自然主義傳統,但沒有人敢于通篇繼承,而是局部繼承。我看《繁花》很興奮的一個點是,終于開始有人給中國現代的自然主義補課。這個補課的結果是非常正面的。自然主義的描寫是對人最本性的反映,是敢于直視。敢直視它實際上就是直視自己。當人在自然主義的底線遊走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看自己。”阿城說。

評彈版《繁花》。攝影:虞凱伊
金宇澄則順著阿城的話延伸開去,從評彈改編《繁花》的嘗試探討價值判斷的問題。《繁花》一書其實是評話的形式,是從頭到尾一個人說話,變成評彈怕一個人說太累,就把它做成三四個男女彈彈唱唱。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判斷人物的傳統,分辨好人壞人的問題。“比如第一場就是繁花引子里抓姦的一段。評彈演員處理這一段一開始就給出了一個價值判斷,最後也改成一個人做了壞事情所以是活該。我覺得這個就不對,因為小說里的分析雖然是一個世俗的畫面,但是在目前情況下也不能說婚外戀的人就是壞人。評彈的人說這是師傅教的,首先要分析一個人物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叫開相。我們現在的觀念在和傳統親密接觸以後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也就是這些傳統戲劇如果觀念不改變,可能就不大有人能接受,因為它把東西簡單化了。人的復雜性應該是我們要關注的,並讓我產生了對于過去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包括對上海。”金宇澄說。
方言是泥土里自生自滅的味道
《繁花》一書因為採用了很多改良後的上海方言,因此引起了對于方言寫作的熱烈討論,而在《回望》中,金宇澄沒有延續方言寫作。金宇澄表示當初用改良上海話的原因和自己多年的編輯身份有關。“因為我自己是編輯。有些方言的稿子,離開一個地方讀者就看不懂,所以習慣讓作者改一下。 等到我自己用上海話寫的時候,就有這個意識,我自己可不能寫讓別人看不懂的上海話,就叫做改良。”
阿城則說讀《繁花》時並沒有閱讀障礙。阿城認為接受教育的思維讓人們養成了一個習慣:一步一步扎實,搞明白了才繼續。但閱讀恰恰相反,是個不求甚解的過程,即使現在全部讀懂了,到了另一個人生階段還會重讀。因此不求甚解其實是閱讀的常態,里面的方言讀多了之後,可以結合上下文語境猜出來,並不會造成閱讀障礙。阿城認為唯一損失的是一種方言的音韻之美,以及里面所蘊含的自然的情緒。
金宇澄則覺得方言是一個泥土里長出來的語言,它沒有辦法進入字典,因為每天都在變。所以當我們用方言寫作,記錄下來的就是方言在某個時刻的樣子。“比如《金瓶梅》里的這種語言,可以看到當時有些話是那麼說,但現在不說了。方言是自然的、泥土里的自生自滅的味道,是很有意思的。”

講座現場
[責任編輯:楊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