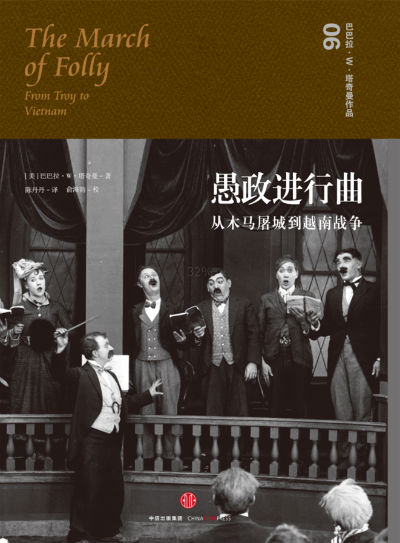
《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巴巴拉·W·塔奇曼孟慶亮 中信出版集團
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 包括天氣
“歷史比小說更精彩”,讀過歷史寫作大師巴巴拉·塔奇曼的書後,你會相信確實如此。兩次榮獲普利策獎,兩部獲獎作品《八月炮火》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暢銷不衰,寫作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且常年背著家庭婦女的本職,塔奇曼是個傳奇。
中信出版社首次集結出版了六部巴巴拉·塔奇曼作品——題材涉及特洛伊的陷落、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越南戰爭。題材廣闊,文筆閃耀,讀來令人擊掌,又不乏警醒作用。
這位有著傳奇色彩的美國老太太生于1912年,卒于1989年。雖然她的獲獎作品被歸類為非虛構文學,但她明白表示,討厭“非虛構”一詞,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歷史,也因此被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等譽為“作為藝術家的歷史學家”。
出身世家 眼界高遠
一開始巴巴拉·塔奇曼就很自然地躋身于美國知識精英階層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紐約從事實務中的人中的自由派領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老亨利的兒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後來成了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她還是哈佛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生時,就曾陪外祖父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對她來說,眼界高遠和公眾人物的品性都是遺傳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學院的時候,塔奇曼的興趣是歷史和文學。1933年畢業時,她開始在太平洋關係學會美國分會工作。該學會是一個富有開創性的“智囊團”和會議組織。當時學會的國際秘書長威廉·L·霍蘭被派去日本東京指導《太平洋經濟手冊》的編纂工作,塔奇曼則在1934年的10月成為他的助手。她在東京待了一年,然後在北京暫住了一個月。暫居日本的一年中,塔奇曼為學會的出版物《遠東調查》和《太平洋事務》寫了一些文章,盡管主題都不太熱門,但她的文章依然受到了學界的關注。
回到紐約後,塔奇曼在1936年開始為《國家》雜志工作,她的父親莫里斯·沃特海姆曾經是該雜志的受托人。受《國家》委派,她在1937年至1938年間去馬德里報道西班牙內戰。之後,她作為倫敦《新政治家》雜志的駐美國記者回到紐約,並于1940年與萊斯特·塔奇曼博士結婚。珍珠港事件之後,塔奇曼的丈夫加入了美軍醫療隊,塔奇曼和女兒跟隨丈夫到了亞拉巴馬州的拉克營,當他于1943年和醫療隊遠渡重洋時,塔奇曼和女兒回到紐約,並開始為戰時新聞局工作。
如此出色的早期職業經歷足以使塔奇曼往外交或行政工作方向發展,但她志不在此。1956年,塔奇曼重拾早年興趣,出版了《聖經與劍: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時期的英國和巴勒斯坦》,這是一本從古代一直講到1918年的歷史著作。從那以後,塔奇曼找到了自己的風格,面向大眾寫作歷史。
題材廣闊 非常好讀
塔奇曼認為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只不過她講的確有其事,並非虛構。她主張把歷史看作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相比這些,像社會流動性、合法性、投資比率和工作觀念之類的問題是次要的。她反復強調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獨特性。
同時,塔奇曼也非常看重歷史的真實性。歷史作家寫過去的事,但他們不是過去的人,因此他們只能無限接近歷史真相,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保證用證據說話”。《八月炮火》出版後,有一個讀者告訴塔奇曼,他尤其喜歡《八月炮火》中那段寫到英軍在法國登陸的下午,一聲夏日驚雷在半空炸響,接著是血色殘陽。這位讀者以為這是塔奇曼藝術加工出了一種末世景象,但事實上那是真的。這個細節來自一個英國軍官的回憶,這位軍官參加了登陸,聽到了雷聲,看到了血色的日落,因此塔奇曼把這段描述寫進了書中,“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塔奇曼如是說。
塔奇曼筆下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也許費正清的評價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說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個事例也可以說明塔奇曼的歷史寫作風格,她曾經在《歷史的技藝》中談及歷史寫作在于發現“新東西”。這里的“新東西”並不是為了有意顛覆前人所見而存在的。新東西,可以是一個未被重視的人,一件被忽略的事件,或者如她自己所說,是“計以盎司的歷史”。美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博士論文主題是法國社會主義史,導師要他了解19世紀某年法國普通商品的物價,對塔奇曼來說,這一點都不值得驚訝,掰開揉碎是每個研究歷史的人的基本功,而她,一個一輩子都是“業余歷史愛好者”,比科班歷史學家更強的地方,是她能夠將“盎司”揉入到“史識”之中。(譚宇宏)
《遠方之鏡》 一連串黑暗中曙光隱現
14世紀的歐洲包含了兩個相互衝突的圖景:這是一個屬于、大教堂和騎士制度等的榮耀時代,也是一個墮入混亂與精神痛苦的世界。塔奇曼在《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中將她的探察領域聚焦在西方文明最為黑暗、最為沒落的歲月,它的意圖是尋找那個最落寞年代的根本原因。塔奇曼從這一時期選擇了貴族——昂蓋朗·德·庫西作為敘事載體,借此人的人生遠望中世紀的百年戰爭、黑死病、奢靡盛宴、雇傭兵制度、殘酷稅收、農民暴動和教會分裂……最終,承載著那一時代的廢墟被留在這里,靜觀著倣如宿命的人類歷史。
西方語境里的14世紀,大致相當于元末明初,在中國歷史上看來尚是一段封建王朝蒸蒸日上的時期,對于歐洲來說,卻是一段暗無天日的黑暗時光。作者對這個時代有著自己的定性:“在中世紀的下坡路上,人類失去了自己建設一個美好社會之能力的自信。”
14世紀的四次大的瘟疫暴發是吸引作者關注14世紀的一個重要誘因。但作者陳述她借助瘟疫的視角去透視14世紀的時候,必然會將她的視線移開去關注那個時代連綿不絕的“人禍”。如果說瘟疫是一種人類的自然災變的話,那麼戰爭,則是人性的災變,而教廷分裂則是信仰的災變。就是這樣的一連串的黑暗風景之下,作者點出了新時代的曙光已經隱現天際,那就是活字印刷開始出現,人類的知識與思想傳播有了更為廣闊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曾經……尋找發泄口的歐洲能量現在將于航海、發現和對新世界的殖民中去尋找其出口。”
《第一聲禮炮》歐洲視角下的美國革命
1776年11月16日,荷屬聖尤斯特歇斯島一個不起眼的要塞上傳來了隆隆炮聲,這是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進入外國港口時循慣例發出禮炮的回應。禮炮聲盡管微弱,卻首次宣告了那個世紀最為重大的事件——一個注定要改變歷史進程的新國家的誕生。
塔奇曼在這部作品中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書寫了美國革命,你會發現,女作家劍走偏鋒,有意拋開美國獨立戰爭的立足于本土的前因後果,而將她的視線拉扯到在一般正史中從未提及的美國獨立戰爭的外部支持因素,作者著重研究和描寫了當時的英國將領,法、荷兩國跟英國的舊怨以及對美國的幫助。這就是女作家在書中特別提及的“另一種視角”的意蘊所在,簡而言之就是歐洲視角下的美國革命。
作者採用了這樣一種外在的視角,其用意何在?又找到了什麼?我想,女作家的意圖明顯的是,將美國獨立戰爭放在全球化的語境里尋找到它的前世今生,這實際上體現出塔奇曼一貫的敘述策略,在她的歷史作品里,作者從來沒有將她的歷史目光聚集于世界的一隅,而始終關注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歷史走向問題。
《愚政進行曲》或是塔奇曼最大膽作品
這也許是塔奇曼最大膽的一部作品,在第一章里,開篇就說到了,政府的失當行為有四種,且通常不會單獨出現。一、暴政或壓迫。二、過度的野心。三、無能或頹廢。四、愚蠢或墮落。本書關注的是第四點,它具體表現為奉行一種與所涉及的國家或政體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應有利于維護統治主體的利益或優勢,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
塔奇曼一口氣舉了許多例子發問:盡管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將它拉到城里去呢?為什麼喬治三世的歷屆內閣,都寧可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的態度,而不採取任何安撫手段,盡管眾多顧問一再勸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什麼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侖,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所遭受的滅頂之災,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呢?……
在眾多例子里,塔奇曼最後選取了四個歷史時期來說明這個問題,分別是:特洛伊戰爭、文藝復興時期教皇導致的教廷分裂、英國喬治三世在美洲殖民地不切實際的政策,以及美國在越南的自欺欺人。
在《愚政進行曲: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爭》一書中,塔奇曼將對愚政的解析,深入西方文化之源,從“人類衝突的故事的原型”也就是特洛伊木馬傳統中,捕捉到了愚政的源遠流長的歷史。實際上,塔奇曼的歷史著作,有著內在的脈線,本書中分析的四個“愚政個案”,其實是塔奇曼歷史著作里一直孜孜以求加以思考的核心主題。如書中涉及的第二個愚政,即“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可以說是她的《遠方之鏡:動蕩不安的14世紀》的後延思考,而第三個愚政“英國失去美洲殖民地”,更像是《第一聲禮炮:另一種視角下的美國革命》的前傳。從中可以看出,塔奇曼的歷史作品暗脈相通,氣韻相連,前後照應,相輔相成,構成了一部立體的西方重大歷史的抒寫文本。
[責任編輯:楊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