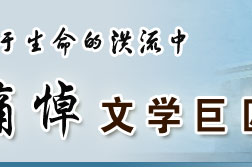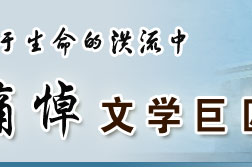| |
神六挾雷歸來,巴金乘風西去。
倣佛不想以自己的告別而衝淡人們的喜慶,捱過整整四天,老人還是走了。
一棵參天大樹轟然倒下,歷史的長河里響起了久久的回聲……
人們都知道巴金這幾年一直在病榻上與死神抗爭著,十分艱難,十分痛苦,離去,有時不失為一種解脫,然而,當他真的走了,人們都悲痛難抑。我們採訪著本市一位位文化名人,他們大都先是驚愕,轉而哽咽,甚至泣不成聲。我們用筆、用淚記錄著他們的追思,他們的緬懷,他們的慨嘆……
唉,又走了一個好人
周小燕(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唉,又走了一個好人。我十幾歲的時候,與巴金關係密切的弟弟周德佑(後在抗戰演劇團獻身)向我推薦這位年輕作家。我從法國回來後,便滿世界找《家》《春》《秋》,一看,就被小說中澎湃的激情感動。建國後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拿著書找不在同一組的巴金留言,記得當時他寫的是“我們都喜歡聽你唱的歌”。後來,丈夫張駿祥跟巴老常來常往,我也因此作客巴金家。盡管巴金工作繁忙,不記得有多少話可以說,但是,我一直是巴金的鐵桿書迷。尤其是巴老文革後陸續寫成的《隨想錄》,看了讓我震動。我最佩服他講真話,吃了那麼多苦,還是敢講,就是敢講。在我心中,他是一個偉大的人。
巴老走了,一個時代成為記憶
王安憶(上海作協主席):巴老就這麼走了,一個時代離我們更遠了。
巴老在的時候,這個時代還是有聲息的;現在巴老走了,這個時代就變成了一種記憶。我們這些人好像一下子沒有前輩了,接下來的時代要由我們自己扛了。
巴老從他這個時代出發,到現在已經走了很漫長的道路了,他實踐了“五四”以來藝術和社會的理想。他曾經為我母親感到惋惜,因為他知道我母親在創作的盛年遇到了文革,所以寫的作品不多。巴老雖然沒有直接對我說過什麼,但他生日時我們都會去看望他。巴老的話不多,看著我們總是開心的樣子。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他心里為我們感到開心,因為我們能夠盡情地寫作。巴老已經經歷和目睹過很多時代了,他最懂得一個作家最需要的就是寫作。巴老看著我們的眼光,使我們真的感到我們很幸福。
重讀作品是紀念的最好方式
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文學研究會會長):
巴金先生自己說過,他是“五四運動”的產兒。巴金先生出生于1904年,他十四五歲正值“五四運動”狂飆乍起,他的整個成長經歷都離不開“五四”精神的影響。巴老的一生完美地體現了“五四運動”的青年精神,他堅持真理、堅持自己的理想,在追求理想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激流。應該說,這種精神也是當時那個時代的總體風格、是一代年輕人的精神。這是因為這種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飽滿的生命狀態,我覺得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歲也仍然是個年輕人。我從20多年前的大學時代起就開始閱讀巴金、研究巴金,當時我見到了70多歲的巴老,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永遠停留在那個時代。巴金的精神是青年的精神,巴金的時代是屬于青年的,而巴金的逝世也象徵著這一青年時代的消逝。今天很多人不理解巴金,認為他的作品天真、單純、膚淺,這實際上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喪失了青春的熱情,變得追求功利和斤斤計較,看不到人生是需要有理想和熱情的。只要我們時代還需要青年的力量來創造未來世界,我想巴金先生就永遠不會過時的。
我認為紀念巴金先生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閱讀他的作品。巴金的小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作為一個研究巴金的專家,我要說巴金的作品沒有過時。《上海文學》即將推出巴金的紀念專輯,但不打算請人寫紀念巴老的文章,而準備重新刊登巴金的小說,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來讀他的作品,認真地思索其中的意義,這才是紀念他的最好方式。
活著是一種力量,走了是一個榜樣
徐開壘(《巴金傳》作者):巴老活著,就是一種力量;他走了,依然是一個榜樣。長時間以來,他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前輩,從此,我們失去了一個大師。我現在非常希望包括李小林在內的巴老家屬能夠在今後多發表一些文章,因為只有他們才真正生活在巴老的最後歲月里,也真正能夠把巴老的最後那段生命時光告訴給想了解巴老的讀者。
巴老對年輕人寫作非常鼓勵。我那個時候做過報社的文學編輯,有時候,他會把一些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的優秀作品推薦到我這里發表。去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手記》,記錄了1962年11月到1965年年底巴老在上海期間的全部手記,這些手記里很多是《巴金全集》里不曾收錄的,里面就不止一次地提到與青年文學愛好者之間的交往。他培養了許許多多作家,他的學生中很多都成為了後來的名家,有些卻比他早去世。
這盞燈永遠不會滅
趙麗宏(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昨天傍晚四點多,我趕到了巴老所在的醫院,一直陪伴到他去世。
他是這個時代的文學巨匠,但對我們來說,他就是一個慈祥的老人,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可以這麼說,我文學的座右銘是他贈我的。那是1984年,我鼓足勇氣寫了一封信給了巴老。信寄出後,就後悔了。當時想,巴老年紀這麼大了,又這麼有名氣,這封信極有可能石沉大海。哪知兩天後,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同時也收到了他寄給我的一本《序跋記》。他在信中贈我兩句話“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這兩句話從此成為我的座右銘。”
這兩句話的涵義其實同巴老一直提倡的‘說真話’是一致的。他的《隨想錄》就是“說真話”的最好代表。他像一盞明燈,生前照耀著文壇,生後也將繼續照耀。
他影響了我的藝術人生
朱踐耳(著名作曲家)我跟巴老神交已久,他影響了我的藝術人生。
巴老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認為,他對于我的最大意義和震撼,是敢于反思自己,懺悔自己,解剖自己,由此反照一個民族的性格。知識分子應當是第一個能做到以史為鑒的,應該用深刻的人文精神來觀照人類。在我的晚年,我多麼渴望也像巴老那樣,用音樂凸現對社會、對時代的人文的思考。可是我做得那麼不夠啊!巴老生前的願望,有的已經實現,有的還沒實現。我們繼承他的遺志,實現他的願望。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記者 齊鐵偕 姜小玲 伍斌 李君娜 韓璟 集體採寫
責任編輯:劍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