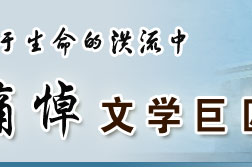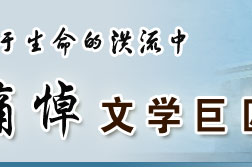| |
新華網上海頻道記者 趙蘭英10月17日報道:一個多世紀的生命長河,淌過崇山,流過峻嶺,穿過峽谷,在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喚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國文壇的參天大樹倒下了。
偉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國文壇,存活于人們心中的。他留給我們的財富,是以數字無法計算的,是以金錢無法買到的,是以文字無法表全的。文壇,因他而生輝;國家,因他而美麗;人民,因他而自豪。
“祖國永遠在你身邊”
“你是光,你是熱,你是二十世紀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書下此言,讚美巴金。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說《滅亡》,被人們認識以後,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光和熱,逐漸成為中國文壇的領軍人,並且長達數十年之久,無人可以替代,沒人可以撼動。巴金的光和熱,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採譯著。這一筆豐贍財富,中國幾代人已經享受了,還會被幾代、十幾代甚至更多的人享用。巴金的光和熱,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這一筆巨大財富,更被人推崇,為人瞻仰,受人感化。
愛國主義,是巴金兩大財富的重要基礎。從年少到年衰,巴金的愛國情懷,從未受任何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反之,更熱烈。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風雲跌宕,世事亂變。她,曾經受三座大山壓迫,貧窮、落後、愚味。她,曾經受種種幹擾,走過許多彎路,使人迷惆、心慮、屈辱。巴金沒有厭棄這一切的一切,始終用行為,追求心中的理想,表達自己的情愫。
巴金12歲那年通讀了《說岳全傳》,深深被岳飛的愛國精神、民族精神震動。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到了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詩話》。書中,明代詩人兼書畫家文徵明的《滿江紅》詞,使巴金愛不釋手,百看不厭。巴金一直將這本書珍藏在身邊,即使在“文革”動亂中,家被數次抄劫,這本書也沒有被毀。上世紀90年代,巴金在眾人的勸說下,到杭州休養。從來怕麻煩別人的他,有一天卻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謁岳墳。在岳飛塑像前,輪椅上的巴金目不轉睛,久久地凝視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深深被這一情景感動,誰也不輕易移動一下腳步。後來,他們來到文徵明《滿江紅》詞碑前。此時,年過九十,平時說話吐字不太清楚的他,卻象小學生那樣吟誦起這首詞來,那聲音越來越清楚,越來越高亢:“拂試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每一句、每一字,其實巴金早就熟背心底,融化在血液中。
巴金是一個不善言笑的人,雙眉總是緊鎖著。冰心老人曾經快言快語笑評她的這位“老弟”:“他很憂鬱。我看,他痛苦時就是快樂著。”憂鬱、痛苦,是巴金愛國情懷的一種表現。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且終身都在追求著。他希望他的祖國強大起來,人民富足起來。他曾說:“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來表達我的無窮無盡的感情。”
這是一段巴金撰寫的關于《滅亡》的創作經過:“每夜回到旅館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于是,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這樣的環境里,過去的回憶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清、希望和掙扎,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一顆寂寞年輕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里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面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我一面在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里我寫成了《滅亡》底(的)前四章。”
1979年,巴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巴黎。這是離別巴黎半個世紀後,巴金第一次再踏上這片國土。故地重遊,對于任何人都會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靜靜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長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雙眼井,廣州的鄉村……他說:“就這樣,我每天回到我親愛的祖國,心里很充實。離開祖國,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我是中國人。這個感覺,50年前也有過。我們常把祖國比作母親,祖國確實是母親。但是,過去這位母親貧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兒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國境,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有一雙慈愛的眼睛關心地注視著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終擺脫不了祖國,祖國永遠在你身邊。”
在很多榮譽前,在許多外事場合,記者多次聽他說:“我生長在中國,我的一切都屬于中國人民。”1983年,巴金在獲得法國榮譽勳章時,對前來授勳的法國總統密特朗說:“謝謝總統閣下光臨上海,在我病中給我授勳。我認為,這並不是我個人有什麼成就。這是總統閣下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尊重,對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的尊重。這是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象徵。”
“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革除舊思想、舊意識、舊制度,迎來一個具有民主、自由與科學精神的新中國,是巴金畢生理想。
用全部的真誠和熱情,關愛人民,“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巴金的心里始終珍藏著這一美好的願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正通順街一個封建大家庭。仁愛的母親,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老師。他從母親這里懂得了愛,懂得了寬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師是轎夫老周。那時,他常去馬房,躺在老周的煙燈旁,聽他講故事。每講完一個故事,老周總要教育他:“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佔別人的便宜……”他還時常去廚房,幫助他們燒火。坐在灶前的石頭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進去,結果常常把火弄滅了。這時,老周就把他拉開,用火鉗往灶膛里捅幾下,火又蹭地燒起來了。老周放下火鉗,關照巴金:“你一定要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後的巴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是什麼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講出這番深刻的道理。這就是仁義、道德、忠愛。而恰恰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根,是為人之本。
巴金是一個不善言談的人。他把他的愛,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此,巴金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反映了時代的呼聲、人民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內容。這也是巴金作品,在經歷70多年後,仍為今天的讀者,接受與喜愛的根本原因。
在巴金許多文論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為,熱烈地愛人民,幫助那需要愛的,反對那摧殘愛的,在眾人的幸福里謀個人的快樂,在大眾的解放中求個人自由。”“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著春天,每顆心都得著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著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著自由。”“我的敵人是什麼,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場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
他善待每一個人。在朋友面前,總是赤誠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蕭乾受到莫須有的批判。這時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眾場合,大聲地喚著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邊,悄悄地關照他:要謙虛,要謹慎。而當曹禺,頭上的頭銜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時,他卻批評他:不要太顧及事務,應該多寫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後,他又囑人幫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發表過的文稿,留下曹禺在最後的真實形象。
巴金對于他人的關心,從來都是潤物細無聲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風中修整花苗的師傅,就擔心師傅會凍著,便趕快讓家人買來羽絨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張、小吳,從農村到巴老身邊工作,一晃多年過去了。巴金一直擔心,自己百年後,這2個孩子怎麼辦?有一天,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翟泰豐來探視,問巴老有什麼要求?從來不象組織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張、小吳的工作。一樁樁、一件件,在巴金身邊或與巴金有過接觸的人,都會說出許多故事,由衷地說一句:“巴老這個人就是好。”
仁愛、忠誠、正義、自律,人道主義相伴巴金一生。
“讓生命開花”
文品與人品的高度一致,是巴金身上最為感染人的地方。
巴金在晚年,多次與記者談及這樣的話:“我現在不能工作了。但是,我的一顆心還在燃燒。我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所寫的和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探究巴金的一生,是巴金人格不斷完美的一生。而貫串始終的,是他的“讓生命開花”的奉獻精神。
在巴金的隨筆、序跋、通信、言談中,我們讀到許多巴金關于“讓生命開花”的論述,我們更看到一位有著獨立人格思想的老人,渴求生命開花的迫切心情:
“世間有一種不能跟生存分開的慷慨,要是沒有了它,我們就會死,就會從內部幹枯。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朋友》(1936年)
“寫到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陣霧,滿腔淚水中我看見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麗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異卉?不,不是。我從未到過沙漠。它若隱若現,一連三天,不曾在我腦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致衛縉雲信》(1986年)
“我願意再活一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讓我的生命開花結果。”--《給和平街小學學生的信》(1990年)
“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結果。否則我們就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斷地自問:我的生命什麼時候開花?那麼就讓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演,再活一次!”--《讓我再活一次》(1991年)
“有人問我,生命開花是什麼意思。我說:人活著,不是為了白吃幹飯,我們活著要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這個我們辦得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維持我們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一心為自己,一生為自己的人什麼也得不到。”--《致東城根街小學的信》(1991年)
……
巴金還在剛踏上文學之路時,朋友約他到自己辦的書店做編輯,每個月給80元大洋。可巴金卻說:40元就夠了。他將第一部小說《滅亡》的稿酬,給了一位生活困難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創作的高峰時期,他卻將14年的寶貴時間,用在編輯他人的書上。而且不取分文。解放後,他是中國唯一不拿工資的作家。晚年後,他悄悄地,將稿費、將藏書,一一捐了出去。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憶這一幕: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時,巴金雖行動不便,還是來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發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後摸出一個紙包來,交給舒乙,說道:“剛收到的稿費,上繳。”舒乙說:“我當時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他這個人完全透明。愛祖國、愛人民,樂于奉獻自己。”
在中國文壇,一代又一代作家,感受到巴金生命之花發散而來的幽香。1936年,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胡風的錢包被人偷了。巴金曾看到胡風掏錢給人,又隨意地把錢包往口袋里一塞,當時就當心,人這麼多,會不會被人偷走。想去提醒他,又擠不過去。葬禮結束後,人群像潮水似地散去。巴金看到,胡風在原地正著急地尋著什麼。趕忙走上去一問,錢包果真被人偷走了。巴金當場就建議:“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幫助他。”那時,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總編輯,便和社長吳朗西商量,以預支稿費的方式,解了胡風的燃眉之急。30年代,劉白羽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學青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見到了巴金。巴金告訴他文化生活出版社準備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劉白羽自然很高興,但著急自己連一篇剪稿都沒有帶來。這時候,巴金拿出一個紙包,說道:“我已經幫你編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沒有修改的地方。”劉白羽拿來一看,自己在這一年中發表的作品,全被剪貼在這里,整整齊齊。這便是劉白羽的第一本小說集《草原上》。
在他身邊工作40余年的徐鈐,平實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總覺得自己欠別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獻。而現實生活中,大多人總認為別人欠自己的。于是,心態很不平衡,怨這怨那。要說我們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這點上。但是,就這點差距,很難趕,趕也趕不上。
一個世紀的不凡人生,巴金為社會創造了無比輝煌的財富。而他在最後,對自己卻是那樣“苛刻”:他一次次提出,不能工作了,是廢人了,不要用好藥了,安樂死吧。
“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隨想錄》是巴金晚年奉獻社會的最為恢宏的財富。
1978年的中國社會,思想解放的枷鎖,還沒有打開。75歲的巴金,思想卻異常的活躍和深邃。那時,他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並不多了,應該先將憋在心里的話說出來,也許對社會更有用。于是,他拿起筆,寫下自己“隨時隨地的感想”。沒有想到,這一寫就是8年。他的思考越來越深邃,批判越來越深刻,感情越來越深厚。
當全部150篇刊完,《隨想錄》合訂本出版時,巴金自己在《合訂本新記》一文中寫道:“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濃血。我知道不把濃血弄幹凈,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樣的濃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歷史又走過近20年,人們對于《隨想錄》社會與歷史價值的認識,更為清晰、深沉:
“真是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他在很多篇章里,毫無保留地深刻剖析自己的靈魂。邊讀邊想,我們的靈魂也在受剖析。實際上,他是在剖析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社會,我們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當代的中外讀者和後代子孫,要知道十年浩劫之後,新中國歷史的轉換關頭,我國知識分子最優秀的代表,中國作家的領袖人物在想些什麼,日夜揪心地在思索些什麼,可以從這些文章里得到些領悟。我們珍視這些文章,因為這是巴金全人格的體現,是巴金晚年最可貴的貢獻。”--張光年
“我在讀巴金《隨想錄》的時候,感到巴金既有一顆火熱的心,又有一副冷靜的頭腦,所以能夠用熱烈的激情感染我們,用清醒的思想啟迪我們。我們民族有著古老的傳統,這有好也有壞。古老的文化給我們提供了傳統的資源,可以使它和現代化的建設接軌。但是也要提防死的支配著活的。魯迅以他的諷刺揭示了這一點,巴金以他的熱情揭示了這一點。無論魯迅的諷刺和巴金的激情在文學風格上存在多少差殊,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有著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愛憎。”--王元化
“這是一部反映了我們時代聲音的大書。從眾多的側面反映了我們時代和歷史發展的一個清晰面貌。里面包括了作者對于社會生活、思想生活、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啟迪意義的思想光輝。這部巨著在現代文學史上,可與魯迅先生晚年的雜文相並比。”--馮牧
“讀這些散文隨筆的感受,不同于讀他早期的小說。他呼喚著我們同他一起,用自審、自省、自責的心情去反思那記憶猶的被扭曲了的歷史。作為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作家,他對人民人民、對人類的摯愛,已經達到了至純至深的境界。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應該以巴老為楷模。”--袁鷹
“巴老的這些短文可寶貴--只因為它是真話。巴老自己說寫的不是傳世之作,我以為確是傳世之作--也只因為它是真話。”--諶容
“《隨想錄》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變遷史。《隨想錄》充滿了嚴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這方面魯迅是一個榜樣,巴金是又一個榜樣。有沒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內心生活,是真作家和冒牌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線。敢于首先起來衝開無邊的黑暗,打破無底的沉默的人,需要最大的勇氣,因此也應該受到特別的尊重。”--柯靈
“《隨想錄》的每一篇、每一章,幾乎都流淌著巴金靈與肉的血。他無情地拷問、譴責自己,揭開自己身上最痛苦的傷疤,展示自己全部的思想,呼喚講真話。巴金的《隨想錄》可以稱之為《懺悔錄》。從現代意義上說,這本《懺悔錄》超過了盧梭的《懺悔錄》。”--陳思和
“他用顫抖的手鐫刻,用滾燙的心熔鑄的書,是矗立在世人面前的一座‘文革博物館’,它時刻告誡經過‘滅亡’後得到‘新生’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在中華大地上曾發生過的這段可悲的歷史,它也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之火,這熊熊的火便是巴金捧給讀者的一顆滾燙的心!”--陸正偉
……
于是乎,一個壯觀的景象出現了:平裝本、精裝本;分冊本、合訂本;精選本、全選本;簡體本、繁體本;線裝本、手稿本……不同版本的《隨想錄》,在近20年中,不斷走向讀者手中。據記者了解,《隨想錄〉是當今中國書籍中版本最多的一部,起碼有15種。
“我也把火傳給別人”
年輕時,巴金是一個讀書狂,任何可以能借到的書刊,他都會不分晝夜地閱讀。也正是書,引他走向文學。1984年,巴金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47屆國際筆會。會上,巴金作了《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的演講。81歲的老作家,無限深情地談起了自己的創作經歷:“我是從讀者成為作家的。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從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的養料。文學作品用具體的形象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較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作者們的愛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輩作家把熱愛生活的火種傳給我,我也把火傳給別人……我們有一個多麼豐富的文學寶庫,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來的傑作,它們支持我們,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要我們勤奮寫作,使自己變得更善良、更純潔,對別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
“我也把火傳給別人。”正是在這種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在百年中國文壇,點燃3把熊熊大火:
--是他1300萬字的不朽著作和譯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一部分極為精採。《家》、《春》、《秋》、《第四病室》、《憩園》、《寒夜》……他的許多作品,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奠基作、代表作,不僅在現代文學史上,也在社會發展史上留下不可估量的作用。表演藝術家林默予談到,她從小就賣給了人家當童養媳,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讀到了巴金的《家》。她被《家》中所描繪的反封建思想所感染,毅然出逃。因此,是巴金的《家》,改變了她的人生道路。誠如林默予,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又有多少青年人,在《家》的感召下,改變生活命運的?錢正英同志,在巴金90歲生日時,代表全國政協前來祝壽。在巴金寓所,錢正英說:“巴老,我是在您文學作品影響下,走向革命的。”有一位名叫程永照的讀者說,他們一家4代人受巴金作品影響,10歲的侄女和女兒,都能背誦巴金的《繁星》和《海上日出》。
--是他在出版崗位上,為文學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1935年,正是巴金創作最為旺盛的時期,他卻以極大的熱情做起了出版工作。上海淪陷以後,巴金把這個小小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辦到廣州、桂林、成都、重慶等地。魯迅、茅盾、鄭振鐸等前輩大家;沈從文、魯彥、張天翼、黃源等當紅作家;曹禺、艾蕪、麗尼、卞之琳等初露頭角的作家;劉白羽、陳荒煤、端木蕻良等尚不見名傳的作家,都被巴金團結在這一陣地上。于是,中國文學史上有了這樣一大筆財富:《故事新編》、《駱駝祥子》、《邊陲線上》、《前夕》、《還鄉記》、《人生採訪》、《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路》、《八駿圖》、《憩園》、《運河》、《山野》……中國讀者有幸讀到這樣一大批世界譯著:《死魂靈》、《上尉的女兒》、《父與子》、《處女地》、《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簡愛》、《萌芽》、《大衛?∟高柏菲爾》、《包法利夫人》、(凱旋門》、《雙城記》、《柔米歐與朱麗葉》、《高爾基傳》……
--是他倡議建起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從巴金夢想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館,到中國現代文學館聳立在北京朝陽區,歷史經過了20年。在巴金心里,建一個文學館遠比自己再寫幾本書重要得多。這是一個關係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光澤子孫後代的大事。他不僅倡議,率先捐出自己的存款、藏書、文獻。他向朋友們鼓動,撰文呼吁。甚至,他向國家領導人致信求援。他說:“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我絕不是為自己,我願意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今天,當每一位對著巴金手印,推開文學館大門的讀者,都會為擁有這麼一座富有的文化寶庫而自豪。
巴金留給我們的財富,無以倫比。它是中華民族不可多得的重要精神財富。
生前,一首《那就是我》的歌,曾如微風吹進巴金的心田,讓他想起了家鄉,想起了朋友,想起了童年……他動情地說:“我家鄉的泥土,我祖國的土地,我永遠同你們在一起接受陽光雨露,與花樹、禾苗一同生長。我唯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里。”
山在呼喚、水在呼喚……華夏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每一片都在呼喚、在呼喚:巴老,您將永遠與祖國同行,與人民同伴,與日月同輝!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劍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