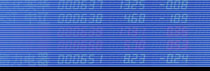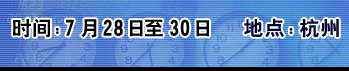| |
(摘要)
本文旨在說明兩岸政府爭衡,臺北政府已經失去中國人合法政府的“法統”,且從九十年代開始,由于積極推動去中國化運動,中華文化在臺灣已經淪為七支文化傳統之一,臺北政府也失去了中華文化擔負者的“道統”。北京政府在全面獲得“法統”的同時,也應該作為中華文化擔負者,在神州大陸恢復中華文化的“道統”。這樣,北京政府就能真正獲得四海(包括臺灣人民)的全面認受而創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代哲學家牟宗三先生,以“理型”(form)和“材料”(matter)的觀念說明一個文化體係。他認為,文化的“理型”是一個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個文化體係所秉持的宇宙觀、世界觀、人性論和以此而有的是非價值觀。這一個部分,能夠決定一個文化的原則和方向。至于,體現“理型”的種種經驗活動,例如藝術、音樂、建築、宗教活動、風俗習慣等,則是一個文化體係的“材料”。中華文化雖然隨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音”和“材料”,但“理型”卻是儒、釋、道三家思想。一種文化的理型,就是這個文化的“道統”。
本文藉由康德哲學的“三種價值”理論:市場價值(market price)、藝術價值(fancy price)與道德價值(moral dignity),說明文化的“理型”體現道德價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理型”則只具備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中華大地保存了中華文化豐富的“材料”,但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中華文化的“理型”至今隱而不彰:
(一)近百年西方文化的衝擊,人民的精神面貌漸漸有被西方文化取代的趨勢。
(二)四九年後神州大陸則提倡馬克思、列寧主義,繼而有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並不重視甚至破壞鄙夷。
當此中華民族展望自強之時,北京政府首當妥善保存中華文化的“材料”,即歷史文物、藝術傳統與風俗民情。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文化的意識,避免使中華文化淪為只具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材料”。如是,則應該自覺恢復中華文化的“理型”,涵養中華文化的精神,這樣才能體現中華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兩岸的統一和我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自強。
國共內戰造成了北京政府和臺北“國民政府”兩個彼此不承認而各自宣稱為“中國人唯一合法政府”的政府。兩岸政府“法統”之爭隨著七一年北京政府獲得聯合國的承認、九一年李登輝“修憲”改選“國民大會”,到今天“中華民國憲法”即將完全失去其作為“中國憲法”之地位,臺北政府已經放棄“法統”之爭,事實上也已經再無資格從事“法統”之爭。北京政府隨著不斷精選,積極改善國民生活,于國際和人民認受層次皆已取得正當法統地位。五十年來,“國民政府”由繼承法統到放棄“法統”,北京政府由革命獲取政權到全面繼承傳統,兩岸政府“法統”之爭形成兩條方向逆反的曲線,一衰落,一冉冉上升。
然而我國自古以來,“法統”的獲得必伴隨“道統”的繼承。簡而言之,中華民族的“道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的道德文明和學術文明。五胡亂華、五代和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原,獲得政權然而與中華民族的“道統”睽違,不但國祚甚短,史家論中華民族“法統”之時甚至無法將之納入正統。有鑒及此,清人入主中原尊孔子、修孔廟、開科取士、敬聖人之書,延襲“道統”,其法定地位始正式獲得天下的承認。
“國民政府”在蔣介石、蔣經國主政之時,致力提倡傳統倫理,發揚孔孟精神。1952年即在臺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基本任務是:
提倡民族文化的研究、創造,並推行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的各項文化建設;鼓勵公私立文化學術研究機構,從思想上、學術上弘揚中華傳統優良文化;協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增進民族智能,發揚民族道德,蔚為正義磅薄的民族人格;推行國民生活須知,加強國民生活教育,並研定文物典章制度。
“國民政府”在臺灣雖小,可是由于積極擔負“道統”,得到世界各地華僑的向心。從九十年代開始,由于積極推動去中國化運動,臺北政府失去了“道統”擔負者的身份。中華文化在臺灣已經淪為七支文化傳統之一,臺灣教育協會師大教授莊萬壽明白宣示:
臺灣要做為一個獨立的有主體性之文化,則必須擺脫于附屬于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並且要走出自賤于大陸中原文化的陰影……臺灣不是要擺脫漢字、漢文化而是把臺灣自己的漢文化獨立于中國之外,切斷大陸中國的文化情結,使之重新與南島、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現代的臺灣新文化。
近年,國民政府由繼承“道統”到放棄“道統”,北京政府由輕視甚至破壞“道統”到重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兩岸政府對“道統”的態度也正好形成兩條方向逆反的曲線,一衰落,一冉冉上升。2002年8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我們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高度,深刻認識加強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要大力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鼓舞我國各族人民不斷前進的精神力量。
這番話顯示北京政府對發揚文化“道統”以復興中華民族的識見與決心。陜西皇帝陵公祭禮儀也將由2004年起升格為國家級儀式進行,祭典程序會分成十二大項,祭禮主持人穿漢代禮服,使用天子級器具進行公祭,而在每五年舉行一次的皇帝大祭中,更會由國家領導人負責主祭。
為了使“道統”在今天的繼承與復興有更明確的方向,僅就文化的理型與材料論說如下。
【第一節:理論(一)文化的理型與材料】
在廣義上,文化是指人類思想、行為與人類活動產品的總和。在此意義上,文化與生物本性截然不同,並且一直用來區別人類與動物。在狹義上,文化包括藝術、體育、娛樂與其他休閒活動,此中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辛格爾編的《美國哲學》解釋說:“一種文化是由習俗、傳統、理想與價值觀念組成的相關網絡。”
本文旨在打破社會科學對“文化”籠統的解析,以哲學的角度建立一套探討文化價值的方法。然而,文化價值的探討,是對在同一文化體係之內各種活動產品的價值的確定,此中並不涉及不同文化體係之間的價值問題。甚且筆者認為,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完整的體係,他們有共同的形上根源,而表現為不同的經驗活動。因為其形上根源相同,萬法歸宗,因此不必比較高下;又因為其經驗活動各有特性(particularity),故不能比較,一比較即生偏見。這是近年宗教哲學家約翰.希克“宗教多元主義”的要旨。本文遵循此要旨不對文化做橫的比較,而僅就一個體係之內其人文化成的價值問題作縱向探討。
牟宗三先生畢生“反省中華文化生命,以重開中國哲學之途徑”,他採用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至康德的一種分判事物的觀念,來認識一個民族的文化體係。對于判斷一個文化的生命有無,牟先生提出一種很有智慧的方法。柏拉圖、亞里多士德以至康德都認為一事物的組成有“理型”(form)和“材料”(matter)兩個部分。正如一個花瓶是圓形或長形,有它的型態,這個圓形或長形型態就是它的“理型”,至于它是玻璃的、瓷的、木的、銅的,這是它的物質部分(materials),稱為“材料”。型態是一種概念,是看不見的,要有了物質部分才表現出是圓的或長的。但是光有“材料”也不成物,材料必須依循“理型”構作出來,才能為一個花瓶。牟先生用哲學上“理型”和“材料”的觀念,來分析一個文化體係,他說道:
簡單地說,形式(理型)即是它自己本身是一原則、是一方向。凡是文化,必然涵著它有自己的原則與方向,否則就不能算文化。……不能夠作為原則,不能夠自定方向,則這文化就只是個材料,而不是形式“理型”。因此,一個文化若只有作為材料的身份而不是形式(理型),它就不能算延續下去。
文化的“理型”是一個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個文化體係所秉持的宇宙觀、世界觀、人性論和以此而有的道理價值觀。這一個部分,能夠決定一個文化的原則和方向。至于,體現“理型”的種種經驗活動,例如藝術、音樂、建築、宗教活動、風俗習慣等,則是一個文化的“材料”部分。舉例而言,中國人盛行供奉關帝君,關帝廟、關帝誕的活動、供奉的儀節、音樂、唱譜、食品,都是文化。但這些是關帝文化的“材料,它的“理型”是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關帝是道教神明,他生前為人景仰的是對國家、黎民、君上、兄弟的忠義,因此關帝文化核心,是天道的生生之德、人道的忠、孝、節、義,無此,即無關帝。
中華文化雖然隨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音”和“材料”,但“理型”卻同是儒、釋、道三家思想。儒、釋、道三家義理雖也有差異,但浸潤于民間,百姓日用為常的,無非是一份對個人良知的肯定,由良知而體會到仁、義、禮、智,體會到親親與尊尊,體會到個人、社會、天地之間所具有的相契相融的關係。這種宇宙觀、倫理觀,浸潤在中華文化的每一個角落,是每一個地方文化的原則和方向。本此“理型”,各個地方隨其山川風物、人民性情,而呈現主觀的(subjective)色彩,例如北方沉穩厚重、江南柔麗婉約,這種色彩,就是“材料”的特質。牟宗三先生強調:
形式(理型)是個框框,是個圈套,把框框加到材料上去,材料就隨著理型而轉。材料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是被決定的而不是能決定的……
如果我們復興中華文化,只著眼于中華的語音特色、風俗習慣,或盡力介紹中國的文學、藝術、戲曲、文物、古董,這是外國人看我國文化的方式,文化的“理型”並未自覺體現。那麼,中華文化還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文化。
【第二節,理論(二)康德的三種價值論】
從事物的組成因素來看,“理型”是文化的第一義。“材料”是第二義。而它的傳播手段:出版、傳媒、教育、旅遊、展覽則是第三義。要一個文化有生命、有內涵,一定要先鞏固第一義,然後讓材料和傳播說段自然表述它。這個次序是不能隨意顛倒的。
但是,“理型”和“材料”的概念比較抽象,我們可以借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基礎》一書中指出事物的三種價值,來了解文化的“理型”與“材料,從價值的角度來看一個文化的精神和道德層面的內容(“理型”)的重要性。他首先區分“有價”和“尊貴”:
人、事、物的衡定,可以分為“有價的”(paice/value)和“尊貴的”(digeity)兩種。能被另一樣東西等值取代的,具有價值。超越任何有價之物而無法被任何一物取代的,不能用價值說明它的地位,只能以尊貴形容之。
然後肯德說明有價的市場價值、心智藝術價值,和無價的尊貴:
和人的欲求或需要有關的事物,具有市場價值(market price)。人類以其智慧才華發明創造出來的結果,例如文學、藝術、科學等等成品,即便非人們生活所需,甚至是完全無所謂而為的腦力活動,都能說是具有心智價值、藝術價值(fancy price)。唯獨那不可比較高下的、本身有就是一個最終目的事物,具有尊貴的價值。因為,它的價值不是被外界衡定的,它本身就是一件尊貴的事物(dignity)。
對康德而言,道德實踐、道德情操(包括廣義的宗教精神)是無價的,它本身就是最可尊貴的,是“人的尊嚴”的要素。
技藝和工作的勤奮,具有市場價值;智力、豐富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具有心智和藝術的價值;由衷的誠信與仁慈,無法以價值衡量,它本身就是最尊貴、最可敬的。
其他的事物,固然有市場價值或心智、藝術的價值,在市場價值或心智、藝術價值的范圍內,固然也有高尚、低俗之分,也可獨立成為一種價值體係。例如京戲有技藝也有美感,我們完全可以從藝術價值或市場價值的角度衡量它們存在的意義。但這屬于孔子所說的“遊于藝”的部分,如果完全不看他們內容所表現的精神價值或道德價值,則他們的生命還不完全。孔子論音樂和武樂:
子謂韶,盡美矣,又畫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按朱熹《四書集注》解,“美”指音樂聲容之盛;“善”是美之實。大舜以孝聞名,而且他的權力由和平禪讓而來,所以他的韶樂既有藝術價值(美),又有道德價值(善)。武王德遜于大舜,天下以徵伐而來,所以他的音樂還不盡善。
當然,不少美學或藝術的觀點,反對以思想成分或道德成分評價一份藝術作品,甚至反對藝術作品說教。但這是光就一份作品的藝術價值而說。完全撇開思想價值和道德價值,一份作品可以有它獨立的評價。但是,若就一個文化體係而說,文化是一個大群集體的人生。就像一個“人”,我們不能光看一個人的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我們還必須看他的思想和道德,才能作真正的評價。文化也是如此。不能光看這一個群體生命的傳統與創作有什麼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而必須重視它的宇宙觀、道德觀。用“理型”和“材料”來參證,則文化的“理型”體現思想價值和道德價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理型”則只具備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
舉例說明。京戲“三娘教子”家喻戶曉,為各地方戲曲所改編。不論各地戲曲的文學、唱腔、身段的色彩如何,三娘教子故事蕩氣回腸之處,在于三娘對兒子的慈愛、對丈夫的堅貞、對公婆的孝順,在在道出中國人家庭人倫的理想。這種滲透在藝術內里的“情義、道義”,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是指導中華文化以方向的“理型”。雖然並非每一種文化產品都明顯地表現思想,表現道德情操,但總或隱或顯可以看見儒、釋、道三家思想在中華文化和中國人生命里貫穿著,表現著中國人特有的尊嚴。無此,則文化產品即成消遣、裝飾、古董、失去生命力。
【第三節 現代化衝擊下的中華文化】
但是,中華文化近百年正面臨現代化的無情衝擊而有斷滅的危機,中華文化的次元文化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這衝擊可以從三方面考察。
第一,中華文化的理型快要被西方文化取代了。
牟先生之所以大聲疾呼,提出文化的“理型”與“財力”問題,因為近百年中國內憂外患,連帶著中華文化的思想核心大受質疑。從民國初年開始,中國成為各種西方宗教、學說的實驗場。儒、釋、道思想再不是顯學,也失去了從天道以至人道的有機連結,只剩五倫八德零零碎碎出現在百姓生活之中。取代中華文化核心部分的,是西方現代文化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牟先生並不是反對民主和科學,相反的,他認為這兩項現代文明是我們該急起直追的。但是他深信,一個民族不能失掉自己的特性,也就是自己文化的“理型”不能被取代。他說:
本來如果一個民族仍然存在,那麼這個民族的文化總可以延續下去,無所謂斷不斷。但這其中也有一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卻不能盡其作為原則並自己決定方向的責任……只勝作為材料的身份,而形式(理型)是外加的,不是由這民族文化之根涌現出來的,則此民族的這文化就不能算延續下去。
從一個民族和她的集體人生(文化)的關係看來,一個文化體係若只剩“材料性”的東西,文化即不成體係,無異于斷滅。而這個民族,物質的生命仍然存在,精神的部分卻已經被西方文化所取代,這民族無異消亡。
第二,多元主義的文化觀促使我們忽略以自己的文化為主體。
牟先生提出文化的“理型”“材料”論點時,他所面臨的問題是西方(westernization)。然而到了上個世紀最後三十年,韋伯(Max Weber,1864—1920)對“現代性”(modernity)所指出的一個特性,便越來越顯著。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世界的解咒(disenchantment),傳統的宗教觀和道德信念都不再是各個傳統文化的主宰。世界變成一個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當前,“多元”(pluralism)成為一種時尚。各種信念一體平鋪,社會強調的是對各種信念和見解的接納與寬容,而不是對信念、見解本身的了解和實踐。對中國人來說,中華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種;對閩南人來說,閩南文化僅是中國地方文化的一種,更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種。我們的生活里,充斥交疊著各種不同的文化“理型”與“材料”,慢慢地“文化”一詞的含意只剩下“材料”的雜多。自己的民族文化,再不是生活的主要方式,而僅是眾多生活方式的一元。則中華文化之于中華民族,由其“理型”有被西方文化替代的危機,進一步變成文化的“理型”和“材料”都不能居民族的主導地位。
第三,近年有論者把“文化”和“藝術”並稱。這起初是探討藝術對社會的影響,風流所及,漸使文化的探討和追求偏向“材料”和藝術價值,忽略其內在“理型”。
文化的探討和追求偏向“材料”和價值,也是現代性的一個延伸。當世界變成一個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信念、道德是非這一個層次的問題已經變得無法討論,能夠客觀討論的或衡量的,只有材料性的東西。如此即演成道德中立主義(moral neutralism),對事物的分析,應把信念、道德的問題撇除在外。因此,政府的政策、學者的建議,在談怎樣保存古跡、發揚傳統藝術、吸收現代藝術方面,都饒有成就;大家也都很願意付出時間和資源,整理、維護、開發中華文化里的“材料”,認為這就是復興文化和發揚文化。如果這些“材料”帶有市場價值,就更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但是,如果文化內在的“理型”和“道德價值”“思想價值”被忽視了,文化產品即成為死文化,終歸不會流傳太久。
【結語:保存中華文化的材料、恢復中華文化的理型】
文化的“理型”和“材料”的提出,旨在激發我們深層的文化自覺。我們在熱愛、發揚自己的文學、藝術、文物、古跡、風俗習慣的同時,不能不自覺地復興自己文化里的指導原則。唯獨當中國的固有倫理重新成為人民生活的信念,人們體會到它的價值並且自願地實踐它,中華文化精神才算能夠指導我們民族的方向,中華文化和它的地方文化才算真正存在。而在這樣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有主有次,才算是健康的發展。
然而,在我們國家急速發展經濟、從事現代化物質建設的這一時期,有一事更值得注意,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材料”應該自覺保存,不可為了功利的目的,濫拆濫建任其消亡。例如:很多戲曲因為沒有太大的商業價值,即將失傳;不少文物古跡在城市建設中幾為發展商拆去殆盡。這都是不可挽回的損失,直接促使了文化的斷滅。文化的“材料”雖不自生,但是沒有了“材料”,則文化只成抽象的觀念。正如花瓶有形無質而不成花瓶,文化有“理型”而無“材料”也不成文化。再者,文化是一個“傳統”,傳統是在時空中流傳的實體,因此要一文化能夠流傳下去,物質性的“材料”必不可無。中國人首當妥善保存自己的藝術傳統與風俗民情,先把中華文化的“材料”好好存留。其次,是提升文化的意義,自覺恢復中華文化的“理型”,涵養中華文化的精神,避免使中華文化淪為只具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材料”,如是才能實體中華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我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復興。
(作者: 淩友詩,香港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編輯:海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