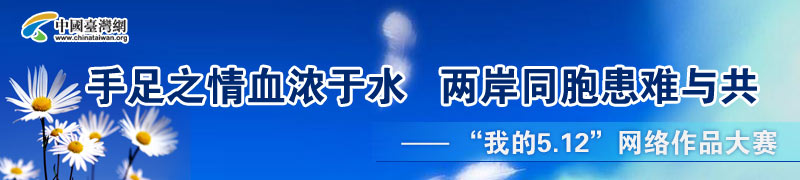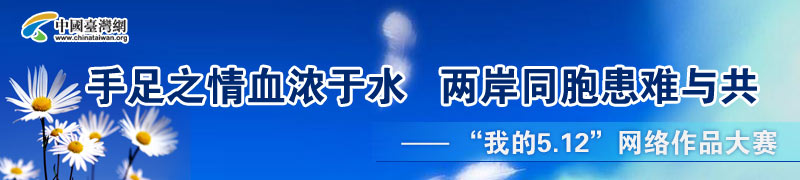——記濰坊援川工作人員
作者 濰坊廣播電視報社記者部 劉鐵飛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際,由濰坊人民廣播電臺、濰坊電視臺、濰坊廣播電視報社記者組成的6人北川報道組近日趕赴北川, 對我市援建北川一年來的工作進行全面深入採訪。
根據省委、省政府統一安排,我市自2008年8月對口支援四川省北川縣桂溪鄉、貫嶺鄉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濰坊援川前方指揮部的25名工作人員,工作環境艱險、生活艱苦,每隔兩個月才能回濰坊休整一次。然而,他們對此毫無怨言,多數工作人員已與這里有了割舍不斷的感情,這片土地,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
孫學明:美麗的貫嶺我的家
對濰坊援川前方指揮部工程建設組副組長孫學明的採訪是在貫嶺鄉的一條小路上,當時正趕上貫嶺小學放學,很多路過的老師與小學生都走過來跟他打招呼,他熱情地回應著,看得出來,這個長著一張標準國字臉、濃眉大眼的山東漢子與當地人已經“混”得很熟了。
孫學明是去年5月22日趕赴地震災區的,他編了個順口溜來形容初到這里時的生活:“礦泉水泡方便面,杠子頭火燒鹹鴨蛋,辣疙瘩鹹菜和大蒜;白天蒸籠蒸,晚上蚊蟲叮;雨天一身泥,晴天曬破皮。”
孫學明說,在援建北川的一年里,工作與生活雖然很苦,但他時時刻刻被災區群眾的堅強樂觀和純樸善良感動著。因為這種感動,他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總想著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質量去完成重建工程。
也因為這種感動,孫學明主動聯係資助了5個孩子,還認了玉龍村上小學三年級的吳春萍做“幹女兒”,放寒假時,他還特地讓女兒從家里過來看望幹妹妹。
鄉親們感動著孫學明,孫學明也感動著鄉親們。在孫學明的日記本里,記者發現了他在2008年11月12日寫下的這樣一段話:“前段時間走遍了桂溪鄉、貫嶺鄉90%的村,高山上的群眾家里特別貧困,不忍心給老鄉增添麻煩,吃老鄉的飯,就隨便吃點野果、蔬菜充饑,有一次,到復興村二組,餓了撿野板栗吃,渴了拔路邊的蘿卜吃……”
臨走前,孫學明塞給記者一張紙條,上面是他剛剛寫好的一首詩《美麗的貫嶺我的家》:美麗的貫嶺我的家,羌族兄弟我愛他,大難面前挺脊梁,山崩地裂人不垮。美麗的貫嶺我的家,羌山羌寨我愛它,靈山秀水汲精力,傾注熱血裝扮它……
陳百波:唱支羌歌解鄉愁
“清涼涼的咂酒唉,伊呀勒索勒哦,咿呀勒索勒呀……”
前往貫嶺鄉採訪的路上,濰坊援川前方指揮部工作人員陳百波在停車休息間隙,站在大山前唱起了這支《咂酒歌》,歌聲從他的嗓子里吼出來,有一股蒼涼的味道。
陳百波說,在援川工作中,與身體的勞累比起來,精神上的痛苦可能更強烈。來援川的隊員,大都成家立業,上有年邁的雙親,下有幼小的孩子。思念親人,想念孩子,成了每個援川人員說不出的痛。
“說不想家,那是假的。”陳百波說,在這點上,援川隊員表現出了很高的素質和覺悟,援川隊員大約每兩個月探家一次,在這期間,沒有一個提出提前探家要求的。“有個隊員家里孩子病了,他想念孩子,背著人偷偷地哭,但表面卻裝得沒事似的。”
“援川生活比較單調,除了工作,娛樂活動幾乎沒有。為了排遣寂寞,也為了分散隊員想家的注意力,指揮部想方設法組織活動,讓隊員在集體活動中沒時間想家。”他說,每周一、四早上集體跑操、每周三、五晚上集體學習,一起聚餐,一起動手包餃子,甚至一起學跳羌族的鍋莊舞。
為了與當地人建立更好的關係,今年春節前,陳百波帶著筆墨,到桂溪鄉沙窩村為建房群眾寫下一副副春聯。由于經常與當地羌族人接觸,他慢慢了解了羌族文化,並且喜歡上羌族歌曲,一有閒暇時間,他便會唱上一段,在歌聲中,釋放自己想家的情緒。
“現在依然想家,但一回濰坊呆上兩天,便馬上挂念起這邊的工作與同事,想盡趕快回來。”陳百波說,這似乎是一種矛盾心理,但從這種矛盾心理中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與這片土地有了割舍不斷的感情,這里已變成他的第二故鄉了。
王波明:這里有我的幹爹和幹娘
王波明是援川前方指揮部里比較特殊的一位,他的父親是第一批援川工作者,父親剛走,他又來到援川第一線,可謂父子兩代共援川。
王波明的父親王連溪是濰坊三建集團董事長,汶川大地震後他擔任寒亭區援建突擊隊隊長,負責桂溪鄉過渡安置小區——永利村板房搭建工作。在援建工作中,他與當地人結下深厚友誼,並認永利村村民梅秀光的女兒梅傑為“幹女兒”,圓滿完成各項援建任務後,他把幹女兒梅傑及她的妹妹接到濰坊,如今梅傑在我市一家酒店工作,她的妹妹在寒亭一所中學讀書。
在父親返回濰坊後,王波明來到援川前方指揮部工作,負責工地安全等事項。工作之余,他經常代替父親到梅傑家去看望她的父母,並把他倆當成自己的幹爹和幹娘。王波明告訴記者,梅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全塌了,現住在永利村板房區,為維持生活,幹爹幹娘在鎮上租房子開了一家米線飯館。
“幹娘每次一見到我都噓寒問暖,並與我聊梅傑姐妹倆在濰坊的生活情況。”王波明說,他一有時間便會去找幹爹幹娘聊天,有時也幫他們解決一些生活中的難題。“有這樣的一家親戚來回走動挺好,這份親情使生活不再寂寞。”
袁軻:最年輕的堅守者
在濰坊援川前線指揮部擔任駕駛員的袁軻是最早到來的一批援建者,也是最年輕的一位,今年剛27歲。
去年汶川大地震剛發生時,袁軻便有了來支援北川建設的念頭, 5月20日他自願報名參加了援川工作。
“剛開始時父母與女朋友都不同意我來,因為這里的環境的確很艱險。”袁軻說道。
說起環境的艱險,袁軻舉了兩個例子:有一次下暴雨,當時擔任濰坊市抗震救災援川建設前線指揮的崔學選正在綿陽開會,他擔心指揮部駐地的安全,堅持要回去看一下。袁軻駕車在雨中濕滑的山路上艱難前行,前方不斷有小石塊從山上滾下來。
忽然,他看到前方滾下的一塊大石頭砸向一位騎摩托車的中年人,人與摩托車一起翻下深溝。袁軻停車聯係了急救部門,沒過一會兒,醫護人趕到現場。
“道路這麼危險,還往不往里開了?”這時袁軻的心里打起鼓來。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崔學選安慰他說:“放心吧,我們來做好事,會有好運氣的。”袁軻膽戰心驚地繼續往前開,最終順利到達駐地。
還有一次,他拉著幾位援川工作人員到沙窩村查看村民生活情況,當時剛下過雨,汽車行駛到離村子不遠的一個上坡時,突然有大片泥沙伴著石塊滾落下來。袁軻緊急剎車。“好險!車頭在石塊滑落前方剎住了。”
望著剛剛落下的一塊塊直徑近一米的巨石,袁軻出了一身冷汗。
如今,袁軻已在當地練出了過硬的山路駕駛技術,援川一年來,他安全駕駛三百多天。現在他依然每天早出晚歸,忙的時候,一天駕駛時間長達十一、二個小時。
“每天出車回來,累得倒頭就睡,哪有時間想家啊。”袁軻說,他現在每周與家中父母及女朋友通一兩次電話,有時忙了便只能發個短信。“現在家里人與女朋友都很支持我,女友想與我今年先領結婚登記證。”
問他啥時結婚,他靦腆地笑笑說:“等援川工作結束吧。”
採訪後記
前方指揮部的每一名援川幹部身上都有一串感人的故事。桑福嶺長期忍受著腰椎間盤突出的痛苦折磨,黃永健腳踝傷疼時時發生,孫佔博經常忍受胃病的折磨……前方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上有老、下有小,肩負著做父親、做兒子、做丈夫的多重責任,來到北川家庭顧不上,長期忍受親情離別之苦。但是,他們憑著對工作的熱忱、對事業的執著,舍小家、顧大家,忘我工作,晝夜奮戰,堅持奮鬥在災區一線。
在未來的兩年里,我市援川人員將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援建加援助,增強滿意度”的“雙援”新思路,帶著感情來援建,充滿激情去援助。早日把桂溪鄉、貫嶺鄉、北川新城建設好,早日讓受災群眾過上幸福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