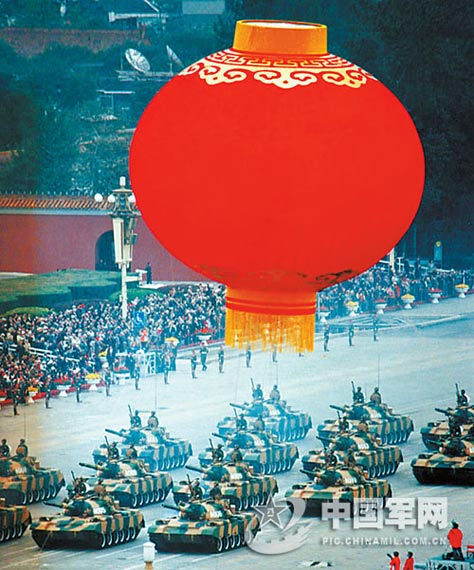
攝影師鏡頭里的閱兵式充滿詩意和美感。
題 記
無論顯赫或卑微,每個人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用生命的痕跡記憶著過去,哪怕是一橫一豎,一撇一捺。與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那些用手中鏡頭記錄一段段難忘歷史的軍旅攝影師們,在尊重歷史的原汁原味時,也融入了更多個性化的情感和行為方式——他們創造了歷史,卻渾然不知,他們定格了歷史,卻不以為然。他們只知道,作為軍人,命令下來的那一刻,就是抱起手中的“武器”,衝啊!
張世鴻:用彩色膠片拍攝閱兵第一人
他板直的坐姿讓人感到一位老軍人的風骨。即便身體已被歲月的滄桑浸染,但透過他的話語,仍能體味到軍旅攝影家不變的愛國情懷。眼前的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曾在戰火硝煙的前線穿梭拍攝,將後勤保障戰線的大批攝影資料送到後方。他還接受過秘密任務,進入某地連續工作了701天……
都說他的鏡頭彌足珍貴,記錄下了新中國成立來無數關鍵的歷史時刻。他就是張世鴻。
與他面對面相坐時,周圍的人都親切稱他張總。因為他是八一廠許多電影和紀錄片的總攝影。
他今年70多歲了,但身子骨出奇的硬朗。他拍著胸脯笑著說:“這是常年扛著笨重的攝影機,走南闖北鍛煉出來的軍人體魄。”直到現在,張世鴻還是不服老,想著跟騰安慶(1999年《世紀大閱兵》總導演)比拍黑白片,看誰拍出來的鏡頭最棒。
追憶是從1956年10月1日的閱兵式開始的。張世鴻說:“八一廠當時正在拍一部關于蘇加諾訪華的片子,沒想到蘇加諾也去參加檢閱了,我們就跟到閱兵式上去拍。完全是一種巧合。”
“那年的閱兵下著雨,元帥們都換上新授銜的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部隊。方隊從雨中走過,那齊刷刷的隊形,那官兵身上散發出的霧氣,特別美,也特別令人神往。”張世鴻回憶起50多年前的場景,就好像剛剛發生過。
“我出發前就想好了,這一神聖時刻要用彩色膠片拍,但是陰天,又有一種擔心:用彩色膠片拍下雨的場面,會不會砸鍋?因為那個年代誰也沒用過彩色膠片,心里沒底。當時現場還有其他電影廠的攝制組,他們保守,不敢冒險,就用黑白膠片拍。我天生膽大,決定破天荒使用彩色膠片。我知道這是一次性拍攝,方隊走過去了,再想彌補是不可能的。結果拍出來一對比,我興奮地叫了起來。黑白片拍得雨天灰蒙蒙的,幾乎看不清楚,而彩色膠片拍出來的,層次感很強。搞攝影的都知道,頭一次用彩色膠片拍大場面,最難掌握的是曝光時間,否則就會一片模糊。沒想到,稀里糊涂成功了。”
更讓張世鴻想不到的是,10年後,美國出現了“新彩色攝影”理論,一個叫做威廉·埃格爾斯頓的攝影師提出要使用彩色膠片拍攝“嚴肅題材”,而另外一位薩麗·奧克萊爾的攝影師則認為,彩色膠片在上世紀60年代依舊沒有成熟,他的理由是,彩色膠片反映的主題色彩過于誇張,很難把握,弄不好會拙劣地表現世界,無法真正用鏡頭構建世界。在一片爭論聲中,“新彩色攝影”理論誕生了,並被歸結為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彩色攝影的新時代。
然而,讓美國人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國八一廠的攝影師們,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將鏡頭對準了聲勢浩大的閱兵式,並將彩色攝影這“難以把握”的主題色彩神奇般地把握住了——在蒙蒙雨中如實並嚴肅地營造出了一個絕佳的視覺語言和影像效果。如果美國人得知的話,恐怕就不會武斷地說是美國攝影師開創了新彩色攝影的時代。
1984年,小有名氣的張世鴻,被八一廠作為總攝影,負責拍攝當年《國慶閱兵》紀錄片。那時,張世鴻拍攝技術和經驗首屈一指,廠領導之所以把這麼重的擔子壓給他,看中的是他的業務。其實,從表象看,張世鴻長得很年輕,怎麼看都不像個領導。但張世鴻是一個有激情、有責任心的人,拍攝準備期間,他提出一個主導思想:今天的歷史是留給後人看的,面對大閱兵這樣的重大而又嚴肅的歷史題材,真實紀錄當時的情形就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後人負責。因此,他和攝制組同仁討論再三,最終決定用傳統手法紀錄閱兵全過程。
他清晰地記得:“閱兵那天,鄧小平主席的講話剛結束,全場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隨之,出現了一點間隙性的平靜。伴隨一聲‘分列式開始’的口令,令人矚目的受閱部隊開始通過天安門——排山倒海的口號聲和鏗鏘有力的腳步聲如同大地上滾過的驚雷。由于當時器材落後、笨重,沒有同期錄音的條件,所以現場聲音都要後期加工。我要求每個攝影師憑印象記住閱兵全過程的所有細節,以便事後注入現場聲音效果時,嚴絲合縫。果然,片子制作出來一看,比現場更逼真,更有氣勢。一位我多年的老戰友跟我說:‘我就喜歡聽你配的這些聲音,真切動人。’”張世鴻說到這里,臉上明顯露出了自豪感。他的妻子拍著他的肩膀笑著說:“你這些事有什麼值得吹的啊?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了一名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但從她說話的表情中,能感覺出作為軍人妻子的驕傲和自豪。
張世鴻笑了,指著他的妻子對筆者說:“她也不容易,我年輕的時候因為工作需要到處跑,她在家里一個人帶孩子。抗美援越的時候,我出去了兩年,中間沒通信,她都撐過來了。現在年輕人不會理解,兩年不通電話不寫一封信是什麼感覺。”他妻子笑著說:“嫁給搞新聞紀錄片的女人不都這樣!”看著互相打趣的老兩口,筆者感受到了他們之間的溫馨和彼此的信任。也只有經歷過磨難的感情,才能如此沉靜和深邃。
王建國:拍攝《世紀大閱兵》是場戰鬥
1999年10月1日,是祖國50歲華誕,恰逢世紀大閱兵。全國人民對這一天都充滿了期待。
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使億萬觀眾當天就收看到了閱兵實況。可是,也因為電視轉播的局限,許多鏡頭無法兼顧。正是八一廠拍攝的大型紀錄片《世紀大閱兵》,彌補了這一缺憾。
《世紀大閱兵》的總攝影師王建國回憶:“那真是如同一場戰鬥,每個攝影師都是士兵,時刻經受著考驗。那年遇到了騰安慶這樣一個好導演是我們攝影人的福氣,他很有魄力,很能張羅,既有親和力,又有聰明的頭腦和領導魅力。當時廠里的要求只有一句話:拍攝一部讓觀眾喜歡且震撼的紀錄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想而知有多難。為尋找《世紀大閱兵》的創新點,騰導絞盡腦汁地先從紀錄片的片頭開始尋求變化。他事先領著攝影師們跑遍了北京城,拍下了許多展示國威軍威的精彩鏡頭:故宮的大門在威武的鑼鼓聲中打開,寓意國門打開,中國人走向世界。還有黃河的壺口瀑布、清華的納米技術、國防大學的上將和中將們在現代化電教室的沙盤前作業、碩士生和博士生從清華大學的大門一擁而出……盡管有些鏡頭最終在審查時被拿掉了,但片頭還是一改過去從天安門拉開的固定模式。”
對于拍攝中遇到的艱難,王建國更是記憶猶新。他說:“最揪心的是下雨。沒想到,9月30日那天真就下起了雨,讓所有在場的人心焦不安。據說氣象專家們早在一年前就開始對50周年慶典活動當日的天氣進行過預測和分析,並準備在必要時人工驅雲,但到了那天就是雨下個不停,誰也說不好何時才能多雲散去見晴天。制片部門買來了雨衣、雨布,攝影師們帶上了‘快片’(一種適宜陰雨天使用的膠片),準備打持久戰。冷雨伴著秋的寒意陣陣襲來,冰涼沁骨。攝影組在金水橋等多處設了器材集散點,器材箱下墊一層雨布,上面再蓋一層,看守的幾個人則穿著雨衣打著傘在雨夜里站著。這一夜,天安門廣場的各個方向,都有《世紀大閱兵》攝影組人員在徹夜值班看守機器。”
八一電影制片廠是一支部隊,命令一下,所有人就必須到位,每位同志必須保證完成任務。導演部門事先繪制了完整精確的機位圖、統籌圖,寫出了每一臺攝影機的分鏡頭,所有內容都同時有3至6臺攝影機做不同景別、不同角度的拍攝。除完成各自的分鏡頭外,攝影師還根據現場變化,不失時機地抓拍一些精彩內容。王建國說:“按閱兵指揮部的要求,我們的機位由58個一次次遞減到最後的29個,機位圖也反復畫了許多張,每一張都很細致,不厭其煩地標出攝影機和小汽車等實物圖像。當機位圖拿到閱兵指揮部時,審查者都豎起拇指誇獎:‘到底是八一廠,真是正規、嚴格!’騰安慶對全廠的攝影師了如指掌,他按照每個人的特長進行了分工,力保每個鏡頭都盡善盡美。”
“負責拍攝中央領導人講話的王保權,在閱兵式即將開始前試機時,電瓶突然短路起火,一股白煙騰起,瞬間燒焦的膠皮味彌漫了全場。安保人員怕出危險,索性把他給趕了下來。好在我們事先有預案,下面有專人接應,趕緊給他換個備用電瓶,又給安保人員做了一番工作,才再一次進入現場。當時嚇出我一身冷汗,軍委主席的講話差點拍不到了。王保權拍完之後,整個人癱在地上,也不知道是累的還是嚇的。”王建國今天說起這些,仍然心有余悸。
最難辦的是一個人跟拍,常常手忙腳亂。王建國記得,當時王迎軍扛著攝影機,從紀念碑後面出來,一路小跑跟拍到升旗的地方時,一卷膠片就用完了,他只好跑到軍樂團指揮平臺旁,將事先隱藏好的另一臺機器扛起來繼續拍。膠片拍完了,再回來給兩個機子同時換片。多次反復,閱兵式快結束時,他已累得端不動機器了,只能趴在地上拍。
王總對他指揮的兵的表現,異常滿意,他說:“大家都很賣力啊!董亞春拍攝閱兵村時,一會兒趴在地上,一會兒爬上高臺,只為拍出好鏡頭,顧不得自己的形象。站在歷史博物館頂上的桑華,臨場發揮的很出色,他用長鏡頭把海軍在進入東華表之前的7步走,拍得相當漂亮,加之,海軍服裝是白褲子藍上衣,飄帶隨風而動,像波浪滾滾而來。我安排兩臺攝影機拍攝江主席檢閱部隊時的一舉一動。給我們開紅旗轎車的司機叫辛亦農,他的技術很好,為保持車距,他一邊要隨時盯著駛在前面的中央電視臺攝影車,一邊還要在反光鏡中瞄著江主席的檢閱車。他完全專注于自己手中的方向盤,以至于他像是根本沒聽到檢閱部隊驚天動地的吼聲。”
《世紀大閱兵》紀錄片完成了,王建國長長地舒了口氣。坐在剪片室的平臺前,看著一個個精彩的鏡頭,他心里樂開了花。他說:“這部紀錄片拍出了軍人的剛強和氣勢,也拍出了人民武裝力量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一片忠誠。不論哪一支方隊,不論你橫看、豎看、斜看,每一個排面都整齊如一人;每一條頭線、胸線、臂線、腳線都筆直如刀割。我從沒見過這麼整齊的畫面!”
如今,《世紀大閱兵》已被視為經典,凡天安門城樓開放時,都在不間斷地播放。上到省部級領導,下至青少年學生,無不因它而慷慨激昂。為此,王建國謙虛地說“我也是一個兵,和閱兵村的官兵們一樣,自受領了任務,就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最佳狀態投入進去。如果說,戰士的美來自烈日下黝黑的皮膚、雙腿上沉重的沙袋,那麼,攝影師的美就在于對偉大祖國的忠誠,對這支軍隊的崇敬,對攝影事業的熱愛。”
石少升:與共和國同生同慶
石少升是軍事片部的領導,工作很忙。他膚色黝黑,帶有北方漢子憨厚的嗓音。他曾參加過1984年和1999年兩次國慶閱兵的拍攝,今年還將參加60周年閱兵典禮的拍攝。
石少升1949年出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清楚地記得,1984年的10月1日正好與他35歲的生日重合,那一年他被頭一次選中參與國慶閱兵的拍攝。他的位置就在東華表紅牆下。當時他屬于八一廠的二線攝影師。
“閱兵前,鄧小平主席要視察閱兵部隊,選擇看望裝甲兵官兵。當時廠里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又興奮又害怕,擔心出岔子。進入現場那天,我被安排的位置果然不好,裝甲車的炮塔剛好擋住了我的鏡頭,怎樣拍效果都不理想。我靈機一動,就大膽爬到了裝甲車的頂部。這在當時是違規的。等安保人員發現驅趕我時,我已抓拍好了。事後我受到了表揚,我抓拍的這組鏡頭被導演用上了,而且是原封不動。導演給我的評價是,作為攝影師,他總會在臨場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發揮,而這些發揮讓整組鏡頭都顯得靈性十足。”
石少升最難忘的還是參加1999年國慶閱兵,他被組織指派去拍攝航空兵部隊的演練。他說:“剛去很興奮,拍攝空中編隊,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沒想到合練開始後,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他們合練的機會也就那麼兩三次,合練的機場卻有遠有近,你剛拍了這里的起飛,得趕緊乘車趕到另一個機場,再拍那里的,來回奔波穿梭。有些鏡頭我想去拍攝,但是空軍配合不了,只能另辟蹊徑自己想辦法彌補。當時制片主任也很著急,跟我反復商量怎麼拍。我給廠里表態,不管難度有多高,一定不折不扣完成任務。”
“經過努力,我終于獲得了到空中拍攝的機會。那天,為保證拍攝質量,我被安排坐在飛機前駕駛的位置,駕駛員坐在我後面。大家上飛機前都知道,這樣做危險性極大,如果飛機高空停車,那麼在我後面的駕駛員就束手無策,我倆只能棄機。但我覺得幹什麼事都有風險,為了拍攝好鏡頭,也只能硬著頭皮這樣幹了。”石少升今天回憶起來,依舊不寒而栗。
“飛機降落的時候,也同樣危險。駕駛員坐在後駕駛的位置上有視覺差,準確度不夠,就會出現偏離。如果偏離過大,很有可能會撞到塔臺。當時我坐在飛機上沒有感覺到什麼,但走下飛機,工作人員告訴我原委後,我只覺得脊梁一陣發涼。”但石少升是一位真性情的男人,在他眼里,軍旅攝影師就是一個高風險職業,當祖國需要你的時候,你必須有一種特別的勇氣和膽識。
“1999年,空軍有了蘇-27,導演告訴我,事先必須搶拍一些鏡頭預備著,等到閱兵式那天,如果出現意外,就都晚了。為此,我決定在跑道上對著飛機正面拍攝。當時,飛行方隊不幹,認為這樣太危險。我苦苦哀求,才勉強答應。拍攝那天,可真叫危險,我的鏡頭稍微正一點,你就會覺得飛機起飛時直奔你而來,那巨大的衝擊力,雖隔著二三十米,依然覺得就在眼前。所以說,攝影師為了一個好的鏡頭,有時是敢冒生命危險的。”石少升這樣感嘆道。
蘇-27升空時超過80分貝的聲波,讓石少升的耳朵留下了後遺症——聽力受損,耳鳴伴著輕度的耳聾,近距離跟人說話常常聽不太清楚。
“有件事我一直很後悔。有一年我去拍演習,看到山洞里的炮彈打出去時,巨大的聲音衝擊波將戰士頭頂上的帽子都掀掉了。那天,有個小戰士在抬炸藥,我正好捕捉到了他,他發現我在拍他,手一滑,炸藥掉到了地上。當時很危險,他應該馬上離開,沒想到他彎腰想去撿,炸藥爆炸了,他被送進了醫院。現在我一想起來就自責,如果不是我當時拍他,他就不會想著去撿炸藥。作為攝影師,有時看到別人受苦卻無法幫助,這種心里的痛苦是很難言語的。”石少升這番話,體現了所有攝影師的良知所在。
在採訪現場,筆者感到了每個攝影師的時尚,無論是張世鴻那身藍色的牛仔休閒衫、筆直的咖啡色西褲,還是王建國那頂帥氣的黑色遮陽帽,都令人忍俊不禁。他們是自信的,他們如同航海的舵手,從容不迫地把重達幾十公斤的攝影機當作武器,去記錄世間的滄桑,去表達自己的情感。他們灑脫自信,他們堅毅剛強。(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相關鏈接
1、1953年,《人民心一條》獲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二等獎
2、1955年,《在帕米爾高原上》獲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二等獎
3、1963年,《偉大的戰士——雷鋒》獲總政治部優秀紀錄片獎
4、1977年,《硬骨頭六連戰旗紅》獲優秀軍事教育片獎
5、1981年,《鋼鐵長城》獲中國電影金雞紀錄片特別獎、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
6、1984年,《國慶閱兵》獲解放軍文藝獎、文化部優秀紀錄片獎
7、1992年,《天界》獲廣電部最佳新聞紀錄片獎、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新聞紀錄片獎
8、1995年,《較量——抗美援朝戰爭實錄》獲“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中國電影金雞紀錄片特別獎、廣電部優秀紀錄片獎
9、1998年,《揮師三江》獲中國電影金雞評委會特別獎、“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
10、1999年,《東方巨響》獲中國電影金雞最佳新聞紀錄片獎、廣電部優秀紀錄片獎
11、1999年,《世紀大閱兵》獲解放軍文藝獎、“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廣電部優秀影片特別獎
12、2005年,《東方神舟》獲“華表獎”優秀紀錄片獎提名、“金雞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
13、2006年,《帕米爾之戀》獲第17屆意大利“軍隊與人民”國際軍事電影節最高獎“共和國總統獎”
14、2007年,《不能忘卻的長徵》獲“華表獎”優秀紀錄片獎提名、“金雞獎”最佳紀錄片獎提名
15、2008年,《為了生命》獲第19屆“軍隊與人民”國際軍事電影節社會影響類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