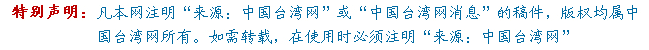藝術家吳冠中橫站于東西方夾縫間

2010年6月26日,著名畫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吳冠中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吳冠中是中國美術界最後一位學貫中西的泰鬥級藝術家,在世時便曾于中國美術館、香港藝術館、大英博物館、巴黎塞紐齊博物館、美國底特律博物館等國內外一流美術館舉辦過多次個展;榮獲法國文化部最高藝術勳位,並被選為法蘭西學院藝術院院士;其作品在國際拍賣活動中不斷刷新紀錄,按總成交額計算,謹以微小差距居于齊白石後的第二位,隨著畫家的去世,超過齊白石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
1919年出生于江蘇省宜興北渠村的一個普通農家。一方面是像那個時代眾多青年一樣,懷抱工業救國的理想,同時也不無對未來出路的現實考慮,初中畢業後,考上了浙江大學代辦的省立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讀完一年,按彼時的規定,參加大學預科生的暑期集中軍訓,吳冠中與國立杭州藝專預科學生、後成為旅法著名畫家的朱德群編在同一連隊、同一班,倆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一個周末,吳冠中隨朱德群參觀藝專,看到前所未見的圖畫和雕塑,心靈受到巨大震撼,當即決定棄工從藝:“十七歲的我拜倒在她的腳下,一頭撲向這神異的美之宇宙,完全忘記自己是一個農家窮孩子,為了日後謀生好不容易考進了浙大高工的電機科。”
林風眠奉蔡元培之旨創辦並執掌的杭州國立藝專(即後來的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的前身),與北平國立藝專(即中央美術學院前身)並立為民國時代南北兩大藝術教育重鎮,師資雄厚,人才濟濟,教學中西合璧,吳冠中在這里受到了包括印象派在內的西方現代藝術的啟蒙。抗戰爆發後,杭州校區被毀,學校被迫輾轉遷移,從長沙到沅陵,從貴陽而昆明。躲警報之余,臨摹《南畫大成》、畫人體模特,藝術並未完全成為戰爭的犧牲。藝專畢業後,在重慶大學建築係任助教,同時自修法文,為赴法學藝做準備。
1946年暑期,教育部在全國設九大考區,公開選拔戰後第一批留學生,其中只有兩個留法繪畫名額,競爭空前激烈,吳冠中幸而考中。翌年夏,赴法留學,入國立巴黎高級美術學校,師從蘇弗爾皮教授(J. M. Souverbie)。這位巴黎畫派的重要成員,把藝術分為兩路:小路藝術娛人,大路藝術撼人;其看對象或作品亦分兩類:美(Besu)與漂亮(Joli)。如果他說學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貶詞,是警惕。老師對藝術的“酷評”標準,顯然也影響了後來吳冠中對藝術作品的評價尺度。
戰後的巴黎藝壇,自由之風吹拂,本來就傾向現代派的吳冠中如魚得水。來法國前,吳冠中原本是不打算回國的,“因為國內搞美術沒出路,美術界的當權人物觀點又極保守,視西方現代藝術為洪水猛獸”。但一方面是思鄉心切(彼時已結婚生子,夫人朱碧琴與長子在江蘇老家),感覺梁園雖好,卻非久居之地;另一方面,梵高的一句話,讓畫家陷入深深的思索:“你是麥子,你的位置在麥田里,種到故鄉的土里去,將于此生根發芽,別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因此,當蘇弗爾皮教授預備為弟子延長公費時,吳冠中向老師吐露了內心的想法,得到了後者的理解與支持。1950年暑期,吳冠中回到新中國,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
吳冠中得以任教中美,係老同學董希文的推薦。院長徐悲鴻一味主張現實主義,與林風眠兼容的,甚至有些偏愛西方現代藝術的學術觀點水火不容,故舊杭州藝專係的學生也與徐係的學生觀念相悖。新教師上任後,徐悲鴻作為校長出面請客,但“除必不可少的禮貌話外,徐先生和我沒有共同語言,雖然我們是宜興同鄉,彼此鄉音均較重”。吳冠中從巴黎帶回三鐵箱畫冊,每次上課讓學生們傳看一兩本,結合名作,解讀藝術觀念和源流,效果甚好。令他驚訝的是,學生們居然從未聽說過波提切利、莫迪里阿尼、塞尚、梵高等西方名家。而當有同學問老師有無列賓的畫冊時,則輪到吳冠中感到汗顏:不僅沒畫冊,甚至從未聽說過列賓的名字。課後問董希文,董說是俄羅斯十九世紀大畫家,是今日國內最推崇的現實主義大師。吳冠中回家後查法文美術史,好容易發現了列賓的名字,但只有寥寥幾行文字介紹。
吳冠中在中美教書的第二年,趕上文藝整風運動,徐悲鴻在全校大會上講話:“自然主義是懶漢,應該打到;而形式主義是惡棍,必須消滅。”吳冠中感到非常孤立。很快,便接到調令,去清華大學建築係任教。在清華,住在原先朱自清等名教授住過的北院六號,吳冠中感到很舒心。建築設計要講究形式,也不怕被批為“形式主義”。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所謂“雙百方針”。9月,由北京師范大學美術係、音樂係為基礎組建的北京藝術師范學院(後改為北京藝術學院)成立,吳冠中應邀去該院工作,任副教授兼油畫教研室主任,就此“歸隊”美術界,直至八年後藝術學院建制取消,並入中央工藝美院(1999年工藝美院又並入清華,成為清華美術學院)。
吳冠中從青年時代起熱愛魯迅,對魯迅的閱讀與理解貫穿了一生。他在1999年為《文匯報》“筆會”專欄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魯迅先生說過因腹背受敵,必須橫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橫站在中、西之間,古、今之間,但居然橫站了五十年……”但正因為費力而決絕地保持著“橫站”的遺世獨立姿態,藝術家打通了西畫與國畫、美術(或曰“純藝術”,Fine Art)與工藝之間的藩籬,成為在諸多領域中獨樹一幟的格外醒目的存在,而不在乎是否會被“藝術主流”邊緣化。
早在杭州藝專預科時期,學生不分科,統屬繪畫科,以西畫為主,兼習國畫。因為國畫的老師是潘天壽,備受學生崇敬。吳冠中也受此影響,一度轉入國畫係。“但我那感情似野馬的青年時期又未能安分于水墨淡雅之鄉,我狂熱地追求色彩,終于又改回了西畫係,從此夢寐向往的是塞尚、高更、馬蒂斯、畢加索……”“我一向著眼于中、西方審美之共性。我愛傳統繪畫之美,並曾大量臨摹,深切地愛過,仍愛著。我也真正愛西方繪畫之美,東也愛,西也愛,愛不專一,實緣真情,非水性楊花也。”因為在藝術家的眼里,“達芬奇的素描山水與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卷》頗為相似;波提切利的作品突出線造型、平面感、衣帶飄搖感,大異于拉斐爾、提香等渾圓豐厚的立體氛圍,獨具東方情致。鬱特利羅的作品中可感到冷冷清清淒淒切切及‘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中國實情,加之他表現手法中強調平面分割的對照及線之效果,我最早喜愛其作品也許緣于吻合了我的中國品味,而中國傳統的或民間的繪畫中也同樣可發現西方所探索的因素。”正是基于如此獨特的視角,吳冠中才能操觚水粉、油彩、彩墨、水墨、版畫等幾乎所有的繪畫媒體,不懈地致力于油畫民族化和中國畫創新的探索,在土土洋洋與洋洋土土、抽象與變形之間東奔西突,左右逢源。所以很難用一個籠統的概念來定義其藝術。如非如此的話,也許只能勉強用“造型藝術”來概而括之。
但雖說如此,在國中現狀的藝術體制下,吳冠中的的確確始終不代表“主流”,甚至可以說,在不同的時期,是被“邊緣化”的對象。1999年文化部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吳冠中藝術展”,佔了三個大廳。不僅規模空前,而且以文化部的名義為一個在世畫家舉辦個展尚屬首例。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國家對藝術家價值的肯定。吳冠中似乎也頗為感動,從展品中遴選了十幅巨作捐給國家。但展覽一結束,便有人策劃了三篇批判文章,在《文藝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濃烈的意識形態味道,恍如文革大字報再現,一掃個展的余韻。
不僅如此,單就作為畫家資質而言,國內美術界對吳冠中也有臧否兩論。譬如,說吳的書法“不行”等等。傳統書畫界歷來有所謂“詩、書、畫一體”說,當代藝壇也不乏這方面的“通人”或自詡“通人”者。對此,吳冠中並不避諱,而是坦言自己的不足:“三十年代我隨潘天壽學畫,潘老師說:‘有天分,下功夫,學畫二十年可見成就,書法則須三十年。’潘老師的話我總是相信的,但當時對書法與繪畫的比較則尚無體會,只根據他的指導臨顏真卿、黃道周,及魏碑、石鼓文。然而,對書法的興趣遠不如繪畫,對畫的優劣感到一目了然,自以為很懂了,可是對書法卻缺乏獨立審評的能力……其後我專攻西洋畫,連水墨工具都拋棄了,更談不上再練書法。”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縱然書法上的缺憾是一個事實,但畫壇宗師的泰鬥地位仍然難以撼動。
晚年,吳冠中除勤奮創作外,還以敢言著稱。畫家以切身之體驗,痛陳體制弊端,語不驚人死不休,不僅諸如“一百個齊白石比不上一個魯迅”、“筆墨等于零”、“藝術活動跟妓院差不多”的發言令許多官員和同行不舒服,所謂“以獎代養”、“撤銷美協、畫院”等建言也觸及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作為解決方案,未必具有現實可操作性。但毋庸諱言,藝術家的激憤之言,很大程度上是對束縛、乃至閹割了藝術家創作力的藝術體制之患的不幸言中。
雖然直至1979年,吳冠中才擁有了一間11平方米的畫室,可藝術家一生勤奮創作,著述(畫作和著作)等身。除了給孩子留下幾幅紀念性畫作外,絕大多數都捐給了社會。其中相當多的作品,作為經濟泡沫的一部分,還處于“充氣”狀態,價格日益飆升,但已與作者無關。作者輕掩畫卷,已走進歷史。
知我罪我,是耶非耶,升值貶值,官司榮辱,都不重要了。用藝術家自己的話說:“時代的變遷,個人的經歷和年齡鑄造了今天的我,無從後悔,無可自得,自己無法對自己作出客觀的評價,倒是可作為別人的借鑒,蓑草乃新苗之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