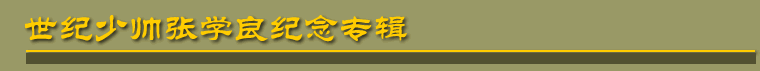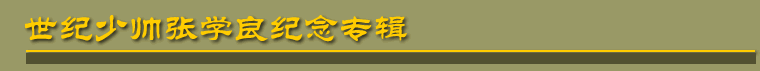|
 |
|
| |
| |
| |
張學良先生走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尤其是他的人格。張學良的人格,主要表現在他光明磊落、無私無畏、淡泊榮利等幾個方面,其最大特點就是一切以國家民族為重。
一、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
張學良的政治生命面對的是國家內訌外侮社會激烈動蕩的時代。基于對現實的深切體驗和悉心思考,他深為國家民族的現狀及未來擔憂。首先他憂內訌外侮國勢阽危。張學良19歲就參加戰爭,經歷了剿匪之役、直奉戰爭、豫南大戰和中原大戰,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和給人民造成的災難,曾慨嘆:吾國不幸,兵禍頻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為什麼?打仗為戰勝,雙方不知犧牲了多少有用的青年。並呼吁:早息內爭,倘再延長,勢必致民命滅絕,國運淪亡,補救無方。那麼他又為什麼參加內戰呢?我們認為除了他統一禦侮的思想動因外,還有他無可奈何的客觀因素。正如趙一荻所說:“他之參加內戰,不是名,不是利,也不是為了爭地盤。他開始是為了遵行父親的意願,後來是服從中央的命令,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本人對此也深有同感:我自22歲領兵打仗,一直打內戰,皆為不得已之行動。不論其為戰勝或失敗,均感覺萬分痛苦。張學良還從國際的視角來憂國家。他曾預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並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將在這一鬥爭形勢下處于受包圍受夾攻的危機地位,在未來自有被蹂躪被犧牲的絕大可能。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蠶食中國之時,他就心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針對中國的土地任人割裂,中國的主權任人剝奪,中國的組織任人破壞的現實,他大聲疾呼:整個中國,眼看就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國難嚴重的程度,實在是無以復加了!整個民族的生命,眼看就要完了,舉國上下若不能一致奮起,那真是國亡無日了。
其次他憂消極、自私、內爭的國民性。國是由民組成的,對國家的憂患最終必然深化為對國民的憂患。他曾在檢討國難嚴重之由來時指出,構成中國國難日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人受了傳統的消極心理的影響。這種心理可用幾句成語代表,如“明哲保身”“休說國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這種心理,實足以斷送民族生命而有余!這種心理,可以使我們中國人的鬥志消磨凈盡,寧束手待斃,決不拼命鬥爭!試打開我國近百年史看看,我們何嘗堅決地徹底地同我們的敵人鬥爭過!他認為國人多數還具有只顧個人不顧團體的狹隘自私心,遇著一樁事情如果于己沒利,無論怎樣容易,怎樣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反之,即使再難甚至妨害旁人,也要去做,結果導致利益衝突,大家受害,以致民族整個文化不能進展,事事落伍。中國之所以弄到這個地步,都是中上層社會的罪惡!無論是軍人、政客、學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他指出:“中國人每基于傳統的劣根性,忽于團體的群力的對外競爭,而徒事對內做無謂的紛爭,這也可以說是整個民族的最大弱點。”張學良如此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一方面是社會現實在他心靈上的投影;另一方面也是他反思歷史,放眼世界所獲得的一種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警覺;同時也是他繼承古代知識分子憂患傳統的必然結果。
二、堅定的民族自尊自信
張學良盡管有著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但他只把這當作探索真理、開拓未來的動力,對于列強決沒有半點媚眼奴骨,相反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自信和堅貞的民族氣節。
1921年秋,血氣方剛的張學良,應邀赴日觀秋操,親眼看到日本以四島彈丸之地稱霸東南亞,感慨萬千,尤其日本人展示的軍事實力,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他對身旁的張作相說:“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日本人總是想以勢壓人,反而促使我反抗。”當日本人問他有何觀感時,他回答道:“你們日本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不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也能做到;請君拭目以待。”歸國後,張學良向父親提議,對奉軍進行全面整治,整頓軍紀,選拔軍官,加強訓練,決心趕超日本。主政東北後,張學良總是自覺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首先想從他始洗刷不平等條約的恥辱。他說:“中日兩國歷來所締結之各種條約,均屬不平等條約,故約滿後,凡與日本或其他各國締結新約,自當以雙方合議為條件,而努力達此平等目的”,“本人對俄意見,以後凡條約以內允我之權利,應當強硬主張,不能放棄”。其次他堅決抵制帝國主義幹涉中國的內政。1928年,日本政府得知張學良要改弦易幟歸順南京政府,便派林權助等人趁張學良為父治喪之機,三番五次地警告他,倘若東三省蔑視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強固之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即謂幹涉內政亦所不辭。張學良卻義正詞嚴地回敬道:“蓋余為中國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國為本位,余之所以願與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當林權助以長輩口吻勸他時,他又以和日本天皇是同庚回絕道,所能奉答者,只此而已。後來日本政府又派張學良的顧問肥源賢二說服張學良出任“滿洲國皇帝”,也同樣遭到拒絕。1935年,日本蠻橫提出罷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字孝侯)的要求,蔣介石就此致電張學良,徵求同意。張學良電復:“中國的封疆大吏,不應以外人的意見為轉移,如此例一開,國將不國,此事所關孝侯的事小,而對于國家主權攸關的事大。”然而蔣裝作沒有得到復電的樣子,屈從了日方的無理要求。張學良對國家的主權向來十分重視。早在繼位不久,他就明確表示:在我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給日本,有損主權之事決不退讓。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決不是張學良“反蘇反共的前奏曲”,而是他發起的一次收回中東鐵路主權的愛國行動。“九一八事變”中,盡管他判斷失誤執行了蔣的不抵抗政策,但他卻全力支持了東北軍、抗日義勇軍和各界愛國民眾,對日軍進行了殊死搏鬥。另外他還對賣國者深惡痛絕。當得知自己的堂弟當了漢姦後,他立即下令捕殺。被軟禁後,他聽說東北軍將領鮑文樾參加了汪精衛的偽政府時氣憤地說:“真是令人可恨!這真是東北人的恥辱,更是東北軍人的恥辱。”他總是告誡人們:“我是誰,我應該無時無地不在想著我是中國人,既然披了中國人的皮,就萬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國人。”
張學良盡管憂國憂民,但並沒有對這個“破敗的門庭”心灰意冷,而是信心百倍。他一直認為:我們中國人天賦的聰明,不但不比外國人低反而優于他們,我們中國的復興條件是絕對夠的!對此,我們要有一種最大的信心!我們打開歷史看看,我們的祖先曾給我們留下了偉大的遺產,只要我們肯努力,在不久的將來,一定還會有偉大的事業出現!並預見,抗日的最後勝利終會屬于我們中華民族。如果說張學良的民族憂患意識,是他探索真理、開拓未來的動力,那麼他的這種堅定的民族自尊自信,就是他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奮力拼搏的力量源泉。
三、高度的民族責任感
張學良不僅在憂國憂民的同時,沒有半點的氣餒,而且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前途自覺聯係起來,既有責任感又身體力行,達到了國與己,思與行的高度統一。
張學良始終把拯救國難,復興民族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在今天的我們,個人的前途一點也沒有了,有之,只是整個民族的前途。”他一直在思考,人類全是圓顱方趾,為什麼我們要受人家的欺淩?我們同是國家,同是民族,為什麼我們在國際間受這樣的壓迫?即使在被“管束”後,他也曾有個龐大的讀書計劃,先研究明史,後研究清史,最後研究民國史,目的就是想弄清楚近百年來老是受外國欺淩的原因。他常說:“我們的苦痛都是我們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債,我們今後萬勿再給子孫留下去。”我們憑著什麼去抵抗這一群逼在門前的債主,憑的就是從自己做起,從即刻做起。他教育他的部下:不可自暴自棄,以為謀國有人即可袖手旁觀,而存偷安茍活之心,須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民一日不安全,國家一日不穩固,我們就應當引為奇恥大辱;要時刻牢記,這個國家是誰的?我應如何完成對于國家所負的責任?要有中國不會亡,何以不亡,有我在;中國能復興,何以復興,有我在的舍我其誰的精神。
張學良之所以有如此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就在于他對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認為個人在國家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說:你是中國四萬萬人中的一個單位,這猶如細胞對于一個生物全體的組織,每個單位都能表現出他的力量,則整個國家當然可以強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團中表現出作用,則必然于整個國家中減少了一份生力。個人在國家里面誠極渺小,但沒有一個一個渺小的個人也就沒有國家了。所以個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個人不應當輕視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國家的問題高于個人的問題。自然,沒有自己焉能有國家,但是沒有國家又焉能有自己?如國家問題不解決,則個人問題永無解決之日,正如一株樹不能根深,焉能葉茂?我們應當視國家問題高于個人問題。總之,在他看來,個人是國家的單位,國家是個人的集體,所以每個人對于國家的復興都有很大的責任。這說明他的高度的民族責任感是以深刻的理性認識為堅實基礎的。
四、大公無我的犧牲精神
張學良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堅定的民族自尊自信和高度的民族責任感的最高體現則是他大公無我的犧牲精神。
張學良認為,要想改造社會,推動時代,那必須具有做一個無名英雄的決心與勇氣。在你打算獻身于有裨國家社會的某種事業時,首先應問問自己:我生于國家這樣危急的時候,能不能艱苦卓絕地無條件地犧牲?如果從內心得到一個絕對肯定的答案“能”,那麼你才能有決心,有膽量,而不會自私無所希求。他對他的部下說過:“張學良早有決心,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決不幹!反之,又絕不惜犧牲!假如,把我的頭割下來,國家便能強盛,民族便能復興,那我張學良絕無所惜!”後來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正是他對這一誓言的最好踐履。他在對總部全體職員訓詞中講道: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當事變發動後未找到蔣介石之時,張學良對東北軍的將領激動地說:“若找不到委員長,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為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這充分說明,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完全出于愛國救國赤誠和自我犧牲精神。尤其他陪蔣返寧的壯舉,更使他的偉大人格光彩照人,對此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被扣後,為穩定局勢,顧全大局,保住和平解決的成果,他一再寫信囑咐東北軍將領,凡有利于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一切以國家民族為重,勿以學良個人為念。半個多世紀後,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負責,我送蔣先生回南京,我是請罪,並且簡單地說,後事我都預備了,我是準備處死刑的,我不這樣做,內戰恐怕會更擴大,我對犧牲自己毫無顧慮。”有人問他有沒有想到會軟禁50年,假如時間倒流,還會如此做嗎?他說,“我還是那麼做,槍斃了我都不在乎。”由此可見,張學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完全把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真正達到了無私無畏的境地!
張學良如此大公無我的犧牲精神,首先出于他對國家的至誠。他認為,要想拯救國家必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誠意,要把自己無條件地貢獻于社會和國家。一個人賦性和言行最難得的莫過于一個誠字,而誠心的表示,又莫過于以死相報。他能向蔣屢諫直陳,敢于“將天捅個漏子”逼蔣抗日,又能義無返顧地送蔣返寧,正是出于他這種對國家對民族的至誠。他總是把錢財權利看得最不重要,曾對前來看他的張治中說過:“我覺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沒什麼,只要國家不打內戰,能統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我張學良當年把東北軍帶到青天白日旗下圖的就是這個,從沒有想到個人的榮華富貴。”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曾在張學良91壽辰的致辭中讚揚道:“無盡寬恕,忍怨含痛的美德舉世罕見。”其次出于他做人的良心,張學良將良心看得很重,特別強調做人要講誠,做事要憑良心。他認為,該做的便一定去做,成敗得失,非所應計。縱使做得沒有結果,受人非難,然清夜自思,尚不致受良心的責備,得失毀譽不妨看空一點,不要著了“相”要完全打破私的意念,對于得失利害,方能毫不計較,這才可以絕對忠實于一己對于國家民族所負的任務,甚或以身殉之而無所畏難。“事變”爆發後,他一再申明:“我們決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若就人而論,我們的舉動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而論,試問全國四萬萬五千萬民眾重,還是蔣委員長一時之身體自由重?”由此表明,為國家為民族,對事不對人,不求見諒于人,但求無愧于心是張學良為人處事的良心準則,也是他大公無我勇于犧牲的心理動因,更是他達到的一種人格升華境界。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