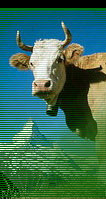上海西南郊的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已經連續兩年在上海市特色億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05年,該村實現凈利潤18035萬元,上繳國家稅收8502萬元,可支配收入達3.3億元。
這個村的3757名村民,每人平均年分配收入3.5萬元,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之外,還實現了人人有股份,從村民變成股民。
戴著“中國十大名村”、“華東最大市場村”等眾多桂冠,在全國十大傑出“村官”的駕馭下,九星村12年間已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演繹著新農村運動中上海版“村強民富”的時代樣板。
“三有”新農村
除了富裕之外,“九星模式”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九星所代表的村民股權改制,在上海市郊今後的新農村建設中,將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上海市農委負責人這樣評價九星。
“我對新農村的理解是‘三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股份。有了股份,農民才有長期的實惠。實際上,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兩種分配方式同時存在於我們的企業內,再加上養老金、醫療保險金以及失業保險金的保障,九星的村民可説是‘三保險’。”“上海第一村”九星村“掌門人”吳恩福説。
2005年底,九星完成了對其20%資産的股份制改革試點,原牛頭管理區股改完成後成立了九星物流公司,全體村民3757人變成股民,成為資本市場的主人。
九星此次股改採用“現進現出”的方法,對資産按現行價格評估,再由大家出錢認購,得來的錢再分給老百姓。改制的資産中並不包括公益性資産,而僅限定在經營性資産的範圍。公益性資産約佔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40%的份額,如路、橋梁、衛生室、幼兒園等,這部分資産用於保障村民福利,一部分用以服務經濟發展。
“這樣可以讓大家記牢手中的股份是自己出錢買來的,在思想上更珍惜;有了這次成功的改制試點之後,剩下的80%資産在今年年末也可以完成。”吳恩福向記者透露。
村強民富的樣板
吳恩福介紹説,今年村裏為已經遷居城鎮的643個農戶每人發放物業補貼1200元,比去年提高25%。
物業補貼只是村民幸福生活的一個側面,除此之外,全村先後投資修建23條總長20多公里的道路,建造8座橋梁,50多座標準化公廁;全村700多名60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發放養老金448元;村民子女上大學、讀碩士,每人每年分別補貼5000元與8000元;去年實行集體資産切塊改制,平均每個村民量化兌現1.8萬元……
“去年光是旅遊費,每人就發了8000元。”吳恩福紅光滿面地説,“其他過年過節發的慰勞費和物資,就更不用提了。”
九星村有3座“善事堂”,村裏人在這裡辦喜事是免費的。
“今年,還要增加3個部分的福利。”吳恩福表示,將為830位老人漲退休養老金,從448元漲至548元;如果村民不使用村裏提供的場所舉辦婚喪喜事儀式,將可以得到2000元補貼;著手為市場內招收的臨時工繳納“三金”,為所有勞動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
據悉,九星村的市場將變成上海市區最具現代化程度的物流中心。“這將意味著,九星村民將擁有衣食富足,精神充實,生活完整的社會主義小康生活。”吳恩福高興地對記者説,“村與民有四種關係:村窮民富、村強民富、村窮民窮、村強民窮。那麼,九星村已經達到了‘村強民富’的理想狀態。”
村辦市場的成功
從九星村委會那幢器宇不凡的大樓看出去,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和住宅。
臨街的門店前,停靠著各色汽車,有轎車、也有許多小卡車,更有蹬著三輪車四處搬運貨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車子的牌照顯示它們來自全國各地:冀、晉、蒙、遼、吉、黑、滬、蘇、豫……看到這些,會使人感覺置身一個全國大市場。
如果不是背靠上海大市場,九星會成就今天的模樣?
吳恩福反問:“上海城郊結合部的村子多的是,又為什麼是九星發展得好呢?!”
村級經濟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滬郊農村發展村級經濟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像近郊的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梅隴鎮華一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向外擴展的需求,為村級經濟找到新‘增長點’。”閔行區領導接受採訪時説。
九星通過興辦大型綜合性商品批發交易市場成就了今天。10年間,九星從一個全村勞動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貧困村莊一躍而成為上海市356個億元村之首。到目前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涌現出4000多位創業老闆。 一個時代的人物
在村民的眼裏,九星和吳恩福是連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吳恩福是土生土長的九星人,是個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臉上總挂著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辦市場揚名上海灘之後,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但吳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66年,吳恩福初中畢業便回家務農,種田、養豬、種棉花、搞副業,他都幹過。有一陣子,搞糧棉高産的試驗,吳恩福種的11畝棉花地畝産皮棉213斤(當時平均一般畝産難超100斤),成為鄉里挂紅花的模範,還前往各個村交流經驗。
1994年,幹過5年生産隊副隊長、5年生産隊長、10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臨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勞動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辦的幾個聯營廠都經營困難,村子欠債1780萬元,而村子的集體總資産不過2100萬元,負債率高達84.8%。
土地是農村人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九星曾擁有4500多畝土地,但隨著上海外環線建設以及房地産開發,九星村先後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畝土地。如何利用好這珍貴的1600畝土地,成為全村村民致富脫貧的重要出路。
艱難的尋找
“九星村辦農業,行不通!”吳恩福首先否定了這個出路,“産出低,一畝田地年收入不過千元,九星每人平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談何致富。況且,發達的交通已經拉近了農村與城市的距離,處於上海郊區並且業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勞動力成本上升,同全國千千萬萬勞動力價格低廉的農村相比,九星發展農業已經毫無優勢可言。”
“搞工業?當時全國眾多農村選擇工業化、搞鄉鎮企業的路子,但鄉鎮企業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臨辦工業帶來的風險,既缺少資金投入,也無專業人才。”
而當時的國情是,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尚且發展困頓,多以為國企做配件生産的村辦企業的發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産開發?看似有大筆資金進帳,但實質是‘賣地’,是對未來資源的一種擠佔,如果把收入分攤到未來幾十年中去,所得不過是極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將無以依託。”看多了“失地即失業”的吳恩福拒絕重蹈其他村的覆轍。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個村屬商業市場。當時的政策並不允許村級辦市場。上級領導部門給了九星足夠多創新的空間,在九星所屬的七寶鎮工商所向閔行區工商所作了彙報後,上級部門給出“試一試”的結論,由此,九星頂住壓力開始了村辦市場的探索。
1998年8月至11月短短的3個月時間,九星村辦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幹貨、膠合板、農副産品五大批發市場。目前,九星村建成了佔地面積106萬平方米、建築面積60萬平方米、營業用房1萬多間、分設22個專業區域的上海規模最大的市場,吸引了全國各地5400多戶商家、18000余名經商務工人員,被譽為華東地區最大的市場村和申城市場的航母。
這幾年,九星村的經濟效益始終保持著高位增長的勢頭:2005年,實現農方收益3.3億多元,凈利潤1.8億多元,上繳國家稅收8502萬元,勞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經連續兩年在上海市特色億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授予了上海郊區12個村“中國特色村”稱號,九星村以其村辦市場特色,榮獲這一殊榮。除了特色經濟村之外,此次評選還歸類出“農業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等四大類特色類型村莊。
九星模式不可複製?
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經濟發力,城市大發展、大建設催生了房地産熱潮,帶動建築行業的火爆。正因為九星起步時趕上上海對建築裝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構建建築裝潢材料市場起步。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産開發業的火爆,是不是就沒有如今的九星?
從前九星是遠郊區,手中的土地沒人看得上;同時,1600畝的土地足夠建市場,因為市場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來的。隨著上海城市化的推進,九星成為近郊而後是城郊,這個時候再想拿這塊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拆遷費,這也是九星市場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還在於那套“種磚頭”理論,其核心是“滾動發展模式”,九星10年裏建造了60多萬平方米的市場,由小到大,這期間,沒有一分欠債。在建倉房沒有錢付工程款時,採取的辦法是給工程隊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後再回收。以後的改造思路也是從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場的時機非常微妙,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在改革開放程度較高的時期,九星進入市場,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質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辦市場的路子。
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環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條“村辦市場”的新路子。(張俊才 張倩)
來源:華南新聞
編輯: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