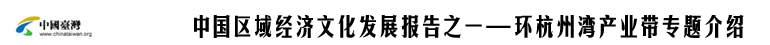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受省體改辦、科技廳、上市辦和浙江天堂硅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邀請,來杭州出席天堂硅谷創業投資論壇春季峰會。期間,吳敬璉就我省建設“天堂硅谷”等論題接受記者採訪。
“天堂硅谷”希望很大
記者:目前從已披露的情況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合肥、西安、武漢等有十幾個城市先後提出要創建“硅谷”,您認為浙江的‘天堂硅谷’能在競爭中勝出嗎?”
吳敬璉:硅谷具有什麼樣的本質特徵?怎麼樣才算硅谷?對于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回答。目前中外研究硅谷的學者較多認同的一種觀點是:硅谷是創業企業的棲息地。
“棲息地”是一個生物學名詞,它是指動植物棲身之地。動植物之所以在此棲息,是因為環境適宜,而環境則包括了復雜的因素,比如氣溫、濕度、植被等。
根據斯坦福大學研究硅谷的專家羅文分析,作為企業棲息地的硅谷,其特殊優勢可以概括為八條:有利的遊戲規則、很高的知識密集度、員工的高素質和高流動性、鼓勵冒險和寬容失敗的氛圍、開放的經營環境、與工業界密切結合的研究型大學、高質量的生活、專業化的商業基礎設施(包括金融、律師、會計師、獵頭公司、市場營銷,以及租賃公司、設備制造商、零售商等)。
任何一個想要使自己成為“硅谷”的地方,都必須考慮創業環境。完全照搬硅谷是不適當的,但是基本原則是普遍適用的。根據我國當前情況,企業棲息地起碼應當具備四個基本要素:高素質專業(技術和商業)人才的集聚、廣闊寬松的創業空間、良好的法治環境、充裕的資金供應。
浙江中小企業多,創新精神強,同時有浙江大學等院校的科研人才和民營企業眾多的經營人才,許多民營企業也集聚了大量資本,並且正在為這些資本尋找出路,這些都是創建硅谷所需要的。綜觀浙江經濟、文化素質,建成“天堂硅谷”希望很大。最後能否成功,還有許多因素。
政府應著力于制度建設
記者:您經常說,現在的政府為高新區、硅谷做的事情太多,太細。有些事情企業、風險投資家能夠辦,政府就應該交給他們去辦。據我們所知,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對于建設‘天堂硅谷’有著極大熱情,您認為,這些熱情應該用在哪里呢?
吳敬璉:這不是說政府就沒事情幹了,事實上政府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並不反對在硅谷創辦初期,由政府進行必要的投入,特別是辦孵化器之類。國外有不少贏利機構來辦孵化器,我們的力量不夠,集中政府力量辦,是很好的做法。但進一步說,政府應該自覺地運用社會資源,讓他們競爭,給創業企業提供更專業化的服務。能夠由市場去做的事情,就由市場去做。
政府要辦的事情還很多,特別是制度創新的問題,這是硅谷成長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多次強調“制度重于技術”。有的地方認為,硅谷光有人才就行了,其實不然。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個。光有比較優勢和人才並不一定成功,人才、資金等是必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因素是制度,是企業創新的大環境。政府不要再直接操辦一些具體事情,而應該為高新技術企業創造創新、創業的條件,提供更好環境。在建立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充分發揮創業者積極性、創造性的制度方面,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高校不應直接辦企業
記者:您剛才提到浙江有學校資源優勢,也提到了建設硅谷不是光有人才就行了,那麼應該如何發揮學校資源?
吳敬璉:硅谷里大多是高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種“人本經濟”,在各種生產要素中,人力資本(智力資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大量專業人才集聚是發展高技術產業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臺灣信息產業的成果與新竹科技園附近有一大批重量級的高等院校,與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貢獻是密不可分的。有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培養了大批技術和經營人才,這些人才是建設硅谷所必需的。
但要明確的是,這只是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智力資源存在于人們的頭腦里,既不能國有化,也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調撥的。怎樣使這些高智力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得以在高技術創業活動中有效地發揮,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目前有兩個不妥當的傾向:一個是院校自己辦企業,一個是政府為院校直接提供風險資金。
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辦企業是一種中國特有的現象。硅谷60%到70%的企業都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或教師創辦的,但是斯坦福大學沒有一個校辦企業。現代社會分工很細,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業,是很難管得好的。而在校辦、院辦、所辦這類特殊國有企業中,發明家和企業家缺乏切身利益聯係,也使企業難以有效開展經營。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從它們所辦的企業中拿到有限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鶩和資源分散,削弱了科研和教學的本業。因此,這種讓院校自行創收的做法免不了會影響基礎科研和教學水平。國內一位大通信設備制造商告訴我,科研教學的削弱已經導致我國一些院校畢業生的綜合素質下降和研究院所科學技術儲備的不足,以致于高級軟件要拿到印度去做。這種現象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而政府直接提供風險資金給院校同樣有著失當之處。基礎理論研究和共用技術開發都是具有外部性的活動,屬于市場失靈的范疇,是需要政府採取適當行動加以彌補的。例如,美國和日本政府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中提供支持、對重大高新技術開發的支持,都對高技術產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政府不應該直接提供風險資金給院校,特別是為院校的某個項目,如此一來,很容易導致計劃經濟那一套,扶持一個項目,卻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環境。政府可以為基礎理論研究和共用技術開發提供資金,同時可以推進院校的改制,將高等院校的資源動員起來,使他們本身能夠在內部整體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