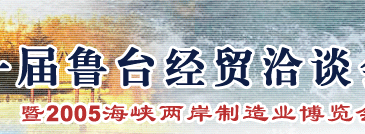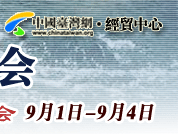今山東曲阜是古代魯國的都城。曲阜距臨淄不遠,兩座城市中間隔著泰山,臨淄在泰山東北,曲阜在泰山西南。齊、魯往往並稱,臨淄和曲阜同為今山東大地上最負盛名的兩座古都。
曲阜也和臨淄一樣坐落在中國的東部,是國之東土。在曲阜所在地,最早有上古部落大庭氏建都,遺址在後來周代魯國的都城內,魯國在其遺址上作庫,稱為大庭氏之庫,是當時曲阜城中一個登高望遠的地方。大庭氏之後在曲阜建都的有少,他是黃帝之子。少昊以後有奄人在這里建都,奄人是嬴姓,東夷的一支,炎帝族的後代,在商代時臣屬于商朝,因此又稱為商奄。後來周人徵服了奄,而在這里封立了自己的宗國魯國。不過許多後來在魯國立功立名的人,都是炎帝族、東夷、殷商的後裔。在曲阜城中有“淹中”、“奄里”,就是周代奄國遺民聚居之地。魯大夫季氏的家臣陽虎,禦姓,為商人的後代。孔子也是商人的後代,是宋國始封之君微子啟的裔孫。
魯國是周初最重要的封國之一,它地域不廣,國力不強,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守文備禮。魯國的始封國君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即位後,以姜尚為師,周公旦為輔。周武王攻進朝歌,周公旦手持大鉞,召公奭手持小鉞,左右夾衛武王。周武王死後,兒子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天子之政,營建東都雒邑,討平三監及東夷之亂。在周初開國功臣中,周公旦是最重要的一位宗室大臣。所以周朝在分封魯國時,分給魯國大輅車、大旌旂,分給古代的寶物“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給六族殷商遺民。除此以外還特別分給了專掌祝、宗、卜、史的官吏和官司禮器。魯國和列國不同,它擁有天子的禮樂,春秋各國大夫學禮問禮,如果不是去都城洛陽,就要去魯國曲阜。據傳周公旦在父親文王在世時,就是一位孝子,篤厚仁愛,異于群子。周公旦死後,周王室為了嘉獎他的美德,特別準許魯國為周文王立廟,每年祭祀他,這是其他諸侯國所不允許的。因此從一開始立國起,魯國就有了守文備禮的特點。魯國的這一特點後來經過各代君臣以及炎帝、東夷、殷商遺民的共同努力,于是更為光大。
魯都曲阜是一個保存比較完好的古都,它最初的城垣至今還有不少地段殘存于地面,最高的地方有10米,整個城市的基址輪廓也比較清楚。城市分為內城和外郭城兩層,外廓城共有十二座城門,有東、西、南、北門和鹿門、萊門、雩門、稷門、子駒門、石門等等。魯莊公的兒子襄仲一族居住在東門,人們就把他稱為東門襄仲,又稱他的兒子子家為東門子家。還有一個大夫歸父居住在石門,人們就稱他為石門歸父。當時公族、大夫們都是聚族而居,以一族為一個整體,一般都是每一族中出一個大夫。佔卜好了居室以後,世代相承,很少變動,所以就可以用所居住的地方相稱。魯國這種情況在當時習俗中是個典型。漢代所說“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的情況也與此相類似,是社會長久安定的一個標志。
《莊子》中所說孔子與盜跖的故事,也發生在東門。柳下季是孔子的朋友,是個賢人,而他的弟弟盜跖卻是個大盜,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孔子想去勸說盜跖,柳下季阻止,孔不聽。盜陽一聽是孔子前來,大怒,“目如明星,發上指冠”,“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孔子講仁義,盜跖反駁,大叫:“丘前來!”對孔子講了歷來名君名臣都並不仁義的事例,說仁義壓制人性,人的一生,“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應該聽從人們順從自己的心願。孔子見了盜跖,大為震驚,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回到曲阜東門外,正遇見柳下跖。柳下跖一見孔子的樣子就知道他去見弟弟了,說:“盜跖違逆你的心意了吧?”孔子說:“我這是無病自醫。我摸虎頭,撫虎須,幾乎不免于虎口!”
石門是外郭城的東南門。《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天在石門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進城。守門的人問他:“從哪兒來?”子路說:“從孔家來。”守門的人就說:“就是那明知做不到卻一定要去做的人吧!”說明當時孔子推行自己的主張已經很難。
曲阜的中部、東部較高,北部、西部較低,在北垣西門有一處水池。這座城門就叫爭門。
南門是曲阜的正門,原來叫稷門,魯僖公時重新修建,使它加高加大,因而改稱高門,又叫雩門。南北朝時人們見到它的基址,猶在地八丈余高。雩門外隔著洙水有一處雩臺。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四個弟子坐在一起,問他們各有什麼願望。子路願意去治理一個千乘之國,使它強大,人人有勇。冉求願意去治理一個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國,使它富足,人人明禮。公西赤說願意學習,如果可以就做個掌管禮儀的小臣。曾點說:“我的志向與三人不同。我願意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新做好的時候,和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少年人一起,在沂水邊洗完了澡,到雩臺上去吹風,一路唱歌走回來。”孔子長嘆一聲說:“我和曾點一樣。”雩臺在南北朝時還有三丈高,是當時一處著名的風景點。
曲阜的外郭城“方九里”、“旁三門”,很合周朝的規定。它的內城公宮在南,宗廟在北,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很符合周朝的規定,可見魯國確實是個守禮之邦。
公宮是國君居處的地方,正殿叫路寢,此外還有高寢、東宮、西宮、楚宮等。楚宮是魯襄公出訪楚國,喜愛楚國的宮殿回來後倣建的。曲阜在漢初是漢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劉余的都城,魯恭王在這里修建了一座靈光殿,除正殿外,還有雙闕、浴池、釣臺等建築,多為石建,據說在建築群中穿行,“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最著名的是靈光殿中的壁畫,描繪了許多神話鬼怪,斑駁浪漫,怪異之極,可惜後來毀于大火。靈光殿的基址就在後來的孔廟一帶,南北朝時其池臺基岸遺址尚整。王延壽有一篇《魯靈光殿賦》描述了這處傑出的建築。史書上說魯恭王好治宮室苑囿,晚年好音樂,但口吃難言,不好文辭。初建靈光殿時,他為了擴大宮殿面積,挖壞了孔子的舊宅,聽到宅中有彈奏鐘磐琴瑟的聲音,就沒敢再挖。在挖壞的牆壁夾層中,出土了用古文字書寫的儒家經傳。宗廟位于公宮的南面,偏東。周朝的制度,每一位君主死後都要立一座宗廟,按時祭祀,每座宗廟按昭、穆的次序排列。周文王的廟稱為周廟,周公旦的廟稱為大廟。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實際上的始封國君,他的廟稱為大室或世室。這座廟最為重要,為不毀之廟。此外各代君主的廟都稱為“宮”。煬宮是魯煬公的廟,武宮是魯武公的廟,桓宮是魯桓的廟,莊宮是魯莊公的廟,閔宮是魯閔公的廟。還有宣宮、僖宮、襄宮等等。魯國經常在各宗廟中舉行各種禮儀。
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廟宇,位于公宮南面,偏西。曲阜中兩社,一為周社,祭祀周人的土地神;一為毫社,祭祀殷人的土地神。毫社在西,代表居住在城西的眾多殷商遺民。周社在東,代表城東的周人。祭祀毫社的禮儀與周社很不相同,雜有東夷的風俗,還使用過人祭,當時曾引起周人的很大爭議。
在公宮之南、兩社之間的就是魯國的朝廷,實際上它是公宮的外廷,與內殿相連。朝廷的大門稱為雉門,門外有兩闕,名為“象魏”。象、魏都是高大的意思。朝廷有新的法令頒布下來,就是挂在象魏上,公之于眾,人人都要遵守。象魏反映了法律的平等,是周人一項良好的制度。
在外郭城東南有一個大路口,名為“五父之衢”,是人們活動的中心場所。魯國人盟誓時,往往要在這里舉行詛咒的儀式,詛咒將來違背盟誓的人。陽虎就曾召集魯定公和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大夫在周社盟誓,召集國中平民在毫社中盟誓,然後在五父之衢詛咒,這樣來決定一國的大事。城內的民居分布在四周,其中也有很多高大建築,如季孫氏的居室在東南部,季武子在院中修建了一座高臺,人稱季武子臺,到南北朝時,雖已崩塌,猶高數丈。孔子的故居名叫“闕里”位于殷人聚居的西南部,當時是一處普通的街巷。孔子的弟子顏回曾經居住過的“陋巷”當然更是一條普通街巷,陋巷本非原名,因其簡陋故名。據傳顏回身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別人不堪其憂,而顏回不改其樂。現在的孔廟、大成殿都是很久以後在唐宋時開始修建又在明清予以重建的,孔府、孔林也在後來逐漸興盛。這些與孔子有關的建築精美壯觀,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周廟、大廟。
在曲阜城中有一條彎曲隆起的地帶,長七八里,古稱“曲阜”,曲阜城由此得名。大庭氏庫和季武子臺都在這條隆起的地帶上,現在這條地帶在曲阜城外的東北部。曲阜城中有很多園林,把城市點綴得清新壯麗。其中有社圓、鹿圃、蒲圃、蛇淵囿等。據傳孔子曾經在杏壇講學,在矍相圃校射。現在坐落在城北的孔林方園七八里,更是一處蔥鬱的園林。在曲阜城外,洙水被引來與護城河相通,自北向南繞城一周。古代洙水源出今新泰縣東北,至泗水縣與泗水合流,至曲阜東北又分流,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流過曲阜,至濟寧又重新匯合。因為孔子曾經在洙、泗之間聚徒講學,後代就用“洙泗”代稱魯國的文化和孔學一派。
孔子雖是殷人的後代,但他向往西周的文化。他最崇敬的人就是周公旦,希望自己能效法周公旦重新在東方建立一個周朝。他思想的核心就是仁愛,讓人們都像父子一樣上慈下孝。他對自己的主張十分自信,說人類不想幸福則已,要想幸福就要仁愛,“誰能出去不走門戶?誰能追求幸福而不走仁愛的道路呢?”可惜他的願望並沒有成為現實。孔子知道要想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先要做官,孔子一生都在謀求做官。但他在魯國只擔任過“委吏”,主管倉庫;又擔任過“司職吏”,主管畜牧。直到晚年才擔任了司空、大司冠、攝相事,可惜只“與聞國政三月”。在其他國家,孔子曾屈尊為齊國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又曾依托衛國大夫顏濁鄒、蘧伯玉和陳國大夫司城貞子。楚昭王曾準備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但沒有實現。孔子在五十六歲時離開魯國,開始了他長達十四年的宦遊,也就是周遊列國。在春秋之際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吃苦的有兩個人,一是晉文公重耳,宦遊了十九年,另一就是孔子。但晉文公成功了,孔子卻沒有成功。他去乎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幹七十二諸侯,結果一無所獲。這才真正是逢時不遇,命途多舛。
孔子到衛國,住了十個月。往陳國,途中被匡人拘困了五天,只好又返回衛國。孔子不得已往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因之不悅。又經過曹國去往宋國,途中受到宋國司馬桓魋的威脅。到鄭國,路上與弟子走散,孔子獨自站在鄭國都城東門下,被鄭人譏為“喪家之犬”。到陳國,陳為晉楚及吳侵伐,不足自保,孔子于是離開陳國。過蒲,為蒲人所阻,于對蒲人盟誓之後,才被放行。至衛國,衛靈公年老而怠于政事,不用孔子。孔子準備西見趙簡子,未果,臨河長嘆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于是往陳,又往蔡。去葉,又返于蔡,途中受到隱者長沮、桀溺二人的批評。楚人伐蔡,孔子轉投楚國,蔡大夫怒,發兵圍孔子于野外。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孔子又為楚國隱者接輿所譏笑,于是返于衛。孔子的弟子多已在衛國做官,唯獨孔子仍無人重用。到將近七十歲時,孔子重返魯國,這一次是因為他的弟子冉求在魯國做執政大夫季康子的家臣,向季康子推薦了孔子。可是到這時,孔子已經老了,他長嘆說:“吾道窮矣!”多年奔波已經耗盡了他的精力,他對做官已經絕望了。
孔子真是生不逢時。他不出名時,弟子們四處稱道為他揚名,可是他的名聲又太大了,各國寧願任用他的弟子,而不敢任用孔子。孔子不得已,就退而著書立說,教授門徒,有弟子三千人,著名的有七十二人。留給後人的印象,好像孔子是個學者、讀書人,其實孔子的本志是要做官、治國。他首先是注重實踐,然後才是讀書治學,只不過人們並沒有給他做官治國的機會。孔子死後,魯哀公去祭奠他,子貢說:“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話說得既委婉,又激憤,同時也道出了孔子一生願被任用的願望。這才是孔子的本來用意。
孔子從小貧苦,社會地位低賤,經濟條件也差。他三歲時喪父,還沒有成年母親也去世了。所以孔子少孤,處境微寒,貧而且賤。孔子晚年,也不富有。這才是孔子的本來面目。
孔子所提倡的仁愛,不能說不美好,但它卻不合時宜。在後代,即使是口上仁愛不絕的人,實際上也從未完全達到孔子的要求。就是在孔子在世時,爭議也已經很大。季孫氏的家臣陽虎是個很有才幹的政治家,他不讀書,見到孔子說:“為仁不富,為富不仁。”意思是要實行仁政國家就不富強,國家要富強就不能實行仁政,把仁愛和富強對立起來。陽虎說的不能說沒有道理,他雖不讀書,目光見識不能說不敏銳。仁愛是人們理想中追求的目標,富強是人們現實中追求的目標,二者都不能說不美好,不正當,但理想和現實二者又往往衝突對立。要十全十美,陽虎辦不到,孔子也沒有辦到,這真是人類的一個大難題。
孔子的價值不在于他解決了什麼大難題,而在于他努力追求人類幸福的精神。他沒有解決什麼具體問題,但他的追求神卻千百年來為歷代傑出人物所效法。後人對孔子有褒有貶。貶他的人則認為社會風氣變壞,都由于孔子的儒教。褒他的人認為要想社會風氣好轉,就該人人尊孔。這兩種態度其實都是錯誤的。貶他的人沒有想到自己要努力,褒他的人則是出于愚昧,並未得孔子的真髓。
孔子死後,他那種甘冒艱辛勇于開拓的剛勁作風以及他善良仁愛的高行大德就很少有人繼承下來。大多數人只是得皮毛,似是而非,借助他的名望,名為儒者,其實庸庸碌碌無所作為,這種人就被稱為“腐儒”、“俗儒”、“小人儒”。再後來,連借助名望的人也少了,戰國之際,最著名的儒者只不過出了兩人,一是齊國的孟子,一是趙國的荀子,都不是魯國人。史書上說,魯國土地狹小,方圓才七百里,最初是以守文備禮聞名天下。但到了戰國時期,人人爭于物利,魯國的禮樂文採堅持不住,終于崩潰。而魯國的人們性情勤儉、吝嗇,世風衰敗以後轉而棄文經商,“好賈趨利,甚于周人。”意即比最擅長經商的洛陽人還厲害!
曲阜的文化本來是以周公旦所開創的禮制文教為特點的,春秋時吳國的賢公子季札到魯國時,就專門觀覽了魯國人排演的禮樂。孔子也多次誇讚周公旦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但是到了後世,孔子的聲望反而大過了周公旦,孔子的廟宇遠遠超過了周公廟,這其實也違背了孔子自己的心。這是曲阜文化的第一個變化。孔子堅持仁愛的理想,終生不移。後世即使不能遵循仁愛,而不得已也要追求物質利益,但也不至于好賈趨利,甚于洛陽。不僅不能守孔子之道,反而適得其反,令人可惜。這是曲阜文化的第二個變化。孔子是一個貧賤的人,他不是不能求來富貴,凡是不合仁愛的事情即使可以富貴他也決不沾取。孔子是一個終生想做官的人,他也不是不能求來高官,凡是不合仁愛的官職即使再高他也決不接受。但是後世表面上尊承孔子的人,為孔子修建了殿堂,為孔子追封了官爵,卻往往有違他仁愛的原則,追求了形式,反而丟棄了本質,反本逐末。這是曲阜文化的第三個變化。曲阜文化經此而一變再變,距離其早先的風范就越來越遠了。而曲阜文化的變化,大概也象徵著中原齊魯地區做為全國的文化中心區的結束。
曲阜從伯禽建都,到魯頃公時楚國滅魯,共持續了二十八世,三十四君,八百余年。(張京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