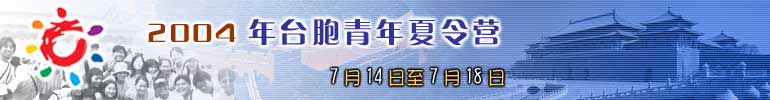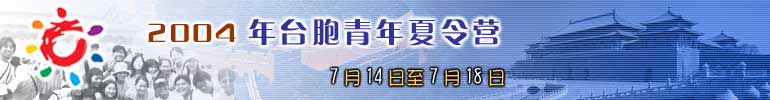注:以下內容摘編自2004年7月17日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在北京大學百年世紀講堂給參加“2004年臺胞青年夏令營”活動的青年臺胞們做題為《我的讀書教學生涯》演講時的內容。
歸來
我的一生就像劃了一個圓,從一個地方開始,去了很遠的地方,現在又回來了。
我回到清華園後創作了一首詩,題為《歸根》:“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峰。深究對稱意,膽識雲霄衝。神州新天換,故園使命重。學子淩雲志,我當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談笑中。耄耋新事業,東籬歸根翁。”
初戀
我初戀的女孩子,她現在已經不在了,叫做張景昭。她是浙江人。那個時候女同學都穿著藍布大褂,只有她穿著紅色西裝,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數學係的學生,我父親是數學係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來,我父親和母親都很喜歡她,我猜想她大概對楊振寧也有好感。可是她對我的影響是這樣的,最開始我發現我到處去打聽,張景昭今天在什麼地方上課,我就請假在她的教室旁邊徘徊,她出來時可以跟她講話。
這樣一兩個月以後,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覺得張景昭對我影響不好。我當時有個很清楚的確定,張景昭來以前,我自己的情緒像很平靜的湖水,張景昭來了以後就變成風暴,整天使我情緒不定。最後我做出決定,這樣下去對我不利,後來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們還是見面的,可是我的情緒上平淡下去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西南聯大我做中學老師的時候,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止是書上的東西,還學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麼?我為什麼能講這句話呢?因為每一個學問里頭都有很具體的東西,可是它有一個精神,這個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來摸去,不能窺全貌。你要達到一個程度,不僅在底下看得清楚,還要知道長高是怎麼一回事情。那個時候我確實是學了很多東西,所以可以有一個看見全面的能力。那時候我對三個人的工作特別欣賞,第一位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比我大43歲,後來我到美國看見過他,還跟他談過,但是我看見他時他年紀已經很大了,所以沒有跟他談過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他比我大20歲,他是英國物理學家,後來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他們三位的物理學我非常喜歡,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復雜的現象,但是很復雜的現象背後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們能把這些定律精神一語道破,這是他們偉大的地方。我很幸運能跟他們有很多的接觸。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里,我因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二十幾位同學經過印度,經過大西洋到了美國,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學。在芝加哥大學不僅看到了艾米教授,還有一位比他年輕的泰勒教授,我看見他的時候,他還不到40歲,已經是很有名的物理學家,後來他變得更有名,後來他被公認為美國氫氣彈之父。原子彈和氫氣彈是20世紀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後,後面不是理的問題,而是工的問題。但是氫氣彈不一樣,會造原子彈,要做氫氣彈還要有竅門,這個竅門在美國是泰勒發現的。
我從泰勒跟艾米那兒學到很多東西,很重要的是我吸收了一點!原來我在中國所學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學的一部分,因為芝加哥大學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國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樣,雖然內容是一樣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在國內所學的物理學是書本上的知識,是已經做好的,就像是菜已經烹調好了,你來吃。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我從泰勒和艾米那兒所學到的不是怎麼去吃這個大餐,是怎麼做這個大餐。所以他們所注意的是一些還沒有被了解的現象,希望把這個現象通過他們的研究可以了解歸納出來規則。在芝加哥大學是從一些還沒有了解的現象里頭提出它的精神,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個學生在研究工作的時候,必須要把這兩個方法融會貫通,這樣才能有大成。
問題集錦
臺胞: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中國國籍的人獲得諾貝爾獎,但是華人有,這是不是和當前中國的研究體制有關?能不能比較一下中國與美國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國有哪些需要改進?
楊振寧:這個問題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這個問題的提法有點不太正確。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獎的時候,我們的護照都是中國的護照,那個時候還沒有入美國籍。很多人問為什麼沒有華人得獎?我的回答是這樣,做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條件,一個條件是要有很聰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平均起來不比別的國家的人差。
第二,要有好的傳統。這一點我想大家也承認,中國的傳統有他的壞處;可是教育下一代,對于年輕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國傳統好的地方。
第三,要有決心。像在清朝末年的時候就沒有決心,那時候還在討論要不要引進西學,今天已經一掃而空,不管是臺灣、香港、大陸,大家都認要一心向科學技術進軍。可是這些加起來還不夠,還需要有經濟的支援。今天比起從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進的國家還是差得很多。
資金增加以後,過一些時候,我相信在臺灣、香港、大陸能夠做出來得諾貝爾獎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會發生的,大家不要太著急。另外有了這個條件以後還要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建立起來的。
臺胞:您能夠取得今天的物理學成就,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楊振寧:我想成功的特別條件是需要機遇,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幸運的。我出生的時候,中國非常貧困,跟我同年級的有千千萬萬的小孩,可是他們多半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我能夠在一個被保護起來的清華園里成長,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幸運。後來到西南聯大,能夠接受最好的大學教育。再後來到美國,能夠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個領域,這個領域叫做高能物理學,是當時剛剛開始的一個領域。
一個年輕人能夠跟一個領域一塊成長,他能夠成功的機會是最大的。我想機遇是第一重要。當然,有了機遇還得要你自己認識到這個機遇的意義以及你自己的努力,當然你過去的經歷跟你的喜愛有關係。我想每一個年輕人,第一,對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麼東西做的好,什麼東西做的不是那麼好。第二,要對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個了解。
這一點上,美國的學生跟中國學生有一個相當大的分別,西方的學生,尤其是美國的學生,興趣廣,東看看、西看看,這樣的好處是把觸角伸得廣,知道哪些領域是自己容易走過去的,哪些領域容易發展。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大陸,從一開始就把學生限制到幾條路上去,讓他很專,這樣有好處,也有很大的壞處,就是觸角伸得不夠廣。在座的同學,我建議在你們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觸角伸得遠一點,能夠看見更多的機會。
提問: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動的事情是什麼?當您站在諾貝爾獎領獎臺上時,您的心情是什麼樣的?當您遇到困難挫折時是怎樣克服的?
楊振寧:我想近年來我最感動的時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眼看著“大英帝國”英國退旗撤兵,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學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當時的感受。我父親那一代的人跟我這一代的人,對于20世紀中國的變化所發生的自我的一個感情,是年輕人不能夠了解的。因為你們不知道在20世紀初,中國是在一個怎樣被欺負、被看不起的狀態。所以我說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觀禮時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豐富,感情衝動是有道理的。
我一生當中遇到的困難很少,我實在是太幸運了。我跟大家講的,我當時很喜歡張景昭,後來由于感情上的波動,那個是我一生比較復雜的一個轉折點。我是幸運兒,我從來沒有找事情,都是事情來找我的,所以沒有失業的困難。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什麼大的挫折。
(責任編輯: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