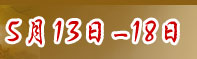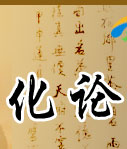�@�̡G�ԥ��K �E��٪��|��ǰ|
�@�@�D�гХߥH�ӡA�v�����c�A�{�b�q�`�H���u�B���@��j�D���۰ϧO�C���O�N�@�Ǧa�ϦӨ��A�o����������������A�Ҧp�Z���D���A�N�O�צX�F���u�B���@��j�D�����иq�M�ǩӪ��@�Ӥ���S�����D���C�Z���D���Φ��p�����檺��]�A�D�n�O�Z���a�B�n�_��ת��~���y��A�[���DzΫH���M�Y�ǬF�v���|�]���A�ϥ��������u�D�V���n�Ǽ��M���@�D��_��I�[�v�T�����n��a�C���E��n�s-�ؤs�D�ЦP�Z���D�Ъ����ʥ�y�A�O�Φ��Z���D�Э��檺���n�]���C
�@�@����չϱq�H��a�z�����סA��Z���P�n-�ؤs�o��j�D�аϪ��D���ǩӰ��@�I���Q�C
�@�@�@
�@�@�j�a�����D�A�n-�ؤs-�Z���O���ۺ�K�p�Y���Ѧ�V�F���T�Ӧa�z�椸�A�S���O�D�Ь}�Ѻ֦a�C�]���D�в�´�M�H��������y�Q���K�Q�A��ϹD���������ǩӶ��z�����C
�@�@���N���Ľs�m�M�L�P�Сn�ۧǻ��A�j�N�D�Ф����|���G�u���B�ӵءB���O�B���@�C�M�N�D�h���Фͻ{���A��ҧǥ|���DZ¤��Ʃ��F�A���j�����Ҷ����u�̤D���O���B�i�D���̤D���@���]�C�� �p�G���ӳo�ؤ�k�Ӱl���D�����y�A�h�Z���D���N�O�ܤ֨䤤�T���۵��X�������C���u�]���O�^�B���@�ۤ������A�ӵج��������ީҳЦѵؤs���A�]�P�Z���D�����K�����W�����Y�C�{�b�Ӱ��@�Ǯz�C
�@�@���߬O�D�Ыe�v������H���C�O�L�A�ϦѤl�m�D�w�g�n�o�H�ǥ@�F�]�O�L�A�����[�P���A�}�ҹD�Юc�[�ؿv�����Y�C�ڡm�n�s���g�O���N�P�u�O�O�n �A���߬O�n���[�P�u�Ĥ@�H�A���y�Ѥ��A���~�n�s�y�ڿ����N�m�D�P���A���ӡA���ܹD�A�Q�P�d�������j�ҡC��ШD����稦���O�A��Ѥl�J���A�k���n���[�A�еۡm�D�w�g�n�C�Ѥl�ɤѥH��A���߿����~��b���[�D�A�ۮѤE�g�A�W�m�����l�n�]��@�D�дL�١m��l�u�g�n�^�C�S�����p�C�ϸv�|�ѧg�A�Q�ʤ�l�u�H�A�R�λ�ѤѥP�h�C
�@�@�m�n�s���g�O���N�P�u�O�O�n���S���өM�u�H���y�A�O��l�u�H���ߪ��q�̡C�q���߭D�A�Q�ӤW�l�n�өM�A�R�U�ΥP���A�ʥN���_���[�A�¹D�h��ۤ��Ѧӥh�C�L�O���[�P�u�ĤG�H�C
�@�@���ߡB���y�G�H�A���X�{�b�Z���P�y���C�m�Z���֦a�`�u���n�M���m�իؤj���өM�s�ӡn �P�˧�G�H�C���Z���P�u�Ĥ@�B�G�H�C�٤��ߤ_���p�|���ѧg����A�k�ϪZ���A���T�Ѫ��۾����U�۪��B�۫ǡA�ߤ��ҩ~�A�j���ɧɡB�ɮסA���L���o�C�H��ҩ~�W�ꤨ�ߩ��A�����Ѽ�B�C�ϼ�A�ҤӤW���ƳX�ߤ��a�C�����y���J�өM�s�A�h������c�өM�u�H�A�������궧���D�w�u�v�C���Z���D�Ф��m�j�եH���߬��}�ݪ����P�DZ��ЫY�A�O���F�ҩ��Z���D�жǩӪ����ΩʡA��ӥ��u�D���_�_�n�B�j��_�Z���A�O�o�@�ǩӪ�����C
�@�@�G
�@�@���u�D�����S�I�A�O�������ǡA�F�l�_���𤭥N�A����_���������A�������v�B�f�}���Φ��DZ���Y�A���Ǽ��_�_��A�i�B�ݬy���_�n��C�b�Z�������ȫҫH���R�����A�]�������������C�ڡm�Z���D�Хv���n��ޡm�ȫҹ���n�y�A�ȪZ�J�Z���D�A�����T�Q�A�����Y�s�A��߹긡�A�M���P�СA�w�}�y�ơA�봲�F���A���Ȥ@�A�q�|�U�u�A�j�o�W�D�C�o�dz��O�����Ҫ��N�y�C�ҥH�m�Z���D�Хv���n�{���G����M�A�ȪZ�D����k���O�A�������j�ġA�ӬO��ߦu�@�B�ҭW��C���S�{���m�ӤW���u�Z���ǧ��g�`�n�Һ١��u�H���A���O�Ҥ��������\�̡C�� �Ѧ��i�H�z�ѡA�����ޭ����襤�Z���@���ײߤ������s���A�åB�@���N�O�G�Q�h�~�C
�@�@���ޥѪZ����u�ؤs����A�@�����m���n�z�A�@���~���ҡA�óгy�F�R�\�Ҫk�C���ަb�����Ǥ譱���i�B�o�q�_�ؤs�a��n�C�������ʤ_���w-�n�s�a�Ϫ��f�}���B�B���ʳ��ﳯ�ު������ҵ����ܤj�v�T�C���ި���A�Φ��F�ӵج��A�S�W�ѵؤs���C�M�N�H����묰�N�����謣�L�^���ީM�i�T�סA�٤ӵج��������P�����H�P�s�ؤs���۰ϧO�C�ڡm�T�ץ��ѡn�ƦC���ǩ��ЫY�A��D���W���_�Ѥl�A���Ǥ_���ߡA�~�����¦�D�̡A�A�Ǭ��Ʀi���ͳ��ޡA�۳��ޤU�Ǥ��s�u�H�A�����ǵ��i�T�סC��ҥH�R�W�������P�����A�O�]���������_�稦���M�ӥդs�A�¦�D�����_�۰�M���s�A�������_�ؤs�A���s�u�H���_�n�s�A�i�T�����_�Z���s�C���ү��P�L�������A�Ӧ��������C�դl��A�Ѥl��S�s�G�A����`�������]�A�G�S�ٵS�s�����C�� �ξ��v���Ҫ���k���ˬd�A�o�Ӷǩ��ЫY��M���i�a�A�q���ߨ�¦�D�̤����ɶ���פӤj���H�q���v�ƹ�W�[�H�s���F���O�q�o�ӹD�����ۧڶǩӻ{�P�ӻ��A�L�̽T��O�H���߬��z�פW���Щl�H�B���ެ���ڳЩl�H���C��ӱi�T�����~�Z���A�N���Хߪ��R�\�o�����j�A�H�ܦ����Z���D�������פ��ҡC���ü֤Q�@�~�]1413�~�^�A�������@�ժZ���s�A���j���өM�s�U�c�[���Ҥ��ơA�ɯ����u�A��@�u���A�~�����ΡA�̵��H�ơA���R���\�A����L���C�@�����ӯB�����H�A�ä��\�ͨƳٵ��A�Z���R�\�A�����D�A�H�̪v�H���o�C���o�D�եO��Z���D�Ъ��Ҥ覡�����F���T�����A�n�D�x���H�����o��ê�D�h�ײ��R�\�C �ҥH���Фͻ{���A�����u���Ц�_�_��C��l�ܫn��̡A�Z���@���]�C���L�b�l�z���N���@�D����Z���D�Ъ��v�T����X�G���Z���۱i�D�Q�B�i�u�M��A�h�ݲ߲M�L�W�D�A���]�i�^�T�L���W�A�s�ú٨䦳�ݾi�ͳN�A���餣���A�פT�е��ѭY�M���e�A�Ҩ��ҹD�w���q���������A�����u���ǭ������K���Ǥ]�C�� �L�{���i�T���~�Ӫ��O�������B�C�B�������u�D�u�ǡA�P�m�T�ץ��ѡn�ۻ{�����ޡ����P�����b�z����Y�M����k�W�O�@�P���C
�@�@�T
�@�@�i�T�צb�Z�����̤l�A�����C�ȲM�B�]�Ѷ��B�c��B�P�u�w�B������B�B�j�u���C�H�A�䤤�C�B�]�B�c�T�H�Ӧ۲n-�ؤs�C
�@�@�ک��m�իؤj���өM�s�ӡn�A�C�ȲM�O���N�E��I�����H�A���ɴI���ݦ�w���C�C�ȲM�ۥ��H�D�h���w�եX�a�A������̤l�Z���W�e���~���B�|�t���a�ѳX�A�S����{�B�Ӥs�]���b�E�n�^�M�X�D�Ӧa�A�x�Z�|�~�]1371�~�^�ܪZ���s�A�Q�i�T���|�����s�c�����A���Z���D�Фj���\�Ҩ��ۡA���ӯ��������ձ¹�ij�j�Ҥӱ`�x��C��̤l�Z���W�����{�D���C�]�Ѷ���C�ȲM�p18���A�O�E�趾���]���j��^���H�A13���J�ؤs���D�h�A�~�b�I�s�A�ײ߳��ޤ����N�C���m�ئ{�ӡn���G���]�Ѷ��A�����H�A�~�ئ{�b�I�s�C�����]�Ѷ��D�g�C�g�U�ˤ������ۤj�ۡA�@�Ǯ]�Ѷ����i�T�ץP�H���D�N�A���b��C�� ��ɱi�T�ץ��b�n�s�@�a�D�A�]�Ѷ�����D�N�O�i�H���C���x�Z�G�Q�C�~�]1394�~�^�A�Q�������l�ܨʫ��A�ʹ���u�D���T�ЦX�@���Ц��C���~�E�~���{�����[�C�ü֤Q�~�]1412�~�^�Q�������l����U�A�ձ¹D���q�k���@¾�ơA�^�����~�Z���n���צ�A�����Z���}�������}�s���v�C�c��O��_���ƿ��H�A���J���u�D�A�b�n�s�j�����U�خc�ײߤ����F�~�J���@�D�A�b�s��s�W�M�c�ײ߲����C��ܪZ���A�^�i�T�שR���n���A�L�e�ӲסC�b���Фͪ��m���K�D�з��y�n���A�����C�ȲM�B�c��B�Z���W�Ƹ�A���S���]�Ѷ��C�m���K�D�з��y�n��7�ٿ������v�D�B��L���G�H�G���۱i�T�צܤ��v�D�ѤH�A��Z�����u���A�M��ҾǤ��ݥ��@�A�\�˪��T�DZª̤]�C���ӮѤޡm�W�s�ä�~�O�n���v�D�Ǫ����A���v�D���~�C�s�M�ؤs�A�o�i�T�ױ¤����N�A��C�n�B�ӥյ��s�C���������l���A�����u�ޡA����a�b���A�O�^�ѭ��M�X�i�T�סC
�@�@�P�C�B�]�B�c�P�ɥN���Z���D�h�A���Ǥ��ݱi�T�D���A�禳�Ӧۤ_�n-�ؤs���C�p�G���w��A�|�t���O�]������^���H�A�ۥ��J�n�s�j�����U�خc�X�a�A���~�C�Z���A���~���]�c�A��~���M�[�C
�@�@�|
�@�@�H�C�B���������P�����s�����O���u�D���Ĥ@�j�D���A�P����{�٩v���W�A�M�N�����s���{�٥b�ѤU�����١C�M�s�����]��ӱo�W�A�v�Ƥ������P�����k�C�M�N�m���\�߿O�n �{���A�s�����H�C�B�������v�A�]�䴿�b�E�������s���s�D�o�W�A��}�Ъ̬��C���̤l���D���A���l�ͥX���D�w�q���R�A�u�`�u�ӲM�A�@���Ӵ_���A�X�Хö������20�r�����ЫY�A���q�ӮѩM�m�ն��P���n �O�������N�ۦW�H���ӬݡA�o���ЫY��ڤW�O�s���ߩv���ЫY�C�ӥC�B������A�̤l�k�Dz��h�A�ëD���O�ߩv����C�Ҧp�A�s�������x�s���}�D�|�A�N�����s���Q�T�С����f�O�A�䤤�G�Цo�M�T�г����ڱ`�����{�s���}�M���֤s�A���Ф����s�`���Z���Ӥl�Y �A���o�ӻ��k���ɪ����Y�����M���A���G�O�M�N�H�᪺�s�����������p�A�]�����{���֤s�O�M��~�}�Ъ��D���C�ӳ��Фͧ�O���X�s�������_�_�ؤs�B�o�W�_���e�s���]���ʥ�ɤ����e����f�^���[�I�C��j�N���G�C�B�����̤l�W�ڭs�`�]�D���^�A���פ_�ؤs���N�}�A�ǹD�k�_�����H�C�����H��u���e�s���_���j��q�A���@���իʫط��[�A�۫�Φ��s�����A�S�٤��N���C�M��ؤs�D�h���M�����_�_�ʥն��[�A�������ض��D�����G�A�@�ӵءA�@���N�]�C�ӵةv���Ʀi�A���N�v�C���K�C�� �o�ǥv�ƻ����A�s�����Φ��_��ɦ�a�B�]��o�W�A�H�γo�ӹD�����ǩ��ЫY���A���٦��ݶi�@�B���ҡC
�@�@���������p�]�ϬM�b�Z�������u�D�M�s�����ǩӤW�C���u�D�h�����i�J�Z�����A�O�E��X���H�N�ӳq�A�L�v�q�������̤l���D �M��M�e�A����~�Z���s�A�Q�~���������A�������B�a�N�A�믫�M���A��B�p���C�� �b���Ф͡m���K�D�з��y�n�@�Ѥ��A�C�B���h�@���᪺���u�k��A�Ĥ@�W���|�j�ɡ]���}���^�A�����ɩ~�Z���|�Q�E�~�A�X�j�x����������u�E��M�X���u�D�A���赴�L���A�_�O���s�A�ܤ��Q�G�~�k�A�P�L�s�`���״_���s�c�C�� �|�j�ɦ��M�X���u�D���ɡA�N�ӳq�w�b�Z���F�|��Z���A�N�w�P�u�]���ΥҤl���^�C��Ӿ|�j�ɱ®{�i�u�M�A�Φ��Z�����s���A������N�Z���D�����D��C�O���|�j�ɮv�{�Ƹ��{�x�ҡm�j�Ѥ@�u�y�U�خc�O�n�S���O���|�j�ɮv�q���u�D���ǩӡA���m���K�D�з��y�n�{�������D�̤l�N�ӳq�~�Z���\�b���������ɡC�j�ɷ����D���u���Ǥ_�ӳq�A���赴�L���A�_�O���s�A�h���K�̤l�t�Ф��a�]�C�Z���ǥ��u�л\�ۤj�ɩl�C���b���ФͲ����A�|�j�ɬJ�O�������k��A�S�O�s�����ǤH�C�m�Z���D�Хv���n�{���G���n�����A�_����u�D����A�|�}���_�W�X�D���u�A�۵M�n�ije�l�����u�D�������ǡA���N��D���¨��ӬݡA�L�ëD�O���u���D�h�C�L����{���@�ʦh�H�A�̱o�N���̤l�i�u�M��q�M�L�B���@�����D�k�A�Ӥ��٬O���u���C�� ���M�|�j�����H�{�w�����u�D�ǩӡA���b�m���K�D�з��y�n���A���H�|�j�ɪ��L�s�`�A�T��O�ݤ_���u�D�A�æC���C�B���k��C�L�s�`�P�|�j�ɤ@�_��Z���A���״_���Ԫ��}�a���Z���c�[�\�Ҭƥ��C��̤l�i�D�Q�S§�M�L�����p��ߥ��@�D�k�C���Фͻ{�����|�j�ɡB�L�s�`�ѥ��u�̤l�A�i�D�Q�v�s�`�ӾǤ_�p��A�\���u�ӭݥ��@���̡C�e�i�}��өҾǤj��A�_�O�Z���E�����u�O���C�� �L�s�`�k�]��D�w��Ӥ_���N�x�Z��~����C��ءB�n�Ѥs�A���~�����U�خc�C��
�@�@�M��A�s�����b�Z������A�}��_�Q���O�L�A�F�l��ƪ̡A�O��ӨӦ��E�誺�s���D�h�C�@�ӦW�s�եȺ֡A���W�p�A�E�_���t���H�A�s�����ĥ|�N�C���J�Z���s�ׯu�A���v�Q�T�~��ש��u�g�A���E�{���D���ҡC�����S�_�d�����~���v�����Ҧ�A�״_�Ӥl�Y�_�u�[�A�պ֤��D��ơC�� �t�@��W�s���`���A�s��H�A������a�n�ؤs�A��E�C�s�A�A�E�Z���_���C �b�պ֤��M���`�����V�O�U�A���u�D�s�����b�Z���o��j�W�ҵo�i�A��d���~���A�Ӥl�Y�D�[�����s�����V����Ǽ����@�ӭ��n��a�A�H���s�����x�����_�A������_�Z���D�h�C�����A�����s���}�D�|�Q���C�M���v�B�d���~���A�Z���Ӥl�Y�D�h���u���B�Цu�s���~��F�s���}�A�����״_�s���}�U�B���t�C��ӡA�]���u���O�D�s���}�j���H�u�Z���v�x�s�A�H�����P�Z���D�ЫH�����ǩ����Y�F�ӥЦu���D�i�H�ɬӤj�Ҭ��x�s�A�G�H�N���ۥ��A�Цu���t��X���A�t�V�s���s��F�����֤s�s�ؤ@�B�D���A�D�^�ɬӤj�ҡC �M�N�H���s�����b�ؤs���ǩӤ]����_�Z���s�����C��N�ؤs�s�����@��18�B�D�|�A����N�ؤs�D�[28�B���j�b�C�䤤��p�K�˷��B�s�U�P�h�[�B���l�p�Ҥ��l�B�C�_�W��D�|�B�n�p���Ѯc�B�a�s���������B�s�U�ӯ��c�B�n�p�s�P�[�B�_�p�u�Z�c�B����W�q��10�B�D�[�A���O�ѪZ���s�Ӥl�Y�դ@�e�B�J�u���A�P���g��X�F�A���]�c�i���s���s�����D�h�۩����y�B�M�������~�_�ةM����C �Z���s���������p�i���@���C
�@�@��
�@�@��W�ҭz�A�Z���P�E�誺��ӭ��n�D�ЦW�s�n�M�ؤs�A�b�D�ЫH���M�D���ǩӤ譱���ۤQ���K�����p�Y�C�j�P���{�b�|�Ӥ譱�G�Ĥ@�A�Z���M�n-�ؤs�A�㦳�˱K���a�t���Y�A�ۥj�Τ��A�H���M��ƪ���y�Q���W�c�A�o�O��Ϥ����D�����ʥ�y���e������F�ĤG�A�b�D�аH���Φ��譱�A�Z���M�n-�ؤs������H���ۦ����B�A�Y��ϳ��H�Ѥl-���߬��H���R�������Y�A���H�����N�@���D���Ҫ��D�n��q�F�ĤT�A�n-�ؤs�O���u�D���D�n�o���a�A�ӪZ���h�O���u�D�V�n��Ǽ����D�n��a�A�Z�������u�D�̪�D�n�Ѳn-�ؤs�D�h�ǤJ�F�ĥ|�A��N�Z�����u�D�����s�����V����Ǽ������n���I�A�Ʀܦ����n-�ؤs�\�h���n�c�[���H�O�귽�w�C��Z���P�n-�ؤs��ϹD�����y�i��`�J�ҹ�M�z�A�N�״I���u�D���v����s�A�]�蘆��[�j��϶����D�баȡB�dzN��y�M�}�@�M�u�ȹC�㦳�n���N�q�C����u�O��B���X�o���D�ءA�@�߿j�ޥɤ��|�A�H���ް_�D�ɩM�Ǭɪ��`�N�C
�`���G
�p�B�z�ҵۡm���s�q�|�n�{�����u�����s���i���ǵ|�����v���A�s�F�Ш|�X����1999�~���A��103�C
�m�@�v�ˬӫҤW�٤��աn��18�G���S���X�g�s�i���H���_�����e�a��������|���C
�ży�m���w���ӡn��75�m����ӡn�����Z�m�өM�s�O�O�n�C
�m�ܩw����m�q�ҡn��24�G�����x���W�����n�����O�s�T�x�q�C�����|�@�d�E��A������s�ƨҡC�q���C��
���|�I��m�����s�ӡn�A��a�Ϯ��]���]�s�m���ؤs�����O�Z�n��17�U�A�u�ˮѧ�2004�~���A��203�C
�������m���s���|�ҡn�A���������B�i�ǥD�s�m���s��s���O�n�A�C�q���v�X����1992�~���C
�B�z�ҵۡm���s�q�|�n�A��103-106�F�s�ҥD�s�m���s���U�n�A�٫n�X����2001�~�A��14-18�C
���Q�g�m���۬O���H�P�R��A����ʸU���ɥ��X�X���N���s�����F���c���ȸg�٪챴���n�A�m�٫n�j�Ǿdz��n2003�~3���C
�����t�m�Q���@�����N���ꤧ�]�F�P�|���n�A�����B�\���~�B�٥ɥ���Ķ�A�T�p�ѩ�2001�~���A��339�C
���߭�m���M�Z���s�c�[�g�٦��J�L���n�A���m����D�СP�Z���s����D�Ф�Ƭ�p�|�פ嶰�n1994�~�W�Z�A��H�m���M�ɴ��Z���c�[�g�٦��J�챴�n���_�m�Z���ǥZ�n1994�~��4���C
���i���m���D�����n����40�m�᳡�E�P���e���P�e���n�]���U�^�A����Ϯ��]���m�Y�L�_��ߡA��880
���i���m���D�����n����40�m�᳡�E�P���e���P�e���n�]���U�^�A����Ϯ��]���m�Y�L�_��ߡA��880-881�C
�}���ȵۡB�u�Э�B�d���ؾ�z�m�}���ȹC�O�n��1�U�m�C�өM�s��O�n�A��52�C
�m�M����P���v����n��16���������~�|��W�B�ࡨ�A�m�M����n��9�U�A���خѧ�1985�~���A��437�C
���ߧӡm���һP�Z���s�c�[�g�٦ҭz�n�A�m�v�оǬ�s�n1998�~��1���C
[��]�����G�m�j���өM�s�ӡn��7�m�զs�d�����n�C
[��]�����G�m�j���өM�s�ӡn��7�m�զs�d�����n�C
�m������P�@�v����n��257���Źt�G�Q�@�~����B�表�A�m������n��44�U�A������s�|���v�y����s��1982�~�v�L���A��5148�C
16�m������P�p�v����n��32�����y�T�~����Фl���A�m������n��50�U��0832�C
[��]�»F�����B�����~���I�m�����[�n��4�m�a���G�n�A���Ш|�X����2001�~���A��70�C
�m�ө��g�@��s�n��406
[��]�涳�l�B�c���ءG�m�j���өM�s�ӡn��3�m�C�t�տ١P�մ���ÿ�ڡn�A���ߧ��I�աm���N�Z���s�ӤG�ءn�A��_�H���X����1999�~���A��294�C
[��]�涳�l�B�c���ءG�m�j���өM�s�ӡn��3�m�C�t�տ١P�զs�d�����n�A�m���N�Z���s�ӤG�ءn��290�C
[�M]�B�m�x�m�s�����O�n��2�A���خѧ�1957�~���A��87�C
1 ���ߧӡG�m�������@�Ѯv�P�Z���D�n�A�m�Z���ǥZ�n�A1996�~2���C
2 ������G�m���O�Pù�X���t�ҧg�q�O�O�n�A����ۡm���u���Q�ءn�A193���A�����j�y�X�����A1987�C
3 �i�����G�m�C�g���ܡn�A���m�L�N�O�ѩ�����s�n��16�C
4 ���@���G�m���w�ȸܡn��2�m�ӳ����O�P�������q�n��23���C
5 �J�A�G�m�F�鶰�n��19�m�~�e�N�x���ԥ������q�O�n�A��228���C
6 ���_�}�ۡG�m���N���|�ͬ��v�n�A482���A������|��ǥX�����A2004�C
7 ���~�U�G�m����D�Хv�n�]�U���^�A816���A������|��ǥX�����A2001�C
8�J���`�B�f���`�ۡG�m�D�dzq�סn�A���|��Ǥ��m�X�����A1999�C
�ѦҮѥءG
1�B �i�ʥɡ]�M�^�G�m���v�n�A���خѧ��A1974�~���C
2�B ��Ʈ��G�m��P����D�Ы�Q�v���n�A�|�t�H���X�����A1999�C
3�B ���~�U�G�m����D�Хv�n�A������|��ǥX�����A2001�C
4�B �Ǯ��M�G�m������|�q�v�n�]���N���^�A�s��Ш|�X�����A1998�C
5�B �]�@�̡G�c���L�A�Z�~�j�ǭ��Ǿǰ|�v�оǫY�б¡F���ɬ¡A�Z�~�j�ǭ��Ǿǰ|�v�оǫY�դh�͡^
�M���Ф͡G���K�D�з��y�A��7�A�ڸ��Ѫ��Z�å~�D�Ѳ�31�U�C
�����H���s�A���ιD�ì}�����O�����F���عD�ò�18�U�C
���B�D���s���G�Z���֦a�`�u���H�j�����F�A���ιD�ì}�����O�����A���عD�ò�18�U�F���իؤj���өM�s�ӡA��6�A���N�Z���s�ӤG�ءA��_�H���X�����A1999�~��1���A��121���C
�����w�B���ߧӵۡA�ؤ�X�����A1993�~��1���A��83���C
�D�ÿ�n�A�����A�i�T�ץ��ͥ����A��1�P���C
���իؤj���өM�s�ӡA��2�F�t���������s�G�D�a���۲��A�媫�X�����A1988�~�A��1���A��1250���A�j���өM�s�t���O�C
�P�`1�C
�����y���~�襻�A���h�ҡC
�Ѩ������w�B���ߧӵۡG�Z���D�Хv���A��197���C
�M�ży�G�Q�G�~�襻�A���å~�D�Ѳ�31�U�C
�M�D�����Ӧ~�襻�A���å~�D�Ѳ�31�U�C
�i��B���k�åD�s�G�C�B���P�s���}�A�E��H���X�����A1999�~��1���A��201���C
�P�`1�C
�������D���G�n�s���x�P�u���ǡA���ιD�ì}�����O�����C
�P�`1�A��6�C
�P�`1�A��6 �C�t�����{�x�ҡG�j���ս�Z���s�j�Ѥ@�u�y�U�خc�O�A���իؤj���өM�s�ӡA��12�C
�Z���D�Хv���A��123���C
�P�`1�C
�P�`1�C
�����j���өM�s�����A��4�C
�����j���өM�s�����A��4�F���K�D�з��y�A��7�C
�i��B���k�åD�s�G�C�B���P�s���}�A��250-252���C
�Ѩ���ۡG�E��D�Ш�d�~�A�T���X�����A2001�~��1���A��174-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