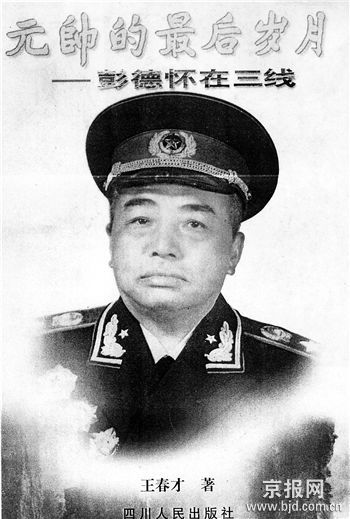
圖一:《元帥的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王春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不是最早披露彭總在三線經歷的書今年初,沈國凡著《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一書出版,很多報刊都對之進行了選載或連載,《中華讀書報》4月18日還刊出一篇題為《走進彭德懷的最後十年》的文章,說“作者充分運用自己身在攀枝花鋼鐵公司工作多年的有利條件,從1975年就開始採訪和搜集資料……取得大量第一手資料”。其實,這樣的說法是不足信的。因為1975年,仍是“四人幫”橫行天下的年代,彭德懷雖已屈死,但頭上還頂著所謂“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黨分子”黑帽,誰敢為他評功擺好,就會立即遭到批鬥。即依我而論,1963年,我在過團組織生活時,響應黨委號召,暴露思想,我質疑說廬山會議本來反“左”,後來反右,批彭德懷,豈非導致更“左”?我的這些言論“文革”中被揭發出來,批鬥我時,說我為“反黨分子彭德懷鳴冤叫屈”。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彭德懷平反了,我也平反了,我的這項“罪名”才被勾銷。1975年,沈國凡才25歲,說那時就已開始採訪知情者,為寫彭總作準備,這是不足信的。沈國凡在《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書末的《跋》中,一開頭寫道:“彭德懷自1959年廬山會議蒙冤之後到哪里去了呢?……由于歷史的原因,這個謎一直很少為國人所知道。”作者說這話的言外之意,好像他是第一個揭開這個謎底的人。其實這同樣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真實的。
有關彭德懷在“三線”的史料是誰最先披露的?
我1979年初調京後,經歷了批判“兩個凡是”、破除個人迷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多次學術會議上,人們都談到該怎樣看待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派他去成都,擔任西南三線建委第三副主任,緊接著又批判《海瑞罷官》,將彭徹底打倒這一段歷史。我認為,回答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彭德懷去了三線後的所為、所想。事實上,這是一段歷史空白,黨史學界完全不清楚。1986年春,時任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副局長(後任規劃二局局長、國家計委三線辦主任)的家兄王春才及原在三線工作、時任國家體改委辦公廳副主任的李爾華一起來我家聊天。王春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國防工辦任基建規劃處長,多次與彭德懷一起開會,還一起看過電影,他與李爾華,都了解彭德懷在三線的不少情況。交談中,我當即建議王春才,把彭德懷在三線的情況寫出來,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寫,不清楚的,採訪知情人。鑒于一些知情人年事已高,要抓緊,這也是搶救史料,最後寫一本彭德懷在三線的書。王春才認為我這個主意很好,李爾華也表示支持。于是他回去就開始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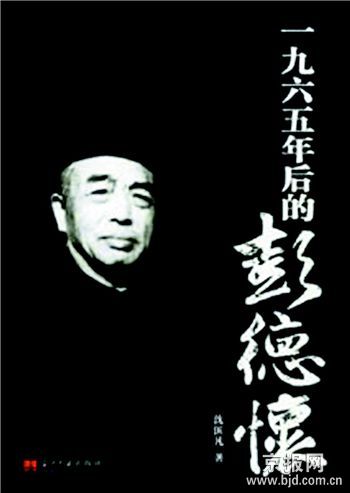
圖二:《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沈國凡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出版
為了取得彭德懷在“三線”的第一手可靠資料,王春才採訪了大量的知情人
王春才先後採訪了彭德懷當年的秘書綦魁英、警衛參謀景希珍、司機趙鳳池、炊事員劉雲、理發員賈月泉、醫生李佩宜;又採訪了西南三線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華、第四副主任錢敏、秘書長楊沛、冶金局局長陳鳳梧(當年曾陪同彭德懷視察成昆鐵路、攀枝花)及機械軍工局、綜合局、煤炭局有關負責同志;並採訪了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朱光、西南局國防工辦主任蔣崇璟、冶金部副部長李非平(曾任渡口市委副書記,陪同彭德懷視察攀枝花)、西南兵工局局長李敏、宜賓地委書記沈學禮、成都東郊火葬場辛自權;彭德懷夫人浦安修、侄女彭梅魁、中央軍委《彭德懷傳記》編寫組組長王焰等數十位知情人,他們為王春才提供了彭德懷在三線的豐富、可靠的資料。
王春才于1986年10月動筆寫《彭德懷在三線》。這年冬天,他來京,將已寫了十幾萬字的書稿交給我,請我審改。我修改後,推薦給華夏出版社出版,該社確定由劉衛平擔任責編。劉衛平定稿後,轉呈中央軍委《彭德懷傳》編寫組審稿,該組主任王焰與顧問浦安修親自審稿,浦安修還為該書題詞“人間毀譽淡然對之,身處逆境忠貞不矢。”為了在紀念彭德懷九十誕辰(1988年10月24日)時此書能夠出版,經有關部門協調,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及時出版了此書。二個月後,一萬多冊即銷完,又加印三萬冊,該書頗受讀者的歡迎。其後,王春才又補充了六萬多字內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該書第四次印刷,書名改為《元帥的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在1998年彭德懷百年誕辰時,王春才再次為該書補充內容,薄一波為該書寫了書名,隨即出版。可見,關于彭德懷在三線的史料,最早由王春才著的《彭德懷在三線》一書作了披露。
新出版的《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一書很多文字與《彭德懷在三線》雷同
隨著王春才《彭德懷在三線》一書的多次印刷、報刊的大量轉載,應當說,對彭德懷在奔赴三線後忍辱負重的生活情形及隨後遭到的殘酷迫害、屈死經過等,黨史界、理論界乃至于普通讀者已比較清楚了。可沈國凡在他年初出版的《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跋”中,仍說“對于這位蒙冤而死的共和國元帥,反映他光輝一生的書籍和文章很多,但至今很少有人寫他忍辱負重,奔赴中國大三線建設,在中國西部最大的鋼都——攀枝花……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最後為真理獻身的事跡,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這種說法顯然是缺少對史料的佔有的表現。王春才的《彭德懷在三線》,不正是充分寫了彭德懷的這些“日日夜夜”及“事跡”嗎?其書第五章“金沙江畔”,不正是寫的彭德懷196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到攀枝花鋼鐵基地視察的情形嗎?
我大體統計了一下,新出版的沈國凡的《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一書,書中有28章、144頁共11萬多字與《元帥的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一書中27節、185頁共計9萬9千余字文字雷同,而且也不加注釋,這種做法讓人吃驚。
還必須指出,王春才請洪學智將軍為其《彭德懷在三線》一書所作的題詞,沈國凡卻將之妄改成“洪學智的讚語”,王春才請朱光部長為其書作的序言,其中有幾處文字也被抄用,沈國凡並將序言說成是朱光的回憶。
王春瑜 5月11日于京華(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編輯:大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