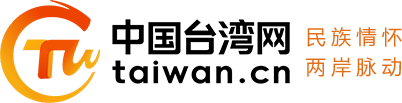將青春寫在塞上大地——記五湖四海“支寧人”
新華社銀川9月17日電 題:將青春寫在塞上大地——記五湖四海“支寧人”
新華社記者曹健、艾福梅、馬麗娟
他們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支寧人”。
隨著汽笛鳴響、卡車轟隆,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數十萬來自全國各地的支寧人員匯聚寧夏。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奮鬥在各行各業,扎根寧夏,奉獻寧夏,用寶貴的年華譜寫了最美的青春之歌,在悄然改變著塞上大地一草一木的同時,也留下了一筆筆珍貴的精神財富。
家國情懷:哪里艱苦哪安家
1954年,18歲的戈敢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放棄留在江蘇南通農業學校當輔導員的機會,從江南水鄉千里迢迢來到幹旱少雨的西北。
“當時因為生病,學校沒給我報名。我一聽堅決不同意,強烈要求到寧夏去。”戈敢回憶說,在那個熾熱的年代,“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青年人的至高理想。
解放初的寧夏十分落後,眾多領域尚屬空白,各方面亟待建設,人才極度緊缺。而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來到寧夏的一批批幹部、科教文衛人員、大學生、工人等則猶如“甘霖”,解了寧夏初建時期的“人才之渴”。
火車一路向西,故土漸漸遠去,青山綠水漸變戈壁荒漠,幾日幾夜顛簸後,終于抵達寧夏。
盡管有心理準備,寧夏的落後還是遠超出支援建設者的想象。1952年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的陳樹蘭,先被分配到西安的一家醫院,後聽聞寧夏急缺醫療人員,她果斷放棄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來到銀川。
“當時根本不像城市,比縣城還小。”這是陳樹蘭對銀川的最初印象。“除了兩座古樓,都是低矮的土坯房。隨便揭開一個破舊的門簾,里面可能是郵局或商店,且物資匱乏,很多東西都得從外地帶。我穿一件普通的針織毛衣,也有很多人圍著看。”陳樹蘭說,但她並不計較環境,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
銀川尚且如此,更多“支寧人”去往的是更為艱苦的固原、石嘴山等地,有些地方偏遠,不通公路,還得換乘馬車、驢車才能到達。
來自浙江嘉興的梅曙光,年僅6歲時父親因抗日犧牲,懵懂的他只知自己成了孤兒。“長大後,我才逐漸明白了父輩的家國情懷,那是一種‘義無反顧’的情感。”十幾年後,梅曙光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擇。1959年從北京林業學院畢業後,他來到了“進了林區卻不見林子”的六盤山區。
艱苦奮鬥:在荒灘上創奇跡
“支寧人”迅速充實到各行各業,憑著戰天鬥地的精神,排除萬難,為寧夏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
民以食為本,可當時的銀川平原,多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鹽鹼灘。“種子挖出來嘗一口,又鹹又硬。”戈敢說。被稱為“土壤癌症”的白僵土是最難改良的土地,曾被外國專家斷言“改良這種土地不是我們這代人能辦到的事”。
戈敢在內的科研人員沒有退卻,迎難而上。從1962年開始,戈敢與農業研究所的同事,先後赴河北唐山、遼寧盤錦考察。他們反復試驗,大膽提出“挖溝排水”和“種稻洗鹽”的方法,開啟了三十年轟轟烈烈的鹽鹼地改良工作。參與改良的還有大量墾荒的支寧青年,他們或住在四處漏風的土坯房中,或擠在冬冷夏潮的地窨子里,烈日當空揮鐮割麥,披星戴月蹚水背稻。
在支寧青年和各族群眾不舍晝夜的努力下,寸草不生的鹽鹼地變成了稻菽浪涌的萬頃良田,“銀川”變成“米糧川”。
在火熱的“三線建設”中,中色(寧夏)東方集團有限公司無疑是典型代表。這家企業的前身是1965年從北京有色金屬研究院遷建到寧夏石嘴山市的905廠,隨之而來的還有大量科研人員。“一家企業擁有四五百名科研人員,這在當時的西北是非常難得的,更難得的是他們來自全國70多所高校。”中國工程院院士何季麟回憶說。他于1970年分配到這里,在國外企業嚴格封鎖相關技術的情況下,他和其他科技人員不斷攻關,終于使鉭鈮鈹材料加工達到世界級水平。
“科研人員執著認真,廠區綠化栽樹都是用尺子量、用線拉,這正是科研攻關所必需的。”何季麟說,正是憑著對科研的熱愛,艱苦奮鬥,無悔奉獻,才奠定了企業在鉭鈮鈹加工方面的“國家隊”地位。
陳樹蘭成為寧夏內科學奠基人,李范文成為神秘西夏文字的破解者,謝守棟為布魯氏菌病防疫做出重要貢獻……在寧夏,貢獻突出的“支寧人”不勝枚舉,更有大量“支寧人”不為名、不為利,為荒灘上創奇跡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艱苦奮鬥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的信念和動力。”謝守棟說。
融入傳承:寧夏有“天下人”
“風還是塞北風,雨已變江南雨。”有網友如此詩意描述“支寧人”給寧夏帶來的變化。歲月悠然,自治區六十一甲子,“支寧人”的標簽逐漸淡去,“寧夏人”的符號日益變濃,他們的融入無疑增強了寧夏開放包容的氣質。
在銀川,人們習慣用普通話而非方言交流;原本不吃魚的本地人愛上了魚宴……“這座城接納了這些人,這些人也融入這座城。”今日,“寧夏有‘天下人’”依然廣為流傳。
當年生龍活虎的青春早已不在,但一批批“支寧人”秉持的不畏艱辛、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等精神,卻永遠在塞上大地薪火相傳。
陳樹蘭的學生,很多成了活躍在寧夏醫療戰線的棟梁之材。“有很多次機會走,但我安心留在了寧夏,這里的病人需要我。”陳樹蘭將這一過程說得風輕雲淡。她從醫66年,如今已87歲高齡,華發滿頭,但還堅持每周一次專家門診、五次查房,身體力行繼續為寧夏培養醫學人才。
82歲的謝守棟早已退休,受他影響,女兒成了寧夏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畜牧獸醫專業的教授,兒子在疾病預防中心繼續從事布魯氏菌病預防。“他們都已是寧夏人了,會包餃子,愛上了吃羊肉。”
梅曙光當初參與在西吉縣火石寨鄉種下的千畝樹苗,如今正鬱鬱蔥蔥。他說:“人活百歲,樹才長成。留下一片林子造福後人,我的使命已完成。”
寧夏沒有忘記他們。在剛剛揭曉的“自治區60年感動寧夏人物”中,不少支寧建設的典型人物赫然在列。
山川沒有忘記他們。銀川平原的稻浪滾滾,六盤山區的松聲陣陣,城市鄉村的一街一路、一磚一瓦,無不在訴說和彰顯著“支寧人”流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