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百年前從大陸避禍逃到臺灣定居的農民家族,從晚清到日據時代,再到光復後國民黨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來的真實故事,將給熟知海峽兩岸國共鬥爭史,卻不了解對岸社會演變和民間生活史的大陸讀者,帶來鮮活的全景式畫面:
“弘農堂”三合院里祖先從大陸挑過海峽的“唐山石”,象徵了家族的血緣根基;日語流利的三叔公“二戰”後期被調往上海法院做通譯,包裹著臺灣被出賣和扭曲的歷史;通靈的外公呈現著臺灣民間信仰的奇觀;奶奶和“稻田里的媽媽”是一個家族能夠生存延續的保衛者;能創業、能闖禍的強韌父親是臺灣進入工業時代的弄潮兒;而第一人稱的敘述者體驗了時代的創痛,同時也領受了歷史賜予的經驗智慧,他描繪出臺灣社會五光十色的世相,和幾代人在時代變遷中磕磕絆絆、摸爬滾打、艱難奮鬥的故事,不啻一部臺灣從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的演進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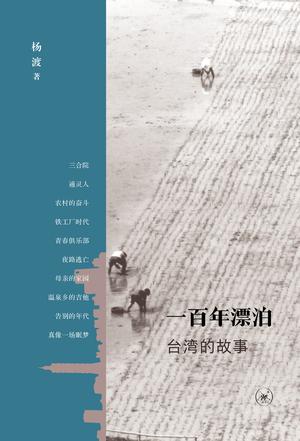
一百年漂泊 臺灣的故事
作者: 楊渡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6年1月
定價: 48.00
序言:讀楊渡新作《一百年漂泊》
趙剛
九月中旬,楊渡兄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有一部新近完成的名為《一百年漂泊:臺灣的故事》的書稿,想請我寫點東西或是給點意見之類的。這本書主要是以他父親,一個原本注定只能是臺中烏日的鄉下農民,在一九七○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終而成為成功的鍋爐制造業者的一生故事為綱,但也兼寫了頭家娘、地方、家族、信仰、中小企業、工人的故事。"這本書或可作為臺灣史的側顏一讀吧!"——楊渡如此說。
老實說,我有點狐疑。兒女不是不能寫父母(或反之),但要寫得回蕩婉轉寫得有公共意義,也的確比較難,因為常常作者那一廂情願的耽情,不見得也能讓讀者們產生共鳴。最近這些年頗流行作家爸爸寫兒子寫女兒,我就常不免詫異于這些作家的膽大,這樣親密切膚的關係也敢動輒寫一本書?對象越寫越近,世界越寫越小,就不擔心如此的寫作泄露的不是經驗的逼仄與創作力的枯竭?于是我想起陳映真的一句我以為的名言:"一個人其實不一定要寫作!"
利用課余事親之余,我一頁頁讀下去,竟然發現,沒有勉強,感到興趣,頗有收獲,甚多感慨。《左傳》里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而楊渡兄不正是一個孝子嗎?而且還是一個對大家都可以有所饋贈的孝子。楊渡說得很精準:這本書"告別的不只是父親,是一個時代"。
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個倫理的意義上,是一個孝子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傳",雖然我必須說它和傳統的行傳不類,因為它並非只是旌表揚善而已,而更是子對父的善惡清濁都試著去盡可能地認識理解,從而認識理解他自身的一個努力。但在一個知識的、社會的意義上,它更是對臺灣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極其壓縮的"短工業化時代"的一個見證與一紙吊文,以他的父母親為陀螺,畫出小人物在時代的快速旋轉中,在社會的坑坑洼洼中,顛撲衝撞的線條痕跡。因此,這本書的難得可貴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維度中的書寫,而是以飽滿的對親人的感情為底氣,努力展開對一個時代、對一群轟轟烈烈但卻將被徹底遺忘的人群的認識與反省。而正由于所書寫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沒有某些作家寫大人物父親所帶著的濃濃翻案風,因為這樣的小人物在歷史上根本是無案可稽的。楊渡的寫作救贖了他的父親,更救贖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體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歷史書寫所遺忘。
因此,這本書的確是"可作為臺灣史的側顏一讀"的!
豈止,透過"魅寇"(楊渡父親名字"銘煌"的日語發音)的不尋常的旺盛生命力,我們看到了一般社會經濟史所難以勾畫出來的隱密而驚人的線條,因為魅寇雖是一般意義上的小人物,但卻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撐破體制與現實所加諸他的種種限制,而這或許是眾多關于臺灣當代的工業化或發展敘事所無從著墨的一個重要側面,因為它們太強調那些既存的結構或文化條件了。楊渡在"終曲"里也如此說:"是的,一個時代,一個屬于工業時代的風景,正隨著父親的離去,慢慢結束了。"讀這本書,讓讀者在魅寇的翻騰不定的無畏人生結束後,深刻地感喟于一個潛在的問題:我們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們又將如何安身立命?我們又將如何面對並迎向未來?我們,又將如何被後人回憶與理解?
以魅寇(一九三○——二○一四)的一生為主要線頭,楊渡編織出一個兼具深廣度的社會、人文與歷史的交響風景。又,如果也可以說魅寇的故事是一個被他兒子詩人楊渡所鏤刻出來的一片生動、可信,乃至可愛的浮雕風景,那麼,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鑲嵌于一個由小至大、由邇至遠的多層次背景架構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親與母親的家族史、烏日(或臺中地區)的社會經濟史,以及作為大背景脈絡的日本殖民史與政權更迭史。
這本書是以主人公魅寇的老病臨終為楔子,引領出每一章的歷史回溯。今昔交織,使得敘述張力飽滿。從銘刻著"弘農堂"這個堂號的一間老三合院,作者講起臺灣的一九六○年代,一個工業化的馬達聲即將響徹全島之前的醞釀蠕動時代。在書寫中,楊渡將這段工業化前的農村史和先人渡海來臺、日本殖民統治、美軍大轟炸、成功嶺的馬場、神風特攻隊以及父係與母係的父祖輩的湖海漂泊或神鬼離奇或兼而有之的命運,以一種蒙太奇的方式拼貼起來,使讀者在平靜的敘事中隱隱地感受到遠方的風雷與腳下的震動。讀楊渡的書,讓我不免想起臺灣這個島嶼的故事的離奇荒誕與血汗現實,絲毫不讓于拉美,但為何終究沒有出現那樣的"魔幻寫實"的文學?這當然是離題了。
"烏日"是一個和包括我在內的眾多成年臺灣男性都發生過關係的地方,因為著名的軍事訓練中心成功嶺就在烏日。千千萬萬的大專生新鮮人都曾在烏日的星空下睡過六周,但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對這個地方可說一無所知。一九九一年後我來臺中教書,烏日雖是緊鄰臺中市,但卻是一次也沒去過,直到近些年有了高鐵,才常常"到"烏日,從高架公路到烏日高鐵站赴臺北;這也還是一次也沒去過。我服兵役時,連上有一個背後刺了一幅裸女圖的悍兵的家鄉就是烏日,烏日讓我聯想起黑道。那時,我就對這個地名很好奇,感覺這個地名詭異離奇得很,令我無端想起一首黑人靈魂曲《午夜的太陽》。讀了楊渡的書,才知道烏日的地名由來。原來,先民因為烏溪河面寬闊,在靜靜如湖的河水上見到"紅彤彤落日,映滿河面",就稱這一帶為"湖日",然後到了日據時期,日本人不索本意,只憑發音,改成了如今的"烏日"二字。但這個誤會還算是"美麗的誤會",因為相對于"玉井"則是讓人哭笑不得了。在楊渡的書里,因為講到他來自玉井的工程師大姑丈,而有了這一段黑色插播:"玉井原名蕉芭年,余清芳在那里發動襲擊事變,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派出軍隊,機槍大炮全面鎮壓,為了報復,日本人在村子樹一根竹竿,約一百二十厘米高,凡是超過的男子,一律槍殺……它被改名玉井,那是東京一個風化區的名字,殖民政府有意用它來詛咒它的後代。"
借著自家親見與長者口傳,楊渡帶我們回到一個曾經風景迥異的烏日,在那一方水土之中"天空是澄藍的,溪流是幹凈的,土地是柔軟的",而每一個早晨"都是用晶瑩的露水去冰透的風景"。這是楊渡對一九六○年代烏日的風景記憶。但楊渡並不是一個田園派詩人,他在明媚的大地上看到陰暗的皺褶,從晴空深處聽到霹靂。在謂之烏日的那塊地界上曾終日行走著一個遭受白色恐怖荼毒的"在自己家鄉流浪",被人叫作"空竹丸仔"的斯文瘋漢。那里的樸實的農民也曾因為幹旱而極其惡毒地搶奪水資源乃至親戚反目。而更之前,在日據時期,則因為成功嶺是日本人的軍事養馬場,而使烏日成為經常要躲美軍轟炸的一塊惡地;曾經,成功嶺上、嶺下有過馬匹在如雨的炮彈下,失魂落魄、尖聲嘶鳴、左奔右突的風景,而楊渡的二叔公就是在這樣的空襲下失去了一條腿。這樣一個烏日,在"二戰"末期,又因日本的軍事需要,成為暫時軍服生產的最重要紡織基地,而這個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下的少有例外,卻成為戰後的重要紡織廠——吳火獅的"中和紡織廠"——的前身。
然後就進入了這本書的主要樂章——轟隆隆的臺灣一九七○年代。魅寇關閉了他脫農轉工的第一個工廠——瓦片廠,開啟了他的"鐵工廠時代"。那是一個雄性的、躁動的、任性的、喜新厭舊的開創時代。
一九七○年前後是一個關鍵的轉變年代,世世代代綁在土地上的人們開始受到無處不在的"發財"誘惑,于是有人開始種植各式各樣的經濟作物,甚至養一種名叫"白文鳥"的經濟鳥,以為可以牟取暴利,但潮起潮落,總歸是一場熱鬧的空,搞得很多人血本無歸。雖然欲望的心血無時無刻不在劇烈地翻攪著,但是一頭熱的人們對于如何理財、如何借貸、何謂信用、何謂規劃,可謂一竅不通,而這只要看到那時的主要金融機構仍是碾米廠或是各種寄生于地上的信用合作社的地下錢莊就可略見一斑了。而魅寇就是這個時代旋渦下的一個屢遭滅頂但仍奮泅向前的小人物。而那時的烏日已經和一九六○年代初的烏日風景迥異了。一九七○年初,那個原先叫作"臺灣紡績株式會社"(村人習稱的"布會社")的中和紡織廠,已經擴充到一千五百人的規模,而由于大多數勞動者都是女青年,又給這個小鎮帶來了無限的青春風光與愛情故事。也就在此時,瓊瑤的愛情電影也成為人們的必要精神商品,讓無數盼望城市生活的年輕男女得到一種夢想的投射。同時,出現了所謂的"鑰匙俱樂部",青年男女工人于假日騎摩托車冶遊,而女方懷了孕則還要請頭家娘代為提親。與全島的摩托化同時,骨科被時代造就為一重要生意……
楊渡投入而不失冷靜地描寫了魅寇這樣一個臺灣男性農民創業者像一條蠻牛般地衝撞、任性,以及整個家族,特別是他的妻子,為他的發達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與坐牢的眾多代價。楊渡不掩其輕蔑與遺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這只僅余其勇而闖入工業化森林中的小獸魅寇吃幹抹凈的無情掠食者的嘴臉,但又以一管熱情如火的筆,描寫了這個時代的新興工人階級群像;他(她)們的揮霍的青春、爆發的生命力、飽滿而壓抑的情欲,他們的肌肉與她們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魯而率真的義氣世界。楊渡把他的腦袋發燒的父親和那個全身滾燙的一九七○年代寫得極為鮮活。合上書,我還能記得魅寇要周轉,回到家里,非要他母親和妻子答應賣田地的"張"(閩南語,慪氣的意思)樣。"你們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過來了,你們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機會,難道要一輩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魅寇的那兼男性憤怒與小孩撒嬌的聲口,在我書寫的此刻仍余音不絕。雖然這個年代有很多問題,帶來很多的傷害——尤其是環境生態,但楊渡對他父親的這個一九七○年代卻抱持著一種對英雄與英雄主義的敬重與惜別。一個農民出身的、日據時期小學程度的魅寇,竟然能夠為了自尊,能夠獨力鑽研出一種屬于當時日本鍋爐工業的高端技術。一九七○年代末的某一個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鄉間公路上,語重心長地告訴和他一起出差檢查某客戶鍋爐的尚在大學就讀的兒子:"這人生,終歸是一句話:終生職業之奮鬥。"
一九七○年代結束時,這本書的十章已經走完八章了。最後的兩章不能不說是潑墨似的快速走過一九八○年代之後的三十余年。讀最後兩章的感覺不能說不好,但有一種說不出的蒼涼,而且還是一種似曾相識的蒼涼。後來,我猛然一驚,咦,這不是很典型的中國式的歷史文學書寫嗎?原諒我個人化的聯想,我的確深深地感到楊渡的這兩章書寫很類似《紅樓夢》或是《三國》的尾聲,一種景物蕭條人事全非的大蒼涼:三合院空蕩蕩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養雞養鴨,然後過世了,魅寇老病殘矣,曾經是烏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紡織廠前朝氣蓬勃青年男女工人進出的盛景消失了……而烏日既沒有了一九六○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一九七○年代的朝氣拼搏,而陷入了一片大家樂賭風,處處是揮金如土的"田僑仔"。這當然不只是烏日唯然,全臺灣都變成了"一條大肥蟲,從加工出口型工業吸飽了血,張著大口,饑餓無比,倣佛什麼都可以吞進肚"。這股怪風甚至吹到了昔日"弘農堂"的楊家,連一向鄙夷魅寇好賭的魅寇妻也不能豁免于此。而之前非要賣地開工廠的魅寇,此時又為了向家里討錢而"張"(慪氣)了,但不是為了開辦實業,而是為了要買賓士轎車。一九七○年代終了以後的魅寇唯一的(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烏日的媽祖廟的籌劃興建。魅寇從一個無所依憑無所畏懼的壯年,走入了一個回向傳統與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從時代的浪頭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兒子——書寫者楊渡,則淡入了鏡頭,攜來了這個社會的變動音訊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
在楊渡筆下,一九六○年代有一種以"三合院"為核心象徵的前工業時代的人文與自然為底色,結合起當時的政治肅殺氛圍,形成的特殊"美感"(姑且如此用吧)。一九七○年代則有一種以"鍋爐"為核心象徵的工業時代的求變求新的狂熱、希望、投機、肌肉與陽剛,而這當然也是一種美感。但他似乎對于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的烏日喪失了一種熱情,乃至連一種淡淡的、頹廢的美感耽溺也沒有。那是一個或可說是以"高鐵"(以及高鐵旁邊廢棄的農田、商城的規劃用地)為核心象徵的"去工業化"的烏日,象徵的是一種精致的、冷漠的、傲慢的、終結的、遺忘的"文明",既沒有向前的熱情,也失去了對傳統的虔敬。于是他看到了那經歷"一九七○年代的大興盛,一九八○年代的狂飆,一九九○年代的沒落,現在已經徹底轉移到東南亞"的中和紡織廠廢墟,而在原址上建立了人聲嘈雜的超市賣場還有幼兒園。于是他嘆息:"有一天當所有改建完成,過去的廠房建築都消失,再不會有任何遺跡可以見證紡織廠的故事了。"這也就是整篇故事為何蕭蕭然地從高鐵烏日站開始講起的原因吧——這里有一股極深的難以言喻的落寞。這就是我為何說這是一篇為那個"短工業化年代"所做的誄文。
一九七○年代,烏日的空氣中充滿了往現代化狂奔的男性荷爾蒙,而魅寇或許就是最浸淫在這個激素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吧。而另一方面,家族里的女性則一如大地般溫柔而執著地體現了對魅寇的支持與制衡——特別是當魅寇頭腦發熱發昏不顧一切向前衝時。當楊渡把書名取為"一百年漂泊"時,以及他不止一次用"尤里西斯"來比喻他父親的一生時,他也許是在描述這一百年來臺灣男性的一種連續狀態(從那位在"二戰"時在上海的三叔公,到魅寇,乃至到敘述者自己)——"我們活著,我們滾動,如一塊頑石,漂泊四方……"但是,這樣的漂泊敘事並不包括這些男人的妻子或母親們。她們生養了一代代的人,敬天法祖,尊重生命與生活的日常要求,無可奈何而又安之若素。魅寇的母親,也就是楊渡的祖母,在魅寇的"現代化"鐵工廠內,不顧魅寇的反對,堅持要養雞、鴨,因為"長到年底剛好可以拜祖先呢!"更何況她認為"一個家,無雞啼,不成家"。魅寇的妻子,也就是楊渡的母親,她的身份也就是一般所通稱的"頭家娘",透過楊渡,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個臺灣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過去,我僅僅狹隘地從一種左翼工業社會學的角度,把頭家娘理解為臺灣中小企業的一種剝削親友鄰居勞動力的角色;她以身作則,設定勞動強度,並帶動生產。但從楊渡這里,我理解到頭家娘不只是一個匯聚多重任務(家長、媒婆、會計、廠長、總務兼倉庫管理員)于一身的角色,更是一個事業單位的精神重心,猶如一艘隨時都會隨波逐流的小船的錨。對此,楊渡甚至說:"這是一九七○年代,臺灣中小企業成功的奧秘。"語雖武斷,但作為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的加重提醒,則是必要的。在工業時代的風浪里,頭家娘仍然扮演著一種永恆的大地般的沉穩與包容,以無比的同情支持著、安慰著那永遠也回歸不了土地的男人。不僅如此,她們還背負了男性的罪愆,成為票據犯的代罪羔羊。楊渡的母親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先生的毫無財務概念的經營,與臺灣男人放縱的揮霍而導致的跳票,而逃亡而坐牢。記得有朋友曾經和我說,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很多棲枝于東京聲色場中的臺灣婦女,就是先生票據違法的妻子受害者。但可惜這些問題都沒有人做過扎實的研究。有很多原因造成這個社會現象,但其中一項必然是關鍵的,那就是這些新興的從黑手或從泥手變頭家的中小企業者,缺少現代資本主義的遊戲能力:他們不懂財務管理。楊渡說得很中肯:"財務管理,涉及一個人對金錢的觀念與處理原則,(不是)一夕可以學會的。"
如尤里西斯般漂泊的臺灣男性,之所以能漂泊,最後還是因為他有一個"水田里的妻子"。楊渡的敘事里讓我頗感動的一個圖像是:當"現代化"工廠的總經理魅寇,以應酬之名在外"漂泊"時,他的妻子,楊渡的瘦小的母親秀絨,不但要顧上一家老小,還得要咬牙擔起向來只有男人才做的——噴農藥。多年後,目睹這一景象的六叔公總是向人說:"這麼小粒子的婦人,農藥桶快要比她高,有這種力氣去噴農藥的,這一輩子沒見過,只有阿秀絨一個人。"這,大概是為什麼楊渡的書寫到了最後第五稿還是定不了題目的原因吧!因為他總是掙扎于指出這出時代劇的真正主人公到底是他父親還是他母親,或甚至于,要認同的是"父"還是"母"所體現的價值!有時,我認為他認同的是"母",但我旋而又覺得我似乎是誤解了。一直讀到"後記",我才知道楊渡把這本書(臺灣版的)的書名從《一百年漂泊》改為《水田里的媽媽》,並不是因為,如我之前所臆想的,當父親一頭熱于開工廠交際應酬自以為現代人時,母親一肩扛起了家事與農活,並像一個男人一樣在水田里勞動……而指的是為了躲避來拘捕她的警察躲在一方水田中,滿臉泥濘不掩驚慌,在暗夜中被她的兒子找到,而後開始流亡生涯的母親。這個母親形象誠然很生動乃至偉大,但卻不是一種承擔家族與傳統之重的母親形象。
穿插一個"八卦"吧。若前所述,前八章的主人公是魅寇,那麼這八章是以一種什麼事件作為壯年魅寇的結束曲呢?楊渡並沒有"曲終奏雅",他"選擇"在對父親的另一個女人的描述中結束。這顯然是相應于這個男性尤里西斯的百年漂泊主旋律的一種終曲震動吧。這是另一個如大地般的女性——雖然是在風塵中,而非在水田中——的故事。楊渡以一種不知該如何訴說但又非得訴說的心情,最後以一種"朋友"的姿態述說了父親在漂泊的一九七○年代中,所結識的那個有情義的紅粉知己,那個在魅寇逃亡的時候不求報償地接納了他,給他吃,給他住,照顧他,幫他解決問題,從而有了感情的一個女人。于是,楊渡也只有把那個名叫阿月仔的如今不知何處的女人,比喻成救起尤里西斯的克莉佩索了。而尤里西斯最終只能回到"他的綺色佳,回到潘尼洛普和孩子身邊。他有他的家園和責任"。對于克莉佩索,楊渡是難掩其同情的,因為他也深深地陷在他父親魅寇的自問中:"這樣的情義,人要怎麼報答?"而楊渡能為他父親做到的"報答",就是把這件事、這個人寫進了這個原本是以家族為綱本布局的歷史中,庶幾不讓"她"被時間的荒煙蔓草所終極覆蓋。若楊渡者,可謂體貼父志,不逆母情者也。
可能和我是一個"外省人"有關吧,讀這本書時,感受比較強烈或較陌生的有三點:殖民、宗教與家族。日本殖民給主體與家族所帶來的影響,只要看楊家的三個叔公的命運就可見其一斑了。"二戰"期間,楊渡的三叔公在上海幫日本人當翻譯,戰後死里逃生回到臺灣,六叔公則是遠赴南洋當軍夫,而平安留在家鄉的二叔公反而被美軍空襲炸掉了一條腿。至于魅寇,則是受日本小學教育的,但這樣一種教育到了國民黨政府來臺,卻又馬上像金圓券一般地貶值,這樣的一種作為無望的殖民地人民的苦悶經驗,對于後來如何形塑了魅寇這一輩人的"臺灣人的悲情"也都是具有關鍵作用的。楊渡關于父親這一代臺灣男人的心理狀況的討論,對于不論是島內的族群大和解,或是大陸對臺灣人民的感情結構的理解,都是有意義的。此外,日本教育也並不僅是"奴化",魅寇的日文教育畢竟還是發揮了效用;他憑借著那一點日文能力,自修了日本的相關出版品,獲得當時的相關科技知識,幫助他成為一個優秀鍋爐制造者。在臺灣,如何直面日本殖民的"遺留",是一個一直缺位的思考課題,而楊渡的書寫以第一人稱做了一番真摯的見證,應該納入吾人的思考參照。
在楊渡的書寫中,家族像是一條綿延不絕的河,有源有流,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有變也有不變。魅寇生了,魅寇壯了,楊渡生了,魅寇老了,楊渡的兒女生了,魅寇死了,楊渡初老了,楊渡當阿公了……而在這條大河中,死掉的人並沒有真正死,常常,祖母每天都還和死去的家人在供桌前講上一個小時的悄悄話。而一個紅通通、皺巴巴的新生兒,也不只是一個新生命,更是這個無盡傳承家族大河中的一個新加入者,既是恩典也是命運。如何在這個無盡的河里有傳有承、繼往開來,這樣一個謙卑而遠大的責任,照亮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而歸其本源,則還是在家族。這樣一個世俗化的、此在的、無可逃避的責任,似乎是當代中國人道德救贖的一個重要根源。楊渡曾經稍帶自棄地以滾石自比,以漂泊自憐,為《金剛經》里的"顛倒迷錯,流浪生死"的經文而感動流淚。但他在他的孩子出生時,領悟到一個道理:"即使再怎麼想擺脫家族的糾纏,想擺脫父母的羈絆,想擺脫家庭的束縛,但這個孩子,宣告了我的生命,無論怎麼想遠離,終究是這一條命運之線、血緣之脈的延續,我是其中的一個,勇敢承續,再也無法脫離。"楊渡講的是他的家族,難道不會讓他聯想到"中國"嗎?我不知道。而這卻是我的聯想。
另一強烈的陌生感受是"宗教"或是"魔奇"(magic)。楊渡花了不少篇幅,以一種至少並不質疑的口吻,描述他的外公的通靈軼事,或是"鳳陽教"的離奇傳奇,或是他父親的撞鬼經驗……對這些現象,我誠然不知如何好好理解,而我相信楊渡或許也有類似的困惑吧。這不是"迷信"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要之,我們還能夠繼續身心合一且安頓地接受理性或是科學世界觀(或楊渡所說的"wayofthinking")的霸權嗎?楊渡還是在一種誠實的困惑狀態中,一方面曾經在他自己所親身經歷的病魔劫難中體會了一個道理:"或許規劃命運的,不是理性自主的力量,而是某一種更高、更難測的偶然性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還是習慣性地以一種理性主義、啟蒙主義的姿態對應世界,例如他對商場中人拜"武財神"的現象所提出的隱晦"批評"。
這是一個大問題。但如果我們暫時先把"宗教"(或中國式的道德義理)從這些神奇超自然中切割開來,是否會有利于討論的進行呢?因為這整篇敘事,如果從一個最高的義理層次來理解的話,是探討我們如何在一個尤里西斯式的英雄主義工業化時代退潮時,重新建立並鞏固我們的生活與生命,以對抗那以冰涼理性安靜空虛流動的"高鐵站文明"。這本書以高鐵站迎來序曲,以朝天宮、以媽祖、以金剛經、以家族在祠堂為中心的信仰光芒中的團聚,送出終曲。于是,漂泊者魅寇的死亡,像是他一代代的先人一般,有了歸宿,于是楊渡"真正地放心大哭起來",因為意義又因家族倫理與"宗教精神"而重新飽滿起來。有了這種歷史連續感,人重新找到了時間的意義,它不再是物理時間、空洞時間,或是貨幣時間了。在"終曲"里,在鄉人眼里"從臺北回來的"楊渡,克紹箕裘,現身為朝天宮的二○一四年除夕夜開廟門的儀式參與者。他說:
時間到了,主委一聲令下:開廟門!
我們一起打開大門。
開門的那一剎那,我倣佛感受到時間之門,在遙遠的天際,緩緩打開,時間之流,像光,像水,像風,那無聲的節奏,拂過廟前的廣場,穿過廟宇的每一個雕像的眼睛,穿過每一個等候的信徒的身體,飄浮在夜的天空中。
新的一年,新的時光,新的希望,來臨了。
而我也記得,楊渡在他十六七歲時,也就是約莫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某一個秋日,母親入獄、債主逼門、父親繼續漂泊、唯一照顧他們兄妹的祖母又老耄病弱……少年的他從臺中老市區的監獄探母不成,一個人失魂落魄踽踽獨行,從三民路一路走回烏日,在那時,他夢想著一種烏托邦,在那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二○一四年初春,在楊渡的"少年烏托邦"夢想四十年後,他似乎重新找到了一種"中年烏托邦",而那是一種幾千年來屬于中國人的烏托邦吧!在一種連綿無盡的世俗時間中,找到了和先人與後人,以及無窮遠方的無盡關聯,亡者未逝,來者已至,慎終追遠,承先啟後,敬己愛人,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無愧生平之志……而如何交接匯通這兩種"烏托邦",或許是楊渡以及他這本"短工業化年代"的社會史,無論它題名為《一百年漂泊》或是《水田里的媽媽》,所留給我們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罷!因為,還需要說嗎——臺灣的今日,不是正見證著這兩種"烏托邦"的消逝嗎?
"家族"與"宗教"是在科學霸權世界觀中,受西化教育的我等,所長期漠視、輕視甚或鄙視的兩個"概念"。但如何將我們從斷裂的時間、斷裂的空間中(用老祖母的話:"像一場眠夢"的世界)自我解救出來,恐怕還是得重新思索家族與宗教這兩個概念及其所涵育的制度與價值。它們未必都好,未必都能為今日的我們所用,但否定了它們,我們也將不是我們了。我們不是很民主嗎?"公民"難道不夠嗎?——或許有人會如此抗議。但徒然"民主"或"公民"能幫助我們克服這個"像一場眠夢"的高度壓縮,從而不成理路地斷裂時空與人生嗎?臺灣人民如何自我救贖,似乎要開始重新思索那些讓人有所敬畏的厚重之德,從那里開始,重建一個真正民主社會的厚重主體,這一點是我所完全同意于楊渡的所在。如今甚囂塵上的"民主"、"自由"、"正義"或"公民"話語,如果只有民粹、自私與妒恨的內核的話,那將使臺灣陷于永劫之地。而臺灣人民果能自救于斷碎眠夢,那勢將對應該同樣陷于"像一場眠夢"的高度壓縮的當代中國大陸的發展時空有所裨益。這是臺灣真正能輸出的"未來經驗",而楊渡已經開始有所反省了。
作為一個應作者客氣之請而寫的讀後感,已經太長了。但是我還想在結尾處提一下這本書第五章里的一個饒富歷史寓言深意的小插曲。是這樣子,楊渡為了要說三合院並非總是祥和一團而有時也會吵成一團而說了一段往事。有一天,院里頭一個叔公家里丟了一串金鏈子,嬸婆大怒罵院,疑東疑西指桑罵槐,這還不解恨,竟指著老天爺詛咒,要偷她的鏈子的人不得好死。結果呢,"小偷"竟是她自己的女兒,因為受婆家欺負,想買點禮物給婆婆討個好,又沒錢,只好順手拿了母親的鏈子……結果,這個女兒也沒買到好,終而抑鬱服毒自殺。消息傳來,三合院如臨大災,全院的人驚恐諱默,而楊渡的祖母和母親則在此時,反復告誡後生,無論如何,不可施人以毒咒,因為"毒咒之于人,咒到的只是自己的心"、"人哪,厚道待人,老天才會厚道待我們"。
我初讀到這段記錄時,感覺很是震動,因為這件發生于一九六○年代臺灣中部的一個尋常三合院的往事,在今日讀來,深具一種寓言性質。這個"祖母與母親的心"相對于那位"嬸婆的嘴",似乎見證了兩種臺灣人心靈狀態的消長關係,一種對天理的敬畏之心與對他人的寬厚之心,似乎在我們的"民粹民主化"過程中,被一種只知有"當下"、"爭奪"、"我要"、"我義"、"他魔"……的心理與言說狀態中給消釋泰半了。這也許是我的"過度解讀",而非作者的本意。但是,我讀這本書時所感受到的楊渡對于他祖母的深摯厚重的感情,也不能不想象這個感情後頭的更大的文化與歷史內容吧!的確,楊渡是把對祖母的告別理解為對一個年代的告別的。
出殯之日,我持著經幡,父親捧著祖母的靈位,走過烏村的街道,街道竟變得如此陌生。它不再是童年時與祖母一同走過的街道,那是一九九○年代有超市與汽車的年代,工業的時代。屬于祖母的歲月,屬于農村生活的溫暖,那柔軟的土地的觸覺,那有著雞啼聲的微涼的早晨,隨著她的逝去,永遠消失了。
但願並非如此吧!畢竟,作者在書的"後記"里,也還如傳統的中國士大夫一樣,仍然抱持著一種信念與堅持。在指出了臺灣發展經驗的沉重代價後,楊渡說了一個寶貴的"然而"——"然而,一如臺灣民間所信持的,無論多麼扭曲、多麼變形,至少有些不變的人性,還是值得人去活、去堅持的。"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于臺中大度山
本文以《一曲告別"短工業化年代"的哀歌》為題刊載于《讀書》20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