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搖晃的中國》
辛亥到了百年雖難逃“被紀念”與“被消費”,但作史者仍應多花些心思制作產品,方可少負過去,無愧本心。在張鳴的新著中我們看不到專屬于辛亥的那個多元復雜,眾聲喧嘩的歷史舞臺,所提供的不過是一堆碎片式的八卦故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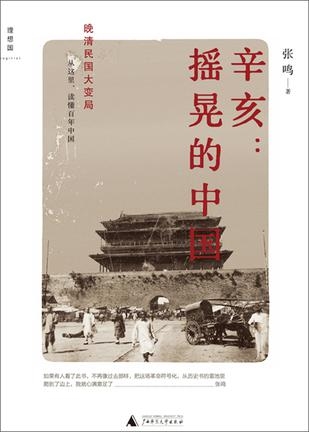
《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344頁,29.80元
公元前49年1月,愷撒率高盧軍團踏過盧比孔河,其與龐貝等支持“貴族共和”元老的內戰正式開始。名將金戈鐵馬,翻山渡河本不是件稀奇的事。此事常載史冊,一則是愷撒的赫赫聲名,二則關乎盧比孔河,其作為羅馬本土的界標,率軍渡河者,將為叛將,軍成反賊。不過有趣的是此事過後沒多少年,羅馬“共和”成為陳跡,新皇奧古斯都將山內高盧行省並入本土,從此盧比孔河失去了作為界標的意義。歲月流逝,竟連“盧比孔”之名也漸漸被遺忘了。
被遺忘的又何止是盧比孔河。太多在某個時代被視為常識的東西紛紛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之中,太多本應能豐富過去面相的人物成了“失語”之士,即使是常常被人提起的“愷撒”們,也少有人會真正在意他們在河邊曾彷徨糾結過什麼。或許有人會說愷撒的時代太過遙遠,難免有史事湮沒、難以解說的遺憾。可辛亥距今不過百年,對她的解說是否會容易一些呢?張鳴的新著《辛亥:搖晃的中國》(以下簡稱張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示范的樣本。
張鳴的作品素以好讀而著稱,在眼下這個充斥著綱目條塊式論文的環境下本屬難能可貴。不過在後記里他仍嫌此書“文字不夠瀟灑,好些意思,表達得又過于直白”,對一個寫史者來說對自己作品的反思若僅限于此,問題就出現了。寫史首在尊重史實,張著在這方面相較其他歷史暢銷書已算不錯,卻仍不免有些瑕疵。如張著115頁說“眾多的漢人官僚罕見有人抹脖子、喝藥或者跳井自殺”。116頁又說“滿人殉節倒是有幾個,比如鎮江駐防八旗副都統載穆、湖北安陸知府桂蔭。十八省漢臣里面,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這樣的封疆大吏,除了個別人比如山西巡撫陸鐘琦被義軍打死之外,居然一個殉節的都沒有”。
張著的說法實和寫《清史稿》諸公的觀點一脈相承。列傳二五六即雲:“武昌變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壽、鐘琦等數人。”說得更極端的是梁濟,在他看來“辛亥、壬子之間,自親貴、皇族、八旗官員以至全國大官、小官、庶人等,無一因清亡而死者,實為歷史上最奇特之事”。不過正是在列傳二五六中就有“仰藥以殉”的另一漢人大員——江西巡撫馮汝轐,四川總督趙爾豐雖非自殺,但也能算“以身殉清”。列傳二八三還有一漢人大員——安徽提法使(正三品,宣統二年由各省按察使改設)張毅,他的故事如從“殉節”的角度看無疑更加動人心魄:
張毅,字仁府,直隸天津人……宣統三年六月,擢安徽提法使。八月,自隴入秦,將入覲,九月,抵乾州,變作,道梗。變軍偵知之,請為參謀官,斥之,攖眾怒,羈留不得脫。會疾作,州人知毅賢,言于變軍,乃出就醫。毅念惟一死可自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醜,乘間投井死。毅無官守,中道遘變,卒完大節,世尤多之。
以上幾位還都為大員,如果不限定品級,據《清史稿》的忠義傳、吳自修輯的《辛亥殉難記》、羅正鈞輯的《辛亥殉節錄》等書記載,或投井死、或仰藥死、或被斫死的漢人官員即不下四五十人,滿人則更多,因此“罕有”或“幾個”實難自圓其說。
又如張著298頁說:“革命黨對滿人,其實倒是相當客氣,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馬,種族屠殺基本是沒有的。”這個判斷亦不能成立。路康樂(Edward Rhoads)在《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一書中就專門辟出一節討論“反滿暴行”。在他看來辛亥革命為時雖短,卻不可能不流血,將其看作一個不超過一千人至兩千人死亡的事件,實與事實相差甚遠,在武昌、西安、太原、鎮江、南京等地都有規模不一的反滿暴行,其中尤以西安最為慘烈,據一個傳教士觀察:
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都同樣被殺……房子被搶光燒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牆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旦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後來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麼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屬。” ……當滿人發現反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跪倒,放下手中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一條生路。但當他們跪下時,就被射殺了。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這樣被無情地殺死。
以上觸目驚心的觀察來自于無明顯傾向性的第三方,且也符合革命初起時的群氓心理學,連吳宓在北京消息不暢的情況下都聽說“吾陜新軍變後頗無規則,一變而為土匪,肆行劫掠”。因此在西安屠殺已成“孽種異類”的滿人並不足為奇,誰叫“土匪總是同胞人,韃子之罪該萬死”呢。據路康樂計算,西安滿人的死亡人數達到萬人,大約為當時滿城內總人口的一半。而且他進一步指出反滿暴行和滿人的反抗程度並不相關。鎮江和南京的旗兵沒有抵抗,卻依然被屠殺、驅逐。筆者還可補充的是,即使是被認為頗“和平”的杭州光復,在較新出的《許寶蘅日記》中,也會發現“獨立後殺戮駐防甚慘”等雖寥寥卻頗能描繪當時排滿景象的內容。
張著在史實上的瑕疵另有幾處,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在筆者看來重要的並不是指出上述瑕疵,而是在這些瑕疵背後反映的作者寫史之態度與心態。或許為了追求出書的速度與迎合讀者,張著所參考的資料明顯陳舊單調,近年新出的諸多材料幾乎不見。用詞通俗過度以至不免有輕佻之嫌,如“被一泡屎毀掉的暗殺”等。讀完張著,辛亥革命中的蕓蕓眾生,無論精英還是草民仍都面目模糊;歷史發展的邏輯看似說得井井有條,清晰無比,實則頗讓人懷疑他有沒有在“倒放電影”並以辛亥之歷史澆自己的塊壘;最要命的是我們看不到專屬于辛亥的那個多元復雜、眾聲喧嘩的歷史舞臺,大時代的獨特風貌正如盧比孔河般消失了!上述種種造成了:
一、張著明顯缺少對人物的悲憫和史事的理解。滿人、遺老自不必說,即使對漢人在革命中的遭際和心態張著又何嘗真正關心過?它所提供的不過是一堆碎片式的八卦故事而已。談史事也是一樣,如張著談禪讓很輕易地說:堯舜之事不可考,實際歷史中,君位獲得無非是血緣世襲和暴力劫奪罷了(頁296)。這樣對禪讓的簡單化理解其實是放過了考察辛亥及辛亥以後的一個極佳角度。事實上不少時人就是以禪讓來定位辛亥的。梁濟就說:“中華改為民主共和,係由清廷禪授而來,此寰球各國所共聞,千百年歷史上不能磨滅者也。”王獧運讀到段祺瑞發給袁世凱的勸進電報,則認為其好似“唱戲賈充”。連作為革命黨人的葉恭綽都感慨:
我國辛亥革命,非徵誅而類揖讓,以是人多忘其為革命。一般知識分子,號稱開明人士者,亦視若無睹,有時且發其時移世易之感,則以民國初期,雖號共和,而大眾多不識共和為何物,未嘗視民主為二千余年之創制,乃歷史上之一大轉變,只視為朝代轉移,如三馬同槽及劉宋趙宋之禪代而已。
為何諸多人等會以禪讓來定位辛亥?這是因為在漢以後中國人的思維世界里,革命與禪讓是理解改朝換代的兩條基本線索。兩者相較,中國經典意義里的“革命”並不是什麼好字眼,經常被儒者存而不論。即使革命在二十世紀初獲得了它的現代正面意義,對此種意義的接受程度也不能估計過高。一是因為革命古義出自《易》,是時人尤其是尚未消亡的士人們爛熟于心的東西;二則因為當時中國革命的參照係多為法國革命,其“嘗馘其王,刈其貴族,流血遍國內”的形象經過王韜、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層層發揮早已深入人心。禪讓則不同,無論是獲得政權的一方,讓渡政權的一方,還是旁觀的一方,以禪讓來包裝政權的更替都會覺得既合法又體面,接受起來較為容易。不僅如此,以禪讓釋辛亥更為日後歷史的發展埋下了很深的伏線。一方面其為袁世凱撈取了頗多政治資本,即所謂領“五族入共和之域,豐碑銅像巍巍高立于雲表”,並為其謀求稱帝提供了相當的口舌之助。另一方面清廷亦就此挽回了些許形象,嚴修就注意到隆裕太後薨,追悼會上有副對聯特別引人注目雲:
本來生生世世不願入帝王家,從黑暗中放絕大光明,全力鑄共和,普照金身四萬萬。
此後歲歲年年有紀念聖後日,于青史上現特別異彩,同情表追悼,各彈珠淚一雙雙。
至袁世凱敗亡,民國一派亂象,有人就提出“因禪讓而民得安,則千古美談,徒禪讓而民不安,則一朝代謝,謂非亡國而何?”由此而推論,1917年復辟的邏輯正在其中。而兩次復辟恰恰對諸新文化巨子們是個絕大刺激,“五四”就此發源,可見辛亥與禪讓之關係著實可令人深思。
二、張著多以革命派、立憲派等貼標簽的方式處理問題。這樣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張著的不少結論經不起推敲,如談清末諮議局選舉,最後竟說從晚清到民國就數諮議局議員的素質最高(頁280)。實際上“素質”的高與低是個最難判斷的東西,如以賄選、舞弊等論清末實在也有不少。作者對近代中國的農民曾有很好的研究,應該知道辛亥十來年後還有個時髦概念叫“土豪劣紳”,如今我們已清楚那些人的“土和劣”實來自于階級革命的“罪與罰”,當不得真。那麼諮議局議員“素質高”是神話還是歷史的實態恐怕也不易判定。另一方面貼標簽對某個具體人物思想和心態的解析幾近無能為力,正如王汎森所指出:
中國近代思想人物的風貌繁復萬端:他們有的是意態極為保守,而手段極為西化;有的是意態極為前進,而手段卻極傳統;有的是意態保守,手段傳統;有的是意態激進,手段西化……所以單只是用“傳統”或“前進”,“新”與“舊”來描述他們,常常是不夠充分的。
而在張著里既見不到立憲大佬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詐與機變,也見不到最“先進”者——留學生奔走旗門,與最顢頇的滿族親貴蠅營狗茍的醜態。同時許多立場搖擺于革命、變革、改良之間,心態處在矛盾掙扎的多重困局中人亦不在其視野之內。呂思勉即說:“君憲革命之爭起,予在手段上,隨康梁主張君憲,在感情上則主張革命。”此種人怎能用一個“立憲派”或“革命派”就能說清道明?
三則是重大概念背後學理的匱乏。一百年前的人絕大多數時候其實要比我們聰明得多,也深刻得多。以張著結論里津津樂道的“自由”為例,張著談了一通民主與自由的關係,進而畫出一條簡單的中國現代史上的民主、自由下行線,可不知為何卻把辛亥前後那些重要思想者所談的自由放在了一邊。那時所談的自由在筆者看來一最大特色即在于澄清自由有哪些類型?我們要什麼樣的自由?而不是一種標榜自身立場式的泛泛而論。梁啟超即有文明自由和野蠻自由的區分,在梁氏看來文明社會的自由與制裁互為表里,從表面看文明社會似乎比未開化社會更不自由,但這恰恰是“自由之德”,即社會成員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以為自身自由的界限。
嚴復對自由分析得更為細致。在他看來自由當分作個人自由與政界國民之自由,前者指群體公域不得侵犯、幹涉個人私域。後者則與政府管束相對,所謂政界國民自由最初的意義為無拘束、無管制,引申義則為拘束者少,管制不苛。因此“考論各國所實享自由時,不當問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得問其國政為操于議院民權,抑操于專制君權。蓋此等歧異,雖所關至巨,而實與自由無涉”。
結合辛亥前後重要思想者對自由的論述,我們可以追問張著一係列問題:作者說的是個人自由還是政界國民之自由?如果是政界國民之自由就應該意識到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科層制官僚的出現,政府角色的凸顯和法律的日趨精細,此種自由可能是越來越少了。其次對個人自由而言,如回到歷史的具體場景中,群體公域與個人私域間實在很難劃分出一條明晰的界線,尤其在那幾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階段。彼時彼刻誰又能說清走這一步就是救國救民于水火,走那一步就是暴民發泄情緒呢?最後我們的歷史敘述多有將責任往領袖、名人和精英身上一推了事的傾向,而常常忘了自身常常也是“平庸之惡”的推手之一,張著亦不能免俗。實際上即使是個人自由最受壓抑的年代,每個人仍都有選擇作高牆一分子還是那顆雞蛋的自由。即使做不了那顆雞蛋,亦可努力培養自制力,鍛煉自己內心的強大,以避免得自由卻不可承受,轉而又交出自由的悲劇命運。正如嚴復所言:“夫國民非自由之為難,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為難,吾未見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
“過去是一片神奇之地”——某學友豆瓣主頁上的一句話,筆者非常喜歡。由此而常想既目之為神奇,當有敬畏與尊重。辛亥到了百年雖難逃“被紀念”與“被消費”,但作史者仍應多花些心思制作產品,方可少負過去,無愧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