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嫬��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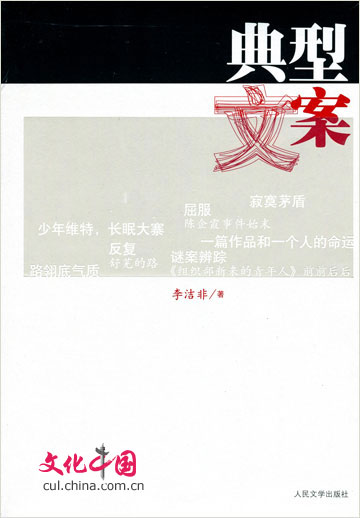
�@�@�o�O�@���y�z1949�~�H�᪺�T�Q�~��������N��ǥv�ۦW�רҪ���s�ۧ@�C�㦳�D�`��ꪺ���Y�\�ҩM���կ��L�B�ޤH�J�Ӫ��g�@����C
�@�@1949�~�H��A������N��ǻP�F�v�B�N�ѧκA��j�A��פO�q�D�`�j�j�A�g����M��˼g�����M�_�����F���M���p�C���N�������諸�������O�H�ӬO���G���B�F���B�ζաB�B�ʵ����C�L�h��s�@�a�@�~�����ѡA�@��q��ۨ����]�A�Ӧb���N�A�����q���|�`����]�A��ۨ���]�h�~���n�D�ܷL�����D�C�]�����N��ǥv���O�@���t�Ч@�ө����v�A�ӬO�@���H�ɳQ���~�����j�j���|�{��]���Ҳo��B�v�T�M���a�����v�C�q�S���ʨ��A���N��ǥv���O�@�a�v�A���O�@�~�v�F�O�ƥ�v�B�{�H�v�M���D�v�C�]���A�m�嫬��סn�M�H��������M�����v����s���j�եD��ʡA��@�a���N�a���~��B�ʱ��B�i������ʤO���P�F�m�嫬��סn�@�ѹ���N��ǥv����s�A���ߩ�b�F�����Y�����o�L�B��R�M�����W�C���N��ǥv�W�s�b�@�Ƕ����ϬM�F���ɤ�ǹҪ����嫬�H���A�٦��μΥ���´�ۿ������Y����ǥv�רҡC���R���̡A�~�����̪��Ѧh�Ӹ`�A���F�m�嫬��סn�D�n�����e�C�o���ѡA�O���_�s���ꤻ�Q�~���N��Ǫ��@�����ɮס��C�䤤�A�L��H�B�ơB�v�A���P�O�_�ҿ���l�A��L�����A���䷧�n�C�O�@���z�����Y�B�㦳�����~�M���z�t�q�M�ӤS��Ĵ��M���@�~�C
�@�@�@��²��
�@�@����D�A�ͤ_�w���X�ΡC���~�_�_���j�Ǥ���Y�A����b�s�ت��B�������N��s�|�B������|��ǰ|��¾�C�K�Q�~�N�����_�q�Ʒ��N��ǧ���A����V�M����s�A�ݨƤp���B�H���M�v�Ǽg�@�C���~�X���ۧ@�D�n���G�m�i�O�j��D�q�n�]1989�^�B�m�p���Ǥסn�]1995�^�B�m�`���C���n�]1997�^�B�m�������ءn�]1999�^�B�m�}�y�̤�O�n�]2000�^�B�m�s�ɡn�]2006�^�B�m�嫬��¡n�]2008�^�B�m��Ū���w�G��ǡB���Ѥ��l�M��ơn�]2010�^���C
�@�@�ѺK�G���X�B�E�M�ͼB�д�
�@�@1956�e��A�B�дũ���a���{�X�����s�����ۡC�L�O�p���Ӻ��Nź�A�H�ܤ_������X�B�����H�����[�����C�ڭ̨ӬݬݦP�ɥN��¤W��ӫC�~�T�Ǫ��y�z�C
�@�@���X�b��۶DzĤ@���m�b�ͦh�ơn���A�X�B�A�μB�дšC�@�B���G
�@�@�b�o�ӷ|ij�]�����C�з|���X�ު`�^�W�C�~�@�̭̳̱`��������o��X�ӡA�@�ӬO���o���A�i���O�p�����o�]���N��A�����O�o���A�֪�����@�~�o���F�C�o�N�ߨ���o���H�@���A�֪�����@�~���o���F�A�N�O���ѤF�˾`�F�����~�ɤF�e�~�t�H�F�C�ĤG�ӬO���l�A�]���j�����P�|�̳��O�g�u�p�@�~���A�֧@��F��ۤv���u�p�@�~���X�X�ѡA�֦۵M��ȶȦb���Z�W�L���]�r�S�������\�F�\�h�C�ĤT�ӵ��O�J�|�A���B�дŤ��A���w�g�[�J�@���|���A�S��ڽ��g�F�ӧ�F��N�Ӷ}�|�j�o�h��o�h�F�C
�@�@�o�T�ӡ��̱`�������ࡨ�A�B�дŮ��ȬO�ߤ@�ɱo���y���H�C���o���o�̦h�A�]�������l���A�٤w�g���J�|���C�Ӥ��X���ɶȶȡ��o���L��g�@�~�A�٦��A�L�ꥻ�A�ۧΤ��U�A�ΥL���ܻ����u�����C���C���L�A������X���A�o�ӡ����C���P�仡�O�L�ۤvı�o�A��p���O�b�O�H��ģ���U�Q��ı�o�C�ɺޥL�u�O���������N�B�дŪ��W�r�����I�F�@�U�A�����ӡ��j�o�h��o�h���B�j�v��ģ�̪����v�A�٬O�D�M�ȤW�C
�@�@���p�W�����q�ܡA�ҫ��|���a�g�A����½�L�@���A�H���ζH�N�ܱo�����A���F�G
�@�@�ӱq�B���H���f���A�ڤ]���D�L�̬O��˦a�a�X�����g�A�����M���c�@���R��ǡA�ӥ��������N���i��C�~�H�C�L�ά۷����ͦn���ܹ�t�@�ӫC�~�@�a���G���A�N履L�I���L�I�d�U�O�f�z�L�I���کM�L�̳̲פ]�L�k���������@���C�ڤ@�W�ӴN���b������աC
�@�@�o�ʤQ�Ӧr�A�O�@�T�L���v���e�A���W�D�m�yø�F1956�~�B�дŤ��}���X�����{�C�����g���O�岴�A�������M���c�@���R��ǡA�ӥ��������N���i��C�~�H���O�������{�A��ܫh�O�Ҧ��o�@�����ζH�ơC
�@�@����A�O���O���X���h���N�Ө�������A�P�ϵ��U���Ҹؤj�O�H�ڭ̦A�h�ݬݥt�~�@�ӤH���y�z�A�L�K�O�E�M�C�q�ͬ���ƭI���H�γЧ@�D���סA�E�M�B�B�дŤ������ۦ��ʡA�j�_���X�B�B�дŤ������ۦ��ʡF�P�ɡA�L�̩������W���]�`�o�h�C�ҥH�A�E�M��B�дŪ��P���A����X���Ѧһ��ȡC
�@�@�ڻ��A���b1951�~�L�̫K���L��D�C���ɡA�B�дťH���Q���ֵ����w�g���o���F�Q�X�ӵu�g�A����L���A�b�O�w���W�F�m�e�_�����n���߽s��C�E�M�o�b�����L��a����s�g���|���h�Z�C�o�ǰh�Z���A���@�g�N�ӦۼB�j�s��C�m�B�дŶǡn���A�������ɳW�x�A�h�Z�H�u��[�\�s�賡�������A���\�s��ӤH�p�W���A�B�o���]��E�M�ܦ��n�P���A�b�h�Z�H�W���g�U�F�ۤv���W�r���C�G���i���ͧ�o��Ʒ��@�E�B�B�ͽ˨Ӽg�A�����E�M��дŪ��o�ʫH�O�s�F�h�~�A�Y�Ϧb�ѴH�a��B���B�Ʒn���~��A�]�S���ٱo����C���M�ӡA�d�m�E�M�f�z�۶ǡn�A�үA�B�дŵ����Ʀh�A���_���H�o�u�r�����F�����_�ӡA�a�����ơA���_�E�M���Ȥ]�D�����ɡ��O�СC
�@�@�Y�H�m�E�M�f�z�۶ǡn���ڡA�E�M��B�дŪ��^�СA�u���t��M���֡C�L�^�Ъ��_�I�O1954�~�A���ɡA�E�M�}�B�дŤ��W�A���H�ټB�дš��p�S�̡����q�����o�u�A�����{�Ѥ@�U�C�O���Y���ܤ������D�A���j�a�����O���F�Ѷm�A�A�̭Ǥ@�����ǯন���n�B�͡��C���n�P���Ѧb�O�����u�@���_�ʤ���������C����A�E�M�������a�q�q���M�ϰO�̲հʨ����A���i���ӧ��_�ʤ�����A�b���f�����k�������H�ӡA���ݬO���ȡA�E�M�N��ť�F�O�����J�٦a�}�ۤv�h��G
�@�@�ګ��Ӫ��ê����I�A¶��F���i�Y���J�P�f�A�@�䩹�訫�@��d�ݪ��P���X�C���b���۬d�ۡA�����q�����q�J�P���ﭱ���ӡA�����ۤ@�ӤH�A��ڭ̤@�˳��O�~���H�C���H�D�D���A���I�¡A���۪������A���ΰݡA�L�@�w�N�O�B�дšC�ڰ����a�ۤ@�n���q�������A�H��j�B�a��W�e�h�C�q�������F�ڡA�L�L�o�F�@�U���A�ߨ谱���}�B���A�A�����ƨ����ڧѤF�C�L�������䨺�ӭD�G�G���H���л��A�o�N�O�B�дšC�ڻ���¼B�дŦ��X��C�B�дŬݧڤ@���A�����ڴ��F���A�Ȯ�a�����C�q�����S���Чڻ��A�o�O��E�M�A�m�e�_����n���O�̡I�ܥ������A�B�д��y�W�����Ҽ˹������F�����A�L���F�����Ѩ�N����աA�������A��ۧڡA���L�{�b�ܦ��A�N�s�����j�����O�̱ijX�A�]�o�ƥ����w�ɶ��A�H�ᦳ�ɶ����w�ɶ��A���a�C�ܭ��踨�A�L�N�~���|�B�e��A���A�z�B�ڤF�C
�@�@���_�o�@���A�ߦ~�E�M�ۼJ�ꡧ�l�P�ڡ��A�Q�H�a����������̡��A��B�дūh�H���W�H���ۺ١A���L�����B�_�����X�i�����ӤS�۵������B�ܤF���_���~�֬q���C�E�M�Z���A��ӼB�дű������ݡA�ۤv���߫ܪ��@�q�ɶ������{�P�O�H��L����P���A���ڤר�{�P��P�L���g�k�M�ӤH�D�q�����C
�@�@�s���X�B�E�M���ɳ��q�B�дŨ������F�@�{�l��A��ݤH�����C�Bź��H�β@���h�_�����A�i���@���C
�@�@�E�M�������ӧ�P�|�W�@�ӲӸ`�G
�@�@�@�ӤW�O��P�o�����H�O�B�дŦb�q����e���Ǫ��J�Ҥ��ФH�C�L���o���A�B�дŦb���ǩ����|��A�S���W�ɺ٥L�����ѱЮv���A���F�I�W���٥L�����P�ӡ��A�D�ܦ��W�J�ҤF�A�L�f�R�g�����@���ҧl���ڤJ�ҬO�@���Ҫ����a�A�p�G���l���ڤJ�ҬO�@���Ҫ��l���I��
�@�@�������o���ݤ_�H�f�۶��A���Ψ������ڡF�p�G�B�дŷ��u���L���ظܡA��L�@�y���f�R�g�����A�u�����L�C
�@�@���ɥL�����ۧڿ��ȡ��A�٦��@�Ӭ�X���ҡC�N�b�L���ɭ��Y���������C�з|���W�A�L������סB�j��ֵ��A�����������ɻ�ɡ��C2007�~12��m�ҥv�ձġn�@�h�v�ƺ١G
�@�@���ɼB�дųЧ@���Y���������|�A���K���Ǧ~���C1956 �~�K�ѡA����C�~�Ч@�|ij�W�A�B�дűa�Y�o���A����ɤ����ɦs�b�����D�o���F�@�q�N���C�j�|���@��t�d�H�A�N���Ƨi��F�Τ����C�Τ������@��ѰO�n�B���B�дšA�i�Jģ�����P�N�C�o�ƾx�o�ܤj�A�S�o�A�줣�k�Τ����ު������ɡA�Jģ���K��B�дŧ�h�ܡC�L�b�֩w�F�B�дŤ@���[�I�٤������P�ɡA�S����L�������b�j�|�W���N�R�F�ٻ��o�O���w�ɴ������M�������@���F�P�ɧ���B�дŤ��Ӥf�X�g���A���������ɻ�ɡK�K�]���íx�G�m�Jģ���P�B�дš����Ф��ӡA�Ф]���ӡ����@���ܡn�^
�@�@�کҾ\��Ƥ��A���S��������X�o�졧�����ɻ�ɡ��O�֡A���L�A�b���X�۶Ǩ��ݨ��L�{�{������@�q�A���O1957�~2��P���N�m��´���s�Ӫ��C�~�H�n�����L�������G
�@�@�K�K�q�L�}�C�~�@�̷|�]�Y���C�з|���X�ު`�^�A�ڤ]���D�@�ǫC�~�@�a�O��˦a�f�X�g���A�S�o��ɡC�o�ɩP�K�۬��Y���A���@�Ӫ��{�ܤ��n���C�~�@�a�A�s����O�A�L����Ĭ�p�Q�뭲�R�᪺��Ǧ��Z���p���R�e�A���ꩵ�w�����y�ͷ|�᪺��Ǧ��N���p�y�ͷ|�e�C�A�惡����ݪk�H
�@�@�ڧ��������F�o�Ӱ��D���ӷP�ʻP�Y���ʡC�ڪ��D�L�����O�B�дšC�ڦ^�����A�ͳo�˭��j�����D�A���Ӧ�����������ơA��`�J����s�A���Y�ª��߽סA�Ӥ����H�K�@���C
�@�@���X�U���ܨ��E���A�����P�_�Q�B�дš��������������ɻ�ɴN�O�P���A���L�A�q�Jģ�������M�������{�ݡA���Ӥ��O���@�롨����ɡC
�@�@�Jģ����B�дťs�h�����d���ɡA�ٻ��F�@�y�G���A�s�ڤ]�ݤ��_�K�K���Rť�ڪ���ժ��ܡA���wť���ǧj���A���H���ܡC�����L�{�u�Ǹo���N�A���B�дŤ����g���A�۹����C�p�G�A�~���Q���A�p�G�H�g�稽�����L�@�ǧ��V�A�L�j������קK�ݦ~���̹B�C
�@�@�]�K�ۧ���D�ۡm�嫬��סn�A�H����ǥX�����A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