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
兩個巧合,一個好奇,讓一個埋藏于歷史塵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來,讓人們重新看待這個不容忽略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巧合和好奇,才讓我們重新認識印度聖雄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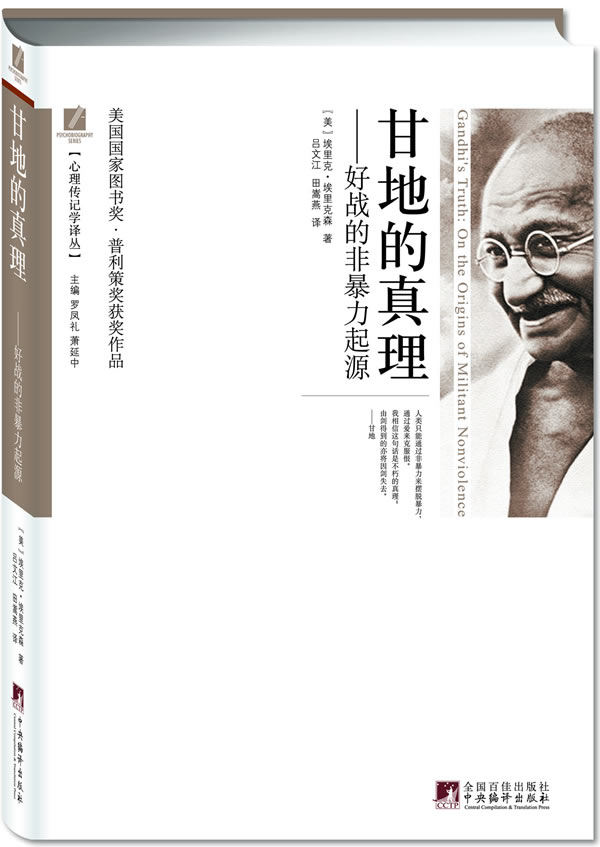
《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呂文江田嵩燕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定價:60.00元
近日,以“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為出版理念的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為“心理傳記學譯叢”的叢書,叢書的第一本——《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同時推出。
《甘地的真理》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對聖雄甘地的歷史出現和他所謂的真理涵義的探索。埃里克森探尋了當甘地成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印度大規模的平民不合作運動的革命領袖時,他是如何成功地從精神上和政治上動員印度人民的。
譯叢歷經波折
七八年前的一天,在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蕭延中聊天時,中國心理史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羅鳳禮研究員感嘆說:“雖然關于‘心理史學’介紹性的著述不算少,但係統的譯介工作並未展開,這必然會誘導學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羅鳳禮與蕭延中一同開始引進並翻譯這套“心理傳記學譯叢”。
讓蕭延中始料未及的是,引進翻譯這套譯叢是條荊棘重重的路。蕭延中回想說,一是這些傳記涉及到精神分析理論,不了解這些理論就無法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意圖;同時,叢書的傳主都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西方名人,其經歷中的許多細節又是作者著重分析的要點。這就對譯者的知識寬度和理論素養有較高的要求。開始的譯稿質量並不令人滿意,其中書籍有改譯的,有重譯的,甚至還有更換譯者的;其次是在涉及到一些為中國人所熟知的革命人物時要避諱,怕惹出政治上的麻煩。當譯叢中《甘地的真理》翻譯完成後,叢書的推出一度因為找不到出版社而擱淺。
這樣那樣的問題曾令蕭延中幾度喪失出版的信心。但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編輯看到這套譯叢後,堅信這是一套值得出版的好書,並不時地給予蕭延中積極的鼓勵和支持。蕭延中說:“說實話,如果不是中央編譯出版社堅定支持和精心編輯,恐怕讀者就不會見到這套書了。”
讀者眼前的這套“心理傳記學譯叢”,就是以譯介“心理傳記學”這一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為其學術要旨,均以大人物為研究對象。據了解,除已經面世的《甘地的真理》外,這套譯叢還將陸續出版《青年路德:項心理與歷史的研究》、《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特勒的心態:美國戰時秘密報告》、《盧梭與反叛精神》、《心理變態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心理史學視野下的領袖們》、《威廉二世與德國人》、《約翰遜與美國夢》等書。
該譯叢的責任編譯賈宇琰說,這套書的出版讓我們對歷史、對大人物會有著更接近其真實的看法,給國內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們提供了新鮮的資料和視角。
偶然的印度之旅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美國神經病學家,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師從于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埃里克森創立了“社會心理危機”的分析范式,並以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為案例,于1958年完成了具有里程碑式的“心理傳記學”名著《青年路德》。1961年後任哈佛大學人類發展學和精神病學教授,當時,他的自我心理學理論已超出精神分析的臨床范圍,廣泛滲透到社會科學諸領域,其聲譽也超出了美國國界。
埃里克森與已過世的印度聖雄甘地的奇遇從次年開始:1962年,埃里克森應邀到印度主持一個研討會,他的第一次印度之旅把他帶到了阿赫梅達巴城市。在參觀德里的柏勒宮時,埃里克森無意間發現了其花園里的一幅壁畫。壁畫簡潔明快地描述了甘地的一生,其左邊追溯了甘地精神上和歷史上的先輩,而右邊則展示了甘地在成為身著土布、代表民眾的聖人之前所經歷的誘惑、錯誤和猶豫:甘地年輕時罪惡地偷吃肉食;在一位妓女的怒吼中驚恐地逃離其房間;在當律師時,由于臨場恐懼,站在面露蔑視的法官面前目瞪口呆的樣子……
壁畫中的另一幕讓埃里克森驚訝不已,因為畫上甘地在他的真理學院前從一位富翁手中接過一袋錢幣,而那個學院正是甘地在阿赫梅達巴的住所,那位富翁恰好是在印度接待埃里克森夫婦的工廠主。更有趣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達巴領導的一次絕食罷工中面對的主要對手也就是那位工廠主,而甘地的主要支持者卻是工廠主的親姐姐。
這兩次的巧合勾起了埃里克森的好奇心。他開始走訪1918年那次罷工事件的知情人,並拜訪了阿赫梅達巴的工廠主協會;在印度國家圖書館翻閱資料,還查閱了司法、公眾、國稅和統計部門的檔案注冊簿和索引簿。他發現只有一本很薄的不到100頁的平裝小冊子描述了那次罷工。“甘地是如何一開始就陷入這種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敗了,他為什麼會失敗?或者說他為什麼這麼想?……”伴隨著這些疑問的同時,他更加確定“那次事件不像甘地本人或者其他傳記作者所描述的那樣,只是他生命中以及印度歷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應該是一個對于甘地後來成為民族領袖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發起人至關重要的事件”。此後,埃里克森開始對甘地中年階段的這段歲月入了迷,並決定重構本書所稱的“事件”,並以此為中心,對他所謂的“真理的力量”在早年生活和工作中的起源作一些廣泛的探索。
兩個巧合,一個好奇,讓一個埋藏于歷史塵土下的事件就此被重新挖掘出來,讓人們重新看待這個不容忽略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巧合和好奇,才讓我們重新認識印度聖雄甘地。
非同尋常的傳記
“眼光柔和,深沉,身體瘦弱,瘦削的臉上有一雙突出的大眼睛,頭上戴著白帽子,身上穿著粗糙的白布,赤著腳。他以大米和水果為食,水是他唯一的飲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卻從不間斷。除了他所體現的‘無限的耐心和無窮的愛心’,他身上沒有什麼能打動人的地方……”這是羅曼·羅蘭描寫甘地的段落。在很多非甘地本人所寫的傳記中也有著類似的文字。但這種字句在這位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森的筆下出現得少之又少。
對這個曾經喚起過三億人民起來反抗的人,這個曾經動搖了大英帝國的統治基礎的人,這個為人類政治生活帶來了近二百年來最強大的宗教動力的人,埃里克森沒有效倣羅曼·羅蘭的寫作手法,也不是平鋪直敘地介紹甘地的模樣、生平以及他的影響力,而著力發掘的是1918年甘地在阿赫梅達巴領導的一場地方性工人罷工事件,分析甘地倡導的“非暴力”鬥爭方式以及其對“真理力量”的獨特體認在他個人早年生活中的精神成因,包括童年“創傷”的深刻影響與人生各個關口的認同危機及克服。正因此,這部備受讚譽的關于甘地的研究著作,曾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在時隔40多年後有幸出現在國人視野里。盡管過去了快半個世紀,但它這獨特魅力卻依然散發到各國國度。
在埃里克森通過綜合臨床心理學研究甘地的童年時光和青年時代的篇章里,我們看到甘地在幼年時通過何種方式讓脾氣暴躁的父親不再對自己使用暴力。他還對甘地爾後的人生也進行了剖析,如分析1918年那次看似不起眼、被人們已經忽視的罷工事件的直接原因與後果時,逐日地加以詳細敘述。除此以外,在書中,埃里克森還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宗教信仰對甘地一生的影響。如,甘地在青年時期在英國求學時,不吃肉、不喝奶,堅持吃素,以保證不殺生,保持內心的潔凈,而這點的保持也是甘地成為印度聖雄的一個因素。
這種寫作手法是“心理傳記學”所特有的,區別于一般傳記的。“‘心理傳記學’不同于一般文學作品中的心理描寫。”蕭延中說,它不是靠人們的常識中所固有的感覺去對傳主的故事進行描述,而是通過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對具有歷史意義的生命過程展開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並揭示其公共行為背後的個人動機,無論這些行為涉及的是藝術作品的旨趣,科學理論的創造,還是政治決定的採納。
該書譯者呂文江說,埃里克森雖然相當敬佩甘地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敘述與分析卻不帶任何曲意美化的成分,反而儼然像一位外科醫生在用精神分析的“手術刀”解剖甘地,並對跨文化的可能誤解頗有警惕。作者對敘述手法也很用心,給呂文江印象最深的是埃里克森竟給不在人世的傳主甘地寫去了一封熱烈而坦誠的信件……
非暴力抵抗
毋庸置疑的是,在看到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這本書之前,大多數人都知道甘地于1919年在印度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而鮮有人了解1918年在阿赫梅達巴甘地曾組織紡織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並第一次以絕食迫使資方讓步。
“事實上,如果不了解那次事件在甘地一生乃至印度歷史中的地位,它將會被認為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對甘地恰恰在一年後成為第一次全國范圍內文明的不服從運動的領導者幾乎沒有一點幫助。”埃里克森說。在他看來,1918年的罷工事件不但具有戲劇效果和精神分析價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1918年,甘地和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早期追隨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阿赫梅達巴結合起來,從而使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學變成一種政治工具,並可以大范圍地使用,而遠不止于僅僅平息阿赫梅達巴的勞資糾紛。呂文江也說,在《甘地的真理》中能看出,雖然1918年是甘地第一次以絕食為抵抗方式,卻也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理念的真正實踐,為此後印度全國大范圍爆發這種非暴力抵抗奠定了基礎。
埃里克森如此解釋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方式,這是種雙向轉變的方式:對滿懷恨意的人,克制他的自私自利的恨,通過學著將對手當做人去愛,以一種包容性的技巧去面對對手,而這種技巧會驅使或者不如說是允許他重新獲得他的信任和愛的能力。
如今,依然有著戰爭,有著暴力抵抗,重溫甘地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呂文江說,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打下深深烙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充分體現了甘地的文化理性,即在對抗中我們也需把敵手當做與自己一樣的人去尊重,而鬥爭的方式對于其取得的結果具有基因般的作用。甘地是不相信暴力革命能取得真正的解放的,這或許是他的局限,但從另一方面倒可啟示我們,暴力革命雖然有其在特定環境下不得不如此的正義性,卻可能帶來不容忽視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