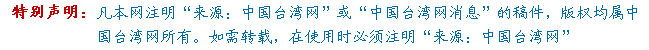話劇《故園》。(圖片來源:北京市臺聯)
中國臺灣網9月1日北京訊 “我很渺小,也很脆弱,但能對奴化教育抵制一分,就是報國一分”,在話劇《故園》的舞臺上,當主角林文軒用臺灣腔說出這句臺詞貌似文雅儒氣,我們卻聽出了普通人的家國情懷亦是擲地有聲。
回溯歷史,人們的目光往往投向金戈鐵馬、生死拼殺,感動于英雄的壯烈,陶醉于勝利的狂歡。人們常常忽視了另一個戰場,它沒有硝煙沒有炮火,卻讓千千萬萬人前赴後繼。抗戰時期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和中國人民的反文化侵略,就是這樣一場無聲的戰爭。而這場無聲的戰爭里,人們又往往忽視了一個群體,他們的名字叫“臺灣人”。
話劇《故園》以北京臺灣會館為背景,講述了1937年至1945年間,從臺灣來的教書先生和生活在小院里的北平石匠之間,由格格不入到患難與共直至生死相依的故事。國難當頭,一群普通人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堅守民族文化,堅守心靈與人性,譜寫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史詩。這部劇將抗戰題材與兩岸題材結合到了一起,以民族情懷為主調,展現了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京臺兩地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和同命運、共患難的手足親情,同時這部劇也第一次將“抗戰時期的臺灣人”這個群體形象搬上舞臺。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賠款割地的《馬關條約》,日本由此強取了覬覦已久的臺灣,開始了日本在臺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殖民者強迫臺灣人入日籍、用日姓,說日語,推行“皇民化”教育,不許臺灣人寫漢字說漢語,甚至強迫臺灣人改變風俗信仰……但臺灣人沒有屈服,他們為擺脫奴役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然而一係列的武裝鬥爭都被血腥鎮壓,臺灣同胞不甘心遭異族奴役,卻找不到出路,因此苦悶、彷徨。
文化感國運之變化、發時代之先聲,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法國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近百年來被世界多個國家選入學生教材,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名篇。在最後一堂法語課上,先生諄諄告誡學生們的那句話,深深地震撼著一代代讀者的心靈:“當了亡國奴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掌握了一把打開監獄的鑰匙。”
話劇《故園》中,臺灣人林文軒雖有日本國籍,卻因辦漢學堂而被日方通緝。作為傳統文人,他在民族危亡時刻承擔起了文化傳承的重任。日方在北平辦起學堂教中國人日文、傳播日本文化,林文軒表面為日本編寫教材,私下卻使用另一本教材,而這本教材中收錄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篇章。劇中的另一些臺灣人同樣心係祖國,他們說自己的祖籍是“福建花蓮”、“福建彰化”……
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神州大地受到空前震蕩。在艱難困厄的環境下,無人可以獨善其身。藝術源于現實,同話劇中所展現的一樣,許許多多的臺灣人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堅守著自己的“故園”之夢。
劇中的人物大多都有原型。林文軒的人物形象與著名臺灣作家林海音的父親林煥文先生頗有相似之處。林煥文畢業于臺灣總督府國語(日語)學校師范部,畢業後在學校教書。後來林煥文考入北京郵政總局,擔任日本課課長。林煥文一家十分講究民族氣節,雖在名義上是日本僑民,但是他卻把自己的籍貫寫成自己在大陸的祖籍。林煥文認為,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的孩子就應該進中國人的學校,學習中華民族的文化知識,所以他沒有把女兒林海音送進北京的日本僑校,而是把女兒送到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小學讀書,林海音在那里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小北京”。林煥文也曾為北京臺灣會館的產權多方奔走。1931年林家發生重大變故。林煥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為了支援朝鮮人民的抗日活動,他以自己在北京郵局工作為掩護,把一批抗日經費送往朝鮮,不幸在大連被日本人發現逮捕入獄,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林煥文從北平趕到大連去收屍,又傷心又生氣,回來不久就染上重病,病逝在北平。
劇中臺灣旅京同鄉會的謝會長則讓人想起臺胞梁永祿。梁永祿是臺南人,小時候被日本學生欺負,他告到校長室。日本學生說:“臺灣人一舉一動都不像日本人,放學就換臺灣服,上街就說臺灣話。”校長對打人者也未作任何處罰。梁永祿夢想著能回到祖國,有一日看到大陸來的京劇團演出《水簾洞》,他給飾演孫悟空的演員寫了一張紙條:“我羨慕你們是堂堂正正的大國公民,我是被欺辱的殖民地可憐蟲,不知何時能再與你們相聚。”那演員回寫道:“希望你們早一點回家。”自臺北醫專畢業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使梁永祿于1938年舉家遷到北平,毅然回到祖國懷抱。他在北平開辦醫院,醫術精湛、醫德高尚,他還擔任臺灣旅平同鄉會會長,為同胞積極奔走。在那個艱苦的年代,臺灣人在大陸的鄉親組織情深似海,大家為了民族存亡而團結一致,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可以說,話劇《故園》中的形象都脫胎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牙醫陳大夫”的原型是臺南人陳順龍,《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他就舉家遷到大陸,在北京前門外廊坊頭條開設了牙醫館;“實業家李老板”的原型是臺中人林子瑾,他響應孫中山先生實業救國的號召,參與修建京古路,開設北方長途汽車行,創辦了北京第一家臺資企業;“江作曲”的原型是旅京臺胞江文也,他創作的管弦樂曲《臺灣舞曲》蜚聲內外;旅京臺胞張我軍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第一人,臺胞許地山則是著名作家,其作品蘊涵著特有的東方哲學精神,這些愛國文人構成了“黃作家”的形象;畫出《棄民圖》、《亡命日記圖》等作品以宣揚抗日思想的旅京臺灣畫家王悅之及臺籍畫家張秋海、郭伯川等人則是臺灣藝術界的代表,其在劇中的形象是“畫家郭教授”……
這樣多的臺灣人,如同劇中人守護故園一樣,他們進行著微不足道卻堅忍不拔的抗爭,誠如魯迅先生所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
《故園》的導演唐燁說:“這出話劇中,我們沒有直接寫戰爭,主要講的是文化侵略與抗爭。在那樣一個大背景下,日本人希望通過文化讓中國人忘掉民族,忘掉自己的傳統,忘掉之前所有的東西。而那些為了抵抗文化侵略而頑強不屈的人們,我們不應該忘記。文化上的傳承和繼承,和戰爭獲勝相比同樣重要。”好在,我們勝利了。70年前,我們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也保住了中華文化之根基。
故園在,山河也在。1946年,臺灣民族運動先驅林獻堂先生帶領“光復致敬團”到大陸,表達600多萬臺灣同胞重歸祖國懷抱、認祖歸宗之意,他說:“光復後已覺有可愛護的國家、可盡忠的民族,永不願再見到有破碎的國家、分裂的民族。”
一百多年來,北京的臺灣會館歷經風雨,它見證過臺灣的分離之殤,見證過“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臺地軍民能舍死忘生,為國家效命!雖肝腦涂地而無所悔!”的“五人上書”,見證過全民族團結一致抵禦外辱,見證過“臺灣義勇隊”在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熱血兒女,見證過日本投降、臺灣光復,見證過一代代臺胞投身國家建設的身影,見證著如今兩岸人的中國夢。
“我的思念在大海東……它心在我心,我心長英勇”,1937年詩人蒲風為臺灣寫下了這樣的句子,那聲音穿過歷史,如黃鐘大呂一般震撼著我們的心靈。讓我們攜手,共創民族復興,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每一寸土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此。(中國臺灣網北京市臺聯通訊員 軒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