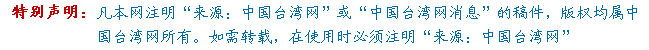臺灣老兵回山東故里 受托帶57壇骨灰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鄉探親時,與故里長輩交談。

高秉涵近照。

小學畢業證書上的高秉涵。
【冰點特稿】:葬我于故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願。
臨終前,那個在臺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里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
可是當高秉涵從臺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只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臺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麼。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臺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只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里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症,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後,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臺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于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後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後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厘米、體重卻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臺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臺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衝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里”。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並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願意家里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臺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序。並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臺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里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臺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里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道返鄉,“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的鄉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于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只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家鄉的樣子,逃難的經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後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願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採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陸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後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只有14歲的男孩,只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屍體上跑”。身後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後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里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將屍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登陸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里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藥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後,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後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臺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于在從阿根廷到臺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臺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臺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只、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後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並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里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後,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里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麼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並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臺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後,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願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並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盡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證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于故鄉的一切,盡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並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就建築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莊稼。至于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里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于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後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里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終于還是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