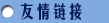臺灣作家李昂以敏銳的筆觸和大膽的手法而名噪文壇,從表現青春期少女反抗成長過程中壓抑與虛無的《花季》《人間世》,到關注鄉土傳統社會與都會 新興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到鉗制的女性身體與女性意識的《殺夫》《暗夜》,再到討論性別與權力、性愛與政治的《迷園》《北港香爐人人插》,李昂的作品中始終飽 含著鮮明的女性意識,不斷對男權社會道德判斷與審美標準進行試探與衝撞。
1983年出版的中篇小說《殺夫》的靈感來自于李昂在1978年讀到的題為“詹周氏殺夫”的社會“舊聞”,兇案原發生于抗戰勝利前夕的上海,距 離小說問世已有40年。小說當年曾獲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因其對性愛的大膽呈現和對性暴力的冷峻揭露,在當時社會形成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話題。而當時正值臺 灣新電影興起之時,一大批文學作品被改編搬上銀幕,1984年,由湯臣電影公司出資,曾壯祥執導、吳念真擔任編劇拍攝了該小說的同名電影。今天,重看這部 創作于30多年前的小說及其改編的同名電影時,仍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小說《殺夫》以“幾則新聞”作為開篇,以生硬冷峻的新聞評論式語言直陳“無姦不成殺”、“必有姦夫在後指使”、“罪大惡極”、“以匡社會風氣” 等官方話語論述,將整個故事放在男性權力主導的社會語境中;故事的講述採用倒敘,傳統封建的鄉村社會中民間話語論述先聲奪人地指出“殺夫”慘劇是“林市的 阿母回來報復的一段冤孽”。這里,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兩種論述都成為壓抑女性生存空間的話語暴力。小說的敘事充滿女性特質與鄉土風格,通過對人物命 運冷靜從容的描寫與講述,不時將讀者從人物投射中抽離出來。林市阿母出場時“嘴里正啃著一個白飯團,手上還抓著一團。已狠狠地塞滿白飯的嘴巴,隨著阿母哼 哼唧唧的出聲,嚼過的白顏色米粒混著口水,滴滿半邊面頰,還順勢流到脖子及衣襟”,“褲子退至膝蓋,上身衣服高高拉起,嘴里仍不停地咀嚼著”,這些刻意醜 化的描寫打破了讀者原本應對這個因饑餓而向“軍服男子”出賣肉體的女人的同情,揭露了女性最基本的生存權在物資匱乏的封建鄉土社會環境中遭到無情碾壓。小 說中的林市被作者當成觀點人物,以她之所見、所聞、所想、所感構成小說的敘事動力,故而林市離開祠堂後的情形只能通過後來她所聽到的幾種關于阿母的傳聞經 由讀者自己拼湊;但敘事口吻與立場卻又倣佛是鄉野村婦間“嚼舌根”似的傳遞家長里短的資訊,這些世俗社會對林市母女遭遇譏諷似的傳說暗示了林市始終受男性 威權體制主控下輿論的宰制。
文學敘事的方式顯然與電影語言的敘事方式有所不同,如果說原作開篇力圖通過多種敘事壓迫的方式有意讓讀者與主人公產生抽離感,電影則省去不易以 影像表達的“官方新聞”,弱化了對林市阿母狼狽不堪的描寫,改變了原有倒敘手法,剝去重重外殼,力圖通過影像讓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情節最直觀地呈現在觀眾 面前:夜色中,小女孩林市透過破敗的祠堂門縫目睹了阿母狼吞下食物後被一個士兵侵犯,族人聞訊趕來,在咒罵聲中絕望羞愧的阿母舉刀自盡,林市哭喊著拔刀, 引出片名“殺夫”。影像能更直接真切地鋪陳敘事,相較于文字卻也缺少了想象空間,因此影片改編時在敘事方式上做了較大變動,採用寫實的平穩敘述的手法表現 故事內容。
除了敘事方式外,開頭部分具體情節設置也與小說出入頗多。首先是林市的“告密”行為在影片中被瓦解,原作中林市目睹阿母受到侵犯後立即奔往臨近 的叔叔家求救,正是這個求救行為使她成為促成阿母走向滅亡的人,也正是這個行為鑄成一段“冤孽”,使後來人們認定林市殺夫是阿母回來報復有了依據。影片應 該是出于視覺效果和敘事節奏的考慮,沒有在阿母受到性侵這件事上做過多闡釋,卻鮮明而誇張地加入了阿母舉刀自盡和林市拔刀的鏡頭,增加了視覺衝擊力,也通 過電影語言與結尾處林市拔刀殺夫形成前後呼應。
林市所目睹的阿母因饑餓出賣身體並遭受族人懲治成為她原罪性的創傷,一直伴隨著她女性身體與心靈的成長過程。小說通過意識流式的描寫記錄了林市 青春期充滿性愛象徵意味的夢境,“幾只高得直聳入雲的大柱子,直插入一片墨色的漆黑里不知所終,突然間,一陣雷鳴由遠而近,轟轟直來,接著轟隆一聲大響, 不見火焰燃燒,那些柱子片時里全成焦黑,卻仍直挺挺立在那里,許久許久,才有濃紅顏色的血,從焦黑的柱子裂縫,逐漸地滲了出來……”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 論來看,這個夢境無疑來自于林市記憶中遭受性侵後的阿母被綁在祠堂柱子上的童年經驗。此後,林市的心理描寫貫穿了整部小說,以上吊的阿罔官為基礎構建的吊 死鬼的想象,拜神用的未煮爛的豬腳滲出的淤血,發霉的長長的面線變成一條條往外凸出的紫紅色舌頭,殘缺不全、血肉模糊的鴨仔塊塊屍身,以及混雜著辛辣膻腥 和嘶吱吼叫如同地獄般的殺豬場面,種種令人作嘔的恐怖意象摻雜在一起,拼接出一係列光怪陸離的夢境和幻覺,成為小說獨特的語言魅力與敘事風格。
林市起初只是毫無知覺、備受宰制的底層女性,默默忍受性愛不和諧的痛苦,當她受到鄉野村婦的戲謔諷刺後刻意忍住呻吟和哀叫,觸犯了陳江水作為男 人的優越感,換來的是他對林市的肢體虐待以及更進一步的經濟控制和食物壟斷,這又與林市阿母因饑餓而出賣肉體構成同一脈絡。陳江水強迫林市觀看殺豬場面並 “抱著整整一懷抱的一堆內臟與腸子”塞給林市的舉動徹底擊垮了林市的精神世界,在祭拜阿母被破壞、制止後,林市最後一點信仰與救贖也被打破,終于在精神恍 惚下依照屠夫殺豬的模式殺死了丈夫陳江水。林市從愚昧無知到瘋癲殺夫經歷了漫長跌宕的心理過程,鄉里的嘲弄、鄰居的冷漠、丈夫的粗暴以及由這些個體組成的 被父權話語牢固而嚴密控制的鄉土社會,都成為林市殺夫的幫兇。小說中林市殺夫的描寫頗為精彩:黑暗中先是恍然閃過“軍服男子”的臉,然後是一頭嚎叫掙扎的 豬仔,上揚噴灑的血幻化成一截血紅的柱子,直插入一片墨色的漆黑中,恍惚中林市以為自己是在夢境中殺豬……整個過程描寫也如夢境一般,完全採用意識流式寫 法,各種前文出現過的重要意向都在“夢境”中再次出現拼接,暗示了林市殺夫的心理過程變化。影像與文字的異質性決定了這些意識流式描寫無法通過影像呈現出 來,林市作為從肉體到精神被雙重壓抑的女性特有的意識形態在影片中被抹去,我們只能從個體經驗出發,通過銀幕上林市呆滯木訥的神情和恐懼畏縮的姿態,揣摩 她空洞的內心世界與性情轉變。
原作中作者無所忌憚地描寫林市的各種感官,對于陳江水殺豬和性虐的書寫也極盡血腥,通過文字最大限度地呈現林市面對的饑餓和性虐的雙重暴力。相 較于文字而言,本應更直觀的影像媒介在呈現這些暴力時反倒不得不有所顧忌,特別是在表現性虐方面只能通過指代性的交代鏡頭點到為止,將林市的苦難更多地局 限在拳打腳踢、羞辱謾罵等普通的家暴層面,弱化了作品以女性主義為核心的抗爭性。現代電影在表現意識流時經常採用蒙太奇跳躍剪輯手法,但這部拍攝于臺灣新 浪潮時期的文學電影明顯不願在電影形式上做過多實驗性的嘗試,在影片整體基調上與同時期許多文學作品改編電影一樣,更多地選取相對疏離、空曠的場景展現荒 涼、冷漠又壓抑的社會環境。
小說中林市面臨的侵害來自丈夫陳江水的性虐待,更來自于以阿罔官為代表的鄉野村婦們的輿論壓力。改編電影中阿罔官的角色重要性更是得到了提升, 原作中許多“民間論述”都借助她“嚼舌根”來完成,她熱衷于窺探並傳遞林市夫妻間最為私密的隱痛,恐嚇與救贖兼具地向林市傳播“民間信仰”,向林市傳授 “性愛秘笈”,又在林市殺夫後成為話語中心,妄下“無姦不成殺”的斷言。阿罔官作為女性成為父權社會輿論環境壓抑林市的代表是一個頗為反諷的現象。原著試 圖通過這種方式表明男性霸權已完全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內化到每個具體而微的人物行為與價值判斷中,很多時候甚至不需要男性出場,已被男權思想同化 洗腦的女性早已完成了“自我整肅”。影片中的阿罔官只是通過鏡頭語言和典型情節被塑造凸顯出來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形象,她的“嚼舌根”整合了鄰里街坊的鄉土 傳統社會的價值判斷。不同于原作者的女性身份,改編同名電影從導演到編劇都是男性,男性創作者恰好可以以阿罔官這一形象作為媒介充當窺探者與講述者,從而 淡化由自身性別而招致的爭議。
李昂的小說《殺夫》以女性為議題,探索傳統鄉村社會中女性受到的饑餓、性虐、暴力等多重創傷,以最赤裸和毒辣的方式揭露社會的瘡疤,其最深層的 根源還是來自于男權社會意識形態中女性基本權利的喪失。改編後的同名電影力圖最大限度地忠實原著的女性敘事,但卻因表現媒介特質與創作風格訴求的不同,省 去了多重敘事表達手法,刪減了意識流式的精神描寫,淡化了性愛與暴力的直觀呈現,最終弱化了影片中的女性意識。“婦人殺夫”的故事已經過去70年,殺夫的 婦人因為時局的變動不知所終,當年婦人所面對的社會環境雖有所改變,但同樣的情節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卻依然偶有發生,是否我們每個人都應反思,誰是今天的 “阿罔官”?(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