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重器的分量——讀劉醒龍長篇小說《蟠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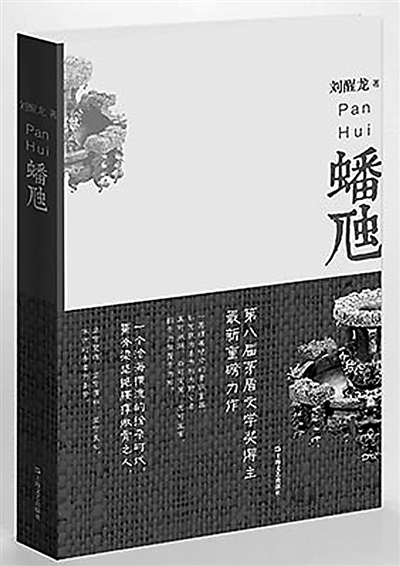
《蟠虺》劉醒龍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到了武漢,是一定要去湖北省博物館看看的,那里有太多珍貴的文物。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件展品:曾侯乙尊盤。這是一件造型繁復精美的青銅器,玲瓏剔透的鏤空裝飾完全是鬼斧神工的傑作。凝望著這件出自兩千多年前的楚國人之手的精美器物,琢磨著器物上那些優美的圖案,心想它們是否傳達了某種信息和情感?我相信,每一個作家,尤其是湖北的作家,面對這樣一件珍貴的文物時,一定不會無動于衷的。因此看到劉醒龍的新作《蟠虺》時,止不住一陣驚喜,終于有湖北作家來寫楚國最神奇(在我看來)的文物了。蟠虺是青銅器中一種常見的紋飾,以卷曲盤繞的小蛇形象組成連續不斷的裝飾。蟠虺恰是曾侯乙尊盤這一神奇文物上特有的圖飾,尊口是蟠虺狀的鏤空花紋,倣佛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的頸部則是蟠虺紋的蕉葉形向上舒展,尊腹和足都是由細密的蟠虺紋嚴嚴包實,尊底的盤也在四只方耳上飾滿蟠虺紋,與尊相呼應。看來,曾侯乙尊盤上的成千上萬條小蛇已經在劉醒龍的文學想象中蠕動起來了,那麼,劉醒龍又從這件文物中剝離出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是遠古的神話,還是歲月累積的傳說?讀下去,才發現有著強烈現實感的劉醒龍講述的仍然是一個現實的故事。小說通過文物進入到學術界,批判的鋒芒直指當下的知識分子。
完全可以用獨辟蹊徑這個成語來描述劉醒龍的構思。曾侯乙尊盤這樣一件珍貴的文物,包含著太多遠古的信息,卻是今人難以讀解的密碼。我最初以為,劉醒龍將它寫進小說里,一定是找到了破解的密碼,要帶我們去領略遠古的神奇。但在閱讀中才發現,劉醒龍完全把遠古的信息翻譯成今文,讓死去的文物在現實場景里激活。劉醒龍或許長時間地站在博物館內的曾侯乙尊盤的展櫃前,觀察來來往往的人們,看人們在曾侯乙尊盤前的神色,更揣摩人們內心的活動。小說就是以今天的人們怎麼對待曾侯乙尊盤而演繹出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曾本之是國內青銅器學界的泰鬥級人物,他之所以能成為泰鬥級人物,又完全與曾侯乙尊盤有關。這涉及一個非常專業性的學術話題,即先秦時期的青銅器的制作工藝問題。據了解,國內研究古代青銅器制作工藝的專家基本上認定,中國在先秦時期的青銅器都是採用范鑄法制作,但湖北出土了曾侯乙尊盤這類青銅器之後,有的專家認為,曾侯乙尊盤上的蟠虺鏤空圖案繁復精細,以范鑄法是難以制作出來的,因此在先秦時期應該同時也有失蠟法的工藝,曾侯乙尊盤就是採用失蠟法制作的。由此便形成了青銅器學術界的兩大派別。這在學術論爭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但劉醒龍濃烈的憂患意識即使在面對學術論爭時也沒有止步,他在想,如果無限膨脹的欲望也盯上了學術論爭,要將學術論爭當成實現欲望的工具,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呢?當然,劉醒龍的想法並不是無中生有,因為在現實中,學術腐敗在學術界變得越來越嚴重,其花樣翻新也是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于是,劉醒龍便以關于曾侯乙尊盤制作法的學術論爭為切入點,大膽揭露了學術腐敗的社會問題。曾本之老教授之所以成為青銅器學術界的泰鬥級人物,就是因為他在曾侯乙尊盤出土後,第一個提出失蠟法的學術觀點。從此他要代表楚學院每年定期給曾侯乙尊盤進行檢測。這是一個多麼神聖的工作!然而天真的學者怎麼也不會想到,有多少貪婪的人在覬覦著這青銅重器。當然,劉醒龍更要告誡人們的是,這些貪婪的人不僅包括“慣于歪門邪道、偷天換日的貪賊”,更有“強權在握的明火執仗者”,而且尤其是後者,幾乎讓人們“無法應對”。一件在地底下埋了千年的珍貴文物,在劉醒龍的手上成為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現實生活中那些冠冕堂皇的強權者的真實面目,他們的貪婪欲望可以將一切都吞噬進肚子里。天真的學者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至他們的生命。
但劉醒龍在把曾侯乙尊盤當成古代留給今人的青銅重器來寫時,還發現了另一件古代的重器留存到了今天,這就是文人的理想操守。“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務者為聖賢”。這是老學者曾本之反復說的一句話,劉醒龍以這句話作為小說的開頭,意味深長。曾本之就是這樣一位當代聖賢,他最大的優點恰好是“不識時務”,不識以金錢和利益為處事原則的“時務”。他更是一個清醒的學者,勇于反思,勇于否定自己。他提出的失蠟法觀點被人們奉為經典,寫進了青銅史,但當他在與曾侯乙尊盤不斷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有了新的發現,也就不顧個人得失,要否定失蠟法的觀點。他說他只遵循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的古訓。一方面,劉醒龍對現實的腐敗和陰謀進行冷峻和無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他沒有失去對真善美的信心。可以說,他就是懷著這樣的信心去讀解青銅器的。他發現,古人在澆鑄曾侯乙尊盤時,也把浩蕩之氣一起澆鑄在蟠虺紋上,所以他要說: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所以,他在寫到真正的曾侯乙尊盤再一次送回博物館時,會讓一股異香從存放曾侯乙尊盤的防護櫃里飄散出來。也許劉醒龍在說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時,他是以君子暗喻我們的時代,他對我們的時代充滿了信心。
劉醒龍大膽借用偵探小說的結構來承載他要表達的嚴肅主題。故事以主人公曾本之突然收到一封以死去二十多年的同事郝嘉的名義所寫的信作為開頭,就為整部小說定下了神秘的基調。誰是寫信人?信中如讖言般的四個甲骨文文字又有什麼深意?這勾起了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其後的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懸念叢生,充滿了偵探小說特有的智力挑戰。但劉醒龍這次的文體試驗並不是為了迎合讀者在故事性上的低端要求,簡單地套用偵探小說這種類型小說的模式。他是從思想主題表達的需要出發,借用了偵探小說的結構形式。因此盡管故事中包含著好幾個案件及蹊蹺的死亡,但劉醒龍並沒有以公安人員作為主視角,而是以曾本之和馬躍之這兩位聰明的老學者為主視角,在層層剝開案件謎團的同時,也揭露出知識與權力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學術腐敗的內幕。劉醒龍在真與假上大做文章,文物市場充斥著以假亂真、弄假成真,而高明的文物大盜老三口卻反其道而行之,來了個弄真成假。而面對種種利害和功名,人們遮掩真相,爾虞我詐,更是將一切變得真假難辨。但一部偵探小說最終要揭開案情的謎底。劉醒龍要告訴我們的則是:該天譴的一定會遭天譴,該天賜的一定會有天賜。(賀紹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