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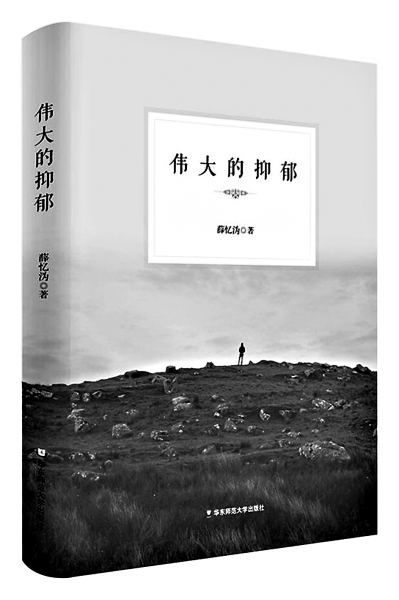
薛憶溈歷時五年的重寫之旅成為國內文學界和出版界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就在人們以為新版《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2013年),是他重寫路程中的“最後一站”,或新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15年)是他重寫“革命”中的“最後一仗”時,他“重寫的革命”烽火再起,其“戰果”之一就是新版《文學的祖國》(2015年),而另外一場“勝利”——《偉大的抑鬱》(2016年)卻來得頗為不易:
“我的這一次攀援持續了八天時間。這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八天。在這八天時間里,我一直都在遭受時差的強烈反應和心理的巨大折磨。每天的睡眠被分裂成中午和深夜兩段,每段長度都不足兩個小時。最後的四天甚至更少,兩段加在一起都只有兩個多小時。在極度亢奮和極度疲勞的狀態中,我幾次感到最邪惡的打擊已經迫在眉睫。”
這種“燈光與黎明之間”的藝術勞作幾乎就是詩人奧登心中“成為別人眼中獻身文學事業的榜樣”的現實寫照。其間所蘊含的不堪重負又讓人想起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的一個著名隱喻:“小說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頭建築他小說的房子”。而我更願意期待的是付出如此艱辛的建築終將成為寫作者生命殿堂的一部分,豐饒著寫作者的生命,誠如作者所言:“重寫雖然能夠獲得美感的回報,卻永遠是透支身心的勞作。每一次完成我都有僥幸之感,都對生命充滿了敬畏和感嘆。”
舊版《文學的祖國》的重寫終于分兩次在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這些經過作者精雕細琢的初寫和一絲不茍的重寫的作品,讓我這個老讀者仍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與啟示。它們見證了時間的神秘、語言的奇妙以及心智的熱誠與虔誠,而如此瘋狂的重寫也是作為完美主義者的薛憶溈的一次自我救贖。
薛憶溈的小說幾乎每篇都有其獨特的敘事方式與結構。饒有趣味的是,隨筆集《偉大的抑鬱》所收錄的文章,經他重新編排之後也以頗有結構意味的形式呈現。如果把這部隨筆集比作一篇結構謹嚴的長文,那麼置于隨筆集首篇的文章標題“靈魂之間的距離”可謂是提綱挈領,點明主旨。“讓讀者穿過時間的煙塵和歷史的迷霧去驚嘆一個偉大的生命不同凡響的孤獨和不可思議的激情”,這句用來描述白求恩的句子猶如貫穿文章的一條主線。而隨筆集的人文關懷則由封底的這句話來體現:“集結在這里的人物地位懸殊:從最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到最普通的中國家庭主婦。而他們的故事卻朝向共同的方向:讓生命走出形形色色的黑暗,讓精神散發經久不息的光彩。”
根據題材的不同,作者將隨筆集大致劃分為“藝術”、“歷史”、“科技”、“奇聞”和“中國”五大“板塊”,板塊內部和板塊之間又有著不同程度的聯係和錯綜復雜的交叉。如關于新浪潮導演雷諾阿的自傳《我的一生和我的電影》,也出現在關于另一位電影大師卓別林的隨筆中。尋找電影大師諾爾曼·麥克萊恩日記的願望就像當初尋找諾爾曼·白求恩大夫的檔案一樣充滿誘惑,兩個“諾爾曼”的命運都與上世紀動蕩不安的中國緊密相連。而關于鋼琴大師古爾德的講述更是以不同的敘述方式貫穿于《意大利協奏曲》、《錯誤的預言》和《最後的變奏》之中。在此,薛憶溈盡顯作為小說家的能耐,將自己在異域與古爾德紀錄片導演羅曼·克羅依特交往的經歷、大師生前的趣聞軼事以及其傳記《奇妙的陌生》混寫,融記敘與評論、現實與回憶、真實與虛構為一體,有風趣鋪陳,有旁證主題,緊要關頭宕開一筆,懸念之處戛然而止,讀來趣味盎然而又富于哲思。事實上,這些敘述手法不同程度地貫穿于這本堪為典范的隨筆集中。
五個“板塊”中,關于“歷史”的板塊分量最重,而其中《“專門利人”的孤獨》又最有影響。作為千千萬萬個“白求恩的孩子”們中的一員,薛憶溈不遠萬里來到白求恩的故鄉蒙特利爾探訪“精神之父”的足跡,而與白求恩的檔案《激情的政治》的激情相逢,給了他創作《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和《白求恩的孩子們》豐富的素材和不竭的靈感。他將平面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變成立體的懷特大夫。這是藝術的創造,更是歷史的還原。這樣的努力也見諸關于“我們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人”格瓦拉的評述。正如白求恩大夫不知道他在1939年3月4日在中國度過的第二個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後的生日,格瓦拉也不知道1967年10月9日的“玻利維亞日記”是他生命之中的最後一篇日記。這兩個共產主義戰士在“通往天堂的最後那一段路程”中,仍然對世俗生活充滿了最單純的眷戀。
薛憶溈的洞見來自于對宏觀歷史的洞察和對個體細節的關注。在龐雜的素材中,他沒有將注意力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西瓜”上,而是聚焦于那少為人知的“芝麻”中,從而在一些極細致的地方顯示對個體命運與生活的關切。在關于韓素音及其撰寫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傳主鮮為人知的一面,而且能體會到傳記作者無可奈何的落寞,因為“被顛倒過來的被顛倒的歷史總是又有可能被顛倒過去”,因為“歷史從來就沒有‘公論’。任性就是歷史的本性”(《耐人尋味的“芝麻”》)。
我相信,不管是談論文學類書籍的《文學的祖國》,還是談論非文學類書籍的《偉大的抑鬱》,這兩本以“書”為本的隨筆集都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因為它們不單是對于一本本的書的評述,更是伸向書背後的那一個個的人。“薛憶溈是低調而出色的小說家,近年在《隨筆》、《讀書》等雜志發表了不少人物隨筆和閱讀隨筆。他善于以小說家的敏感,抓住人物命運中脆弱易碎的部分,以之擊中讀者的良知;亦善于在讀解文學作品時,高度精確地捕捉其詩學細節,彰顯其哲學意味。他的文字飽蘸體恤慈悲,散發詩之光芒,對柔軟靈魂的呵護凝視動人不已。”這是作家、批評家李靜的精準概括。薛憶溈用辨識度很高的文字和文體將那些生命和歷史中“看不見”的角落呈現出來,讓我們從“看不見”的角落里看見生命和歷史的偉大,看見生命和歷史的神奇。而通過談論這些“巨匠”和“傑作”,薛憶溈也何嘗不是在記錄他在“異域的迷宮”所走過的心路歷程。
[責任編輯:楊真斌]